2024-10-02《隧道》:我只能让逻辑支配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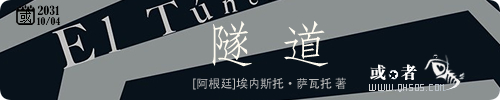
“您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您就是发信人呢?”
“我有信的草稿。”我把草稿纸拿出来说。
“我们怎么能知道这就是原信的草稿呢?”
“很简单,把信拆开就可以了。”
“如果不知道这就是您的信,我们怎么能把它打开呢?我不能这么办。”
——《30》
如何从邮局里拿回已经寄出的信?要有身份证明,这样可以证明寄信人的身份?要有寄信的收据,这样就可以证明的确寄过信?但是这并不能真正让信退回到自己手中,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没有收据。”于是,取回自己的信件就成了一个完全的悖论:要证明你就是发信人,就必须让那封信和曾经写下的草稿基本一致;但是这个证明的前提是要拆开这封信,而私人信件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私自拆封的;不能拆封就无法看到信的内容,也就无法和草稿进行对比,也就无法取回信。
摆在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面前的就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种种通向这个问题的终点又将他拉回到原点,而悖论对于卡斯特尔来说,并不仅仅是信的问题:他写这封信也完全是一种矛盾,在庄园里他被冷落,又目睹了玛丽亚的堂哥温特尔和咪咪“虚伪而轻浮”的表现,一气之下离开了庄园,然后在信中开始对玛利亚进行谩骂和伤害;但是在写好之后,又对信件作了修改,把“逃跑”改为“出走”,把“我非常敬重她对我的关心”的“对我”改成“对我这个人”,把“正如她自己能想象的”的“想象”改成“估计”,口气变得缓和,似乎不想太赤裸地伤害玛丽亚;而等到这封信寄出,又后悔于这种刺人的方式,甚至不想告诉她自己离开是因为“温特尔在吃醋”;但是当信已经从自己的手中寄出,在矛盾而悖论的世界里,再也无法收回。
无法收回便成为了一个唯一的结局,而这个唯一的结局就只属于卡斯特尔:一种像是隧道的命运,“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条隧道,一条阴暗孤独的隧道:我的隧道。”从自我出发,一切都在自我的猜测和怀疑之中,在如信件一般成为最私密的存在,还有什么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处女作,他塑造了一个活在“隧道”般命运里的个体,并不是外界让他躲进了隧道里,当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囚禁起来,他其实就是隔绝了这个世界的隧道:不是孤单和孤独,而是自我的孤立,而在这条隧道里,最可怕的不是里面的人试图爬出来,而是在矛盾中制造悖论,在感性中建构理性,最终只能越陷越深,越来也就极端:最后拿起了刀,刺向了一个在他看来深爱着的人。
这无疑就是最后的悖论:“曾经有一个也许能了解我的人。但是,此人恰恰是我杀死的那个人。”制造死亡才是悖论最后被解开的结局,所以关于死亡本身并无任何的悬念:在第一章的时候,萨瓦托通过卡斯特尔的自述,讲出了这起杀人案:“我想只要说出我的名字——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是杀死玛丽亚·伊丽巴内的那个画家,大家就能够回忆得起这桩案子,对我这个人也就无须多做解释了。”我是杀人者,一个名叫卡斯特尔的画面,我杀的人是叫玛丽亚的女人;在第二章,卡斯特尔又重复自述道:“我已经讲了,我的名字是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而在第三章,卡斯特尔的自述是:“大家都知道我杀死了玛丽亚·伊丽巴内·温特尔。”前面三章在合分的不同自述中,强调着关于死亡两端的信息:我杀死了玛丽亚,如此重复,如此强调,其实就是将杀人变成了一个和他人无关的事件,一个没有任何疑问的结局——而这又是一个悖论:这个毫无疑问的事件却是因为卡斯特尔充满了太多的疑问,当所有的疑问都不是为了寻求解答,当所有疑问都在自我推论中建立“逻辑”,逻辑也完全变成了感性的存在:它是推论,它是或者,它是可能性,于是最后逻辑变成了更多的疑问。
悖论就是那条阴暗的隧道,就是囚禁自我的隧道,就是毁灭人的隧道,而卡斯特尔之所以把自己的逻辑变成了疑问,就在于他的整条推论线路都是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正如他无法忍受对他画作进行评论的评论家一样,他们所谓的“一些深刻的理性”让他感到恶心,也就是说,卡斯特尔并不想进入他们的理性世界,而是活在自己的隧道里:在这个隧道里,记忆之中是灾祸、无耻和残酷的面孔,“记忆就像一束可怕的光线,它照亮了一个充斥着耻辱和肮脏的博物馆。”在这个隧道里,世界是可憎的,“在一个集中营里,一位曾经的钢琴家因为抱怨肚子饿而被逼吃下一只老鼠,那可是一只活老鼠。”连这样一件事都可以证明世界的无情;在这个隧道里,他把自负看作是“人类进步的崇高动力”,和仁慈、自我牺牲、慷慨结伴而行;在这个隧道里,即使他杀了人,即使把杀人的经过写下来,也认为是出于傲气和狂妄,而且认为对生活中的任何事都不需要作出解释。没有真理,没有解释,只有耻辱和肮脏,只有自负和狂妄,这就是卡斯特尔的“隧道哲学”。
但是,当他那幅名叫《母性》的画作中画着一扇被忽视的小窗,从小窗里可以看见荒凉的海滩,在海滩上有一个眺望大海的女人,女人正在望着大海等待着什么,这是不是就是在隧道哲学中留下了一个进口?“我认为,这个画面提示了一种忧郁的、绝对的孤独感。”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想要结束这种隧道的生活,但是正是因为打开了这个小窗,那个名叫玛丽亚的女人在这里驻足,正是因为玛丽亚在这里驻足,他找到了“同类”,他在孤独中发出了呼唤,正是因为他以绝对冲动和偏执的感性发出了呼唤,并让玛丽亚看到了他,于是不仅是玛丽亚再无法走出,卡斯特尔也将永远把自己禁锢起来——可悲的是,他依然活在自己的隧道里,以对外界敌视的方式为自己的罪恶寻找解释。
| 编号:C63·2240707·2151 |
小窗打开,隧道打开,当玛丽亚看见这条幽深而令人害怕的隧道,卡斯特尔对于这个能感受孤独、忧郁和绝望的“同类”表现出了无法遏制的冲动,寻找她、接近她、等待她、需要她、报复她以致最后杀死她,构成了卡斯特尔情感行进的步骤,而每一步都是在自己的所谓逻辑中,从怀疑走向更多的怀疑,从伤害切入到更深的伤害,从偏执发现更大的偏执。画展中注意到玛丽亚是卡斯特尔故事的第一步,他认为找到了自己,所以等待她再次出现;终于在街上看到了玛丽亚,于是进行了跟踪,在T大楼的电梯上,他找到了机会进行了搭讪,从那幅画,从那扇窗开始,没想到玛丽亚在犹豫之后记起了什么,然后回答他的是:“我一直记着它。”这是一句让卡斯特尔兴奋的话,茫茫人海中遇见知音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事,没有想到这么顺利地发生了,“我高兴极了,感到身体里有无穷的力量。”
但卡斯特尔也从此进入到了自设的逻辑世界里:在玛丽亚进入T大楼之后,卡斯特尔在外面等她,他分析了和玛丽亚有关的几种可能:玛丽亚是到这里来办事的,所以她还会出来;玛丽亚在相遇之后很是激动,她会先出去走走再来办事;玛丽亚就在这里上班。但不管是那种可能,对于卡斯特尔就只有一种行动:等待她再次出现。但是等待着等待着,从等待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在七点还差一刻的时候,没有见到玛丽亚的卡斯特尔又为自己提供了可能:她或者是这里的高级职员,或者是高级职员的秘书,“我抱着一丝希望想着”,但是,“到七点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后来还是等待,还是寻找,终于在希望快成为泡影的时候,看到了地铁口出来的玛丽亚,于是再次上前和她谈话,卡斯特尔比上一次更直接:“我很需要您。”而在谈及了那幅画作之后,玛丽亚告诉他的一句话是:“但是,我不知道您与我见面会有什么收获。一切靠近我的人,都会变得不幸。”
画作、窗户、玛丽亚,或许都可以看做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它们在卡斯特尔那里仅仅是看见的现象,对于玛丽亚,他并不了解却不顾一切地想要她,这种想要一开始是知音一般的存在,但是后来在“需要”意义上被冠以为爱,而实际上是得到,是占有,甚至是肉体的结合,玛丽亚对画作容易忽视部分的关注,那句“我记得你”的话,以及礼貌性地说起“我也想你”,使得卡斯特尔越陷越深,他以为这就是爱,这就是结合的开始,自我的逻辑不断延伸,不断组合:因为猜测而怀疑,因为怀疑而嫉妒,因为嫉妒而自卑,因为自卑而狂妄,最后可能的情况变成了必然,感性的解释成为了结论,“我只能让逻辑来支配自己”:他打电话给玛丽亚,发现玛丽亚在另一边想要担心被人听见,“我一关上门,别人就知道不该来打扰我了。”玛丽亚的这句话留下了诸多疑问;之后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女人却在犹豫中对话;直接去了玛丽亚的家里,却发现里面的男人竟然自称是她的丈夫,而且还是一个瞎子,而且还交给他玛丽亚的一封信,而且玛丽亚还在心里写着“我也想你”……
于是诸多的疑问开始涌现:玛丽亚为什么要逃离自己?那个女人为什么犹豫?为什么去她家里是丈夫给他的信?玛丽亚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她已经结婚?嫁给一个瞎子是她被迫的?还有玛丽亚去的那个庄园名义上是表哥温特尔的,但他们在那里到底搞什么鬼?信中那句“我也想你”是什么意思?是写给自己的还是写给别人都是这种口气?卡斯特尔被这些疑问包围着,而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这些疑问的制造者,“我的经验告诉我,它几乎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每当有一件看来非常清楚的事,—个看来属于小事的行动,它们的背后几乎总是有很复杂的动机。”但是更可怕的是,卡斯特尔并不只是对自己的回答确信,他也认为自己“无限分析事情和言论的习惯”容易走向极端,也认为应该忘掉自己作出的种种愚蠢推论,甚至也希望求得玛丽亚的原谅,甚至在自己的这个黑暗隧道里,他也希望自己以自杀的方式逃离困境,但是在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那些所谓的后悔也构成了他的逻辑,乃至最后对玛丽亚变成了威胁:“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欺骗了我,我会像杀一条狗一样把你杀掉。”
他渴望所谓的爱,渴望肉体的结合,但是他又怀疑玛丽亚的爱只是一种母性挚爱或姐姐之爱,甚至认为她的一切所为都是伪装出来的,而在去了庄园之后,他开始怀疑玛丽亚就是温特尔的情妇,甚至将其演变成了一连串的“阿连德问题”:“爱我?爱温特尔?爱那些打来电话的神秘人物中的一个?或者,她也很可能像某些男人一样,以不同的方式爱着不同的人?但是,也可能她一个人也不爱,而分别对我们这些可怜虫、毛头小伙子中的每一个人都说我们是她的唯一,而其他人只是阴影,她同他们只是表面关系。”在那封信无法取回之后,卡斯特尔开始恨自己,他去酒吧买醉,他霸占了一个罗马尼亚妓女,然后头脑中闪出一个念头:“她当然是个婊子!”罗马尼亚女人和玛丽亚,他在仇恨中建立起了逻辑:同为女人,同为快感,同样伪装,玛丽亚就是妓女,“玛丽亚和妓女有着相同的表情;妓女假装有快感,因此,玛丽亚也假装有快感;玛丽亚是一个妓女。”这是卡斯特尔运用自己的逻辑作出的推理,而这个推理彻底将他推向了那个幽深的隧道。
看了画作最后一眼,含着泪看见了海滩、女人,“种种希望都变成了纷纷剥落的碎片。”这个被打开的小窗就是一个绝望的进口,卡斯特尔终于拿起了刀,戳进了玛丽亚的身体,还在阿连德面前说:“您才是蠢货!玛丽亚也是我的情妇,是许多人的情妇!”在仇恨、轻蔑和同情中,杀了人的卡斯特尔选择了自首,甚至通过回忆和自述将其变成了出版物,这是卡斯特尔的悔过?这是事件带来的启示?真正可怕的是,卡斯特尔还在自己的逻辑里,还在自己的推论里:他还会分析骂他是“疯子”的阿连德可能自杀的原因,他还要画画并且怀疑医生们将在自己背后偷偷发笑,他甚至还偏执地认为“只有一个人理解我的画”——那扇不被人注意的窗户还留着,那个偏执的黑洞还打开着,那条黑暗的隧道还没有封闭,“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条隧道,一条阴暗孤独的隧道:我的隧道。”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