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10《把灵魂放在掌上前行》:随机而必然的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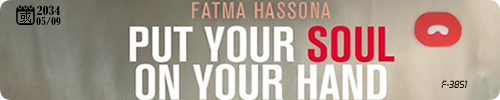
祈祷不会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2025年4月15日,导演瑟派德·法塞打通了身在加沙的女孩法蒂玛的电话,他们断断续续的连线已经持续了一年,在电话接通、在视频中看到法蒂玛平安的一刹那,法塞像往常一样,心中的石头落了地,而这次法塞告诉法蒂玛的是另一个好消息:电影已经被戛纳电影节选中了,法塞邀请她去法国戛纳,虽然法蒂玛知道自己还一时无法离开,还是愉快地分享了法塞带给自己的好消息,甚至还提到了自己的护照。出去看看世界、更好地投入摄影创作中,这一直是法蒂玛的心愿,和自己有关的这部电影入选戛纳电影节平行单元,自然是实现这一心愿所走出的第一步,“除了加沙我们一无所有”,即使面对这样的现实,法蒂玛说:“我们会重建我们的家园。”
美好心愿走出了第一步,法蒂玛的故事也通过戛纳被更多的人看到,但是悲剧却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仅仅在通话结束几个小时后,4月16日凌晨1点,正在睡梦中的法蒂玛一家6人均在以色列空袭中身亡——4月15日的这次通话成为了她和法塞之间最后的对话。也许在睡梦中法蒂玛还梦见了自己出现在戛纳,梦见了重建的加沙,梦见了一家人不再躲避子弹的生活,就像法塞在法蒂玛遇难后所描述的那样,法蒂玛的一位姐姐怀有身孕,两天前的视频中,“她曾向我展示她隆起的孕肚”,而法蒂玛在几个月前刚刚订婚。生活中充满了希望,但是炸弹却轻易击碎了梦想,最后一次通话怀抱着希望,几个小时后梦想就被无情碾碎了,它的另一个名字就叫:死亡。
当法塞告诉法蒂玛电影已经入围了戛纳电影节,那么她所说的“电影”一定没有最后的死亡,而现在作为最后成品的电影有了法蒂玛的悲剧,无疑是在法蒂玛一家遇难之后她进行了补充,电影于是被加入了最悲剧性的一幕——法蒂玛的死亡的确是一件预料之外的事,尽管最后悲剧的发生对于电纪录片来说,带来了更多的震撼,起到了更好的效果,但法塞一定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持续一年的通话中,每次法塞拨打法蒂玛的电话,她总是处在一种不安的等待中,在尚没有接通发出的声音里,法塞经历着一种煎熬,“我们的交谈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害怕悲剧发生,祈愿死亡没有降临,当电话真正接通,那悬着的心才能放下,从不安到害怕,从祈祷到放下,是法塞的拨打电话前的心路变化,这一变化折射的正是像法蒂玛一样的巴勒斯坦人在巴以这场冲突中被困住的命现实: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它是一种随机的存在,但是当炸弹真的变成了现实,它就是一种必然:随机而必然,在死亡的两端之间,有多少备受煎熬的等待,有多少毁灭希望的经历,又有多少可以留存下来的脆弱希望?
| 导演: 瑟派德·法塞 |
法塞通过和法蒂玛的视频通话,达到对“在场”的记录:电话里不时会想起阿帕奇直升机的声音,随时有炸弹在附近爆炸的声音,通话中被中断的信号、继续连接的等待,以及摇晃的镜头,都是一种对“亲历”的还原;法蒂玛也总是将手机朝向外面,整个城市已经变成了废墟,不远处还有浓烟,天空中还有飞机;法塞还在纪录片中插入了法蒂玛在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墙上的血迹,是倒塌的房屋,是街上的孩子;还有法蒂玛拍摄的几段在加沙的视频,人们在排队领取食物,或者在街上寻找什么……法蒂在现场记录着战火中的加沙,她的照片和视频是第一手资料,而与法塞的通话更是以记录的方式呈现最鲜活的现场。在视频通话中,法蒂玛背后是烧焦的墙,是残垣断壁,是避难所,她也向法塞介绍自己亲眼目睹的事,那里有叔叔一家的身亡,有身首相离的婶婶尸体,有艺术家朋友的罹难,有回到奶奶身边的梦,有最终止不住悲伤的哭泣。
当然,法塞和法蒂玛的通话,记录战火中的加沙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记录像法蒂玛一样的巴勒斯坦人积极的生活态度,法蒂玛爱好摄影、喜欢艺术,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像法塞一样能出去走走,看看世界各地的风光,虽然遥不可及,但是这个看似理想甚至梦想寄托的是她向往的正常生活;每次在视频中法蒂玛总是面带微笑,她表现出自己阳光的一面,有一次法塞看到她的房间里有阳光照进来,就让她稍微退后一点,当阳光撒在身上,法塞说:“真实太美了。”法蒂玛身处战火之中,她的身上却有着更多勇敢活下去的勇气,“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她在诗中写到:“狙击手的子弹穿过了我,而我成为了天使。”她念出《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经典台词:“希望总是非常危险的。”十个月来她一直保存着那包薯片,未曾拆开,她说这就是自己保留的希望所在。“把灵魂放在掌上前行”,“Put Your Soul On Your Hand And Walk”,这句话就来自法蒂玛的那首诗,在她看来,尽管物质匮乏,尽管生死难料,尽管每天面对困境、每天目睹死亡,但是灵魂却一直在前行,前行需要勇气,前行是为了寻找希望,活着就是不断前行。
法塞在纪录片拍摄期间,忙于自己的电影宣传,从开罗到巴黎,从加拿大到意大利,她行走在世界各地,和法塞正常人的自由相比,法蒂玛却只能困在加沙,困在战火纷飞的加沙,困在随时面临死亡的加沙,她的身边都是一面面墙,她是不自由的,她是被困的,也正因为被困,所以她渴望离开。法塞和法蒂玛之间的通话就这样呈现出战争和和平截然不同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法蒂玛甚至只活在小小的屏幕里,而当死亡变成随机发生的事件,连小小的屏幕都难以保证每一次连接会成功,每一次通话会不受干扰,每一次都是笑脸。即使如此,这依然是一个窗口,对于法塞来说,记录通话就是向世界展现战火加沙的窗口,而对于法蒂玛来说,这就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虽然杀戮仍在进行,我仍要记录,记录成为我自己,并告诉孩子我所经历的一切……”

《把灵魂放在掌上前行》电影海报
这也许就是这部纪录片的真正意义所在。但是相对于法蒂玛在“前线”冒着生命的记录,法塞虽然通过手机连线、通话还原了现场、返回了现场,并完成了在场的叙事,但是两者的对话而和交流还是缺乏丰富性的内容。一方面法塞更多是作为法蒂玛记录的二次传播者,通话、照片、视频构成了最原始的素材,法塞将这些素材剪辑而完成了纪录片,这里的问题是,加沙的生存状态只有法蒂玛的单一来源,纪录片记录的通话大约是15次,15次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这样的信息渠道还是显得单一,即使法塞在这些素材之外加入了各网站上对巴以局势的报道,作为背景的交代呈现了国际视野下的加沙,但依然无法更立体呈现加沙的现状,更深度挖掘战争对生命和生活造成的创伤。
另外一点,也许是为了和法蒂玛能有更多交流,法塞在视频中总是寻找自己亲身经历的话题——她18岁由于政治原因离开伊朗,开始了流亡生活,40年来她通过电影发声。被迫离开伊朗、无法和母亲取得联系、也无法回国,法塞的这些经历其实和法蒂玛的现状并没有多少同构的意义,法塞所面对的国内问题和法蒂玛所面临的地区局势问题也无法相提并论。虽然可能同时指向尊严、人性、自由等,但毕竟太过宽泛,也无法在对话中引起共鸣,所以在话题的引入中多少变成了尴尬,尤其是法塞说到法蒂玛的头巾,就问她在巴勒斯坦女人是不是必须戴头巾?这个问题无疑是法塞从伊朗妇女的遭遇提出的,但是法蒂玛并没有引起共鸣,她说巴勒斯坦女人并没有被强迫戴头巾,也有很多不戴头巾的女孩。虽然纪录片有不足,有遗憾,但毕竟法塞用最简单也是最富感染力的表现手法,呈现了轰炸、饥饿、逃难与死亡的加沙日常,呈现了笑容和悲痛同在、希望和忧郁相伴、勇敢和痛苦结合的个体命运。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