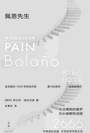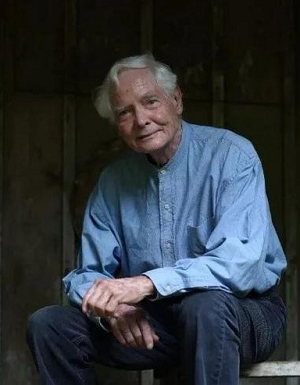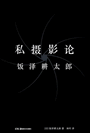 |
编号:Y55·2191018·1602 |
| 作者:【日】饭泽耕太郎 著 | |
| 出版:湖南美术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52.00元当当29.40元 | |
| ISBN:9787535684097 | |
| 页数:255页 |
“私摄影其实就是摄影家通过摄影这个媒介去探寻自己和自己周围的环境、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今年三月,饭泽耕太郎来到上海,在和读者就“摄影的私性”这一主题进行分享死如此解读“私摄影”,私摄影体现的是私性,这种私性所要探讨的是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流行,私摄影却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读,中平卓马认为,想要在“私”这个对象中寻找信赖和真实,作为一种态度无可厚非,“但这种将自我主义的丑陋显露或表达出来的做法,简直是为了逃避艰难的自我克制而做的自我辩护,又或者可以说,裸露癖般叙述身边琐事的这种做法其实毫无益处。”在这本经典日本摄影论《私摄影论》中,摄影评论权威饭泽耕太郎就是从日本摄影谱系出发,以中平卓马、深濑昌久、荒木经惟、牛肠茂雄四位代表性摄影家为例,以简洁清晰的文字、敏锐的洞察力讲述他们各自传奇的人生历程,解说一百多幅相应时期的精彩作品,观察、深入其作品中的“私性”表现,解读令人痴狂入魔的私摄影。
《私摄影论》:我自己就是乌鸦
一旦摄影家们朝着“私摄影”的方向迈进,他们往往能做出这样一种事情,即彻底破坏既是拍摄者又是拍摄对象的“我”的生活。
——《第三章 再论私摄影》
小女孩站在路上,仰着头,露出有些诡秘的微笑;身后的另一个小女孩双手抱着她,头靠在她的肩上,脸上透出的也是隐隐的笑。牛场茂雄的影集《SELF AND OTHER》,标注着的第32张照片,这是他镜头下的童年纪事,这是一览无余被定格的画面,客观、真实,以及缺少故事的虚构性,但是为什么牛场茂雄拿着这张照片的时候,会问一个奇怪的问题:“这里有几个女孩子?”几个女孩子,是露出脸的孩子的数量?但是为什么在细看之下,两双脚之外还有第三双脚:它在站着的女孩双脚和抱着她的女孩双脚之间?
从粗看到细看,从两双脚到第三双脚,无疑进入到了牛场茂雄的那个问题里:到底有几个女孩?六只脚无疑指向的是三个女孩,在排除了“怪物论”之后,牛场茂雄无疑是用照片制造谜语,就像这本影集的名字一样,是self,也是other——当other仅仅以一双脚的显露而成为和self一样的存在,牛场茂雄不是为了制造一种迷惑性,而是“不动声色地将隐藏在人类身上的未解之谜,以异于孪生子照片的角度表现了出来”——self和other一样是并置在照片里,成为被拍摄的对象,也成为被定格的存在,那个这个“不解之谜”就成为了被解之谜,它在一种被展示的平等状态中成为“三个少女”。
但是,这里的一个明显的举动是:牛场茂雄故意将应该平等展示的other即“第三个女孩”隐藏在两个女孩之后,又故意露出一双脚,既制造了一种隐秘,又创造了一种开放。和影集第58张照片一样,一家人围聚在一起,而中间那个即是牛场茂雄,当他被家人围聚在中间又表现出一种拘谨状态的时候,既成为“家族照片”的一部分,又在被围聚而守护中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家人创造的“家族”概念是一个self,而特殊存在的牛场茂雄便成为other,它是一体的,也是分割的,它是展现的,也是隐匿的。第32张照片里的第三双脚,第58张里的“我”,在既隐秘又显露,既展现又隐匿中,成为私摄影的表现的一个永恒问题:自我是物化的other,还是他者是不在场的self?
“无论哪一张照片,都可以看出与被拍摄者处于同一年纪时的牛肠君的影子,他希望照片中的这些人如超越时空一般变身成为他自己。我想,他拍摄这样的照片,就是想把这样的照片当成自画像吧。”大辻清司这样评价牛场茂雄的摄影,当他拍摄照片又想把照片变成自画像的时候,牛场茂雄的存在是作为摄影师还是作为照片中的被拍摄对象?主体和客体,似乎也并不是从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割裂开来,而这便也是“私摄影”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摄影家朝着“私”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在破坏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恒定关系时,所展现的“我”的生活,是不是一定就是一种“私摄影”?或者说,“我”是不是会变成“另一个人”的存在?
似乎要涉及到“私摄影”的定义,当“私摄影”成为一个固定词组并被大力发展的时候,完全超出了“私”和“摄影”的简单组合,而这个词组的关键词无疑是在“私”字上。饭泽耕太郎作为一个摄影评论者,站在“定点观测式地贴近摄影家实践的现场”,他其实是想发现“私摄影”里的可能性问题,而可能性之存在,就是对于必然性的突破——摄影的必然性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当按下快门,当定格瞬间,照片就变成了对于现实正确地、客观地再现,甚至导致了“摄影就是再现真实”的神话的产生。而可能性似乎在质疑这种神话:摄影是一种记录的手段还是具有创造性的“表现式媒体”?
从照片作为一种媒介特性来说,它一定是客观存在,即使如牛场茂雄的第32张照片,第三双脚在隐秘处,也是定格在照片里的一种客观,但是当这双脚被藏在不易发现的地方,牛场茂雄拍摄时的主观性就体现了出来,这种主观性就是一种“私人性质”的体现,也就是说,任何一张照片,只要有这种主观性存在,只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按下快门,就必定会有一种“私性”,“从任何照片中都能看到一个赤裸裸的‘私’的存在,它就这样借由照片显现出来。”但是这种“私性”是一种广义的私摄影,它是摄影本身就具有的特性,显然,饭泽耕太郎的这种定点观测是要寻找狭义的“私摄影”,而非常奇妙的是,摄影史从最初发展来看,“私”反而以各种形式隐藏起来,也就是说,照片在“必然性”的道路上成为一种表达公共性的媒介。
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的《自然的铅笔》,以极为日常且亲切的景象,“勾起了与之相连的思想与感情,并唤醒绘画似的创造力”;雅克-亨利·拉蒂格用照片记录资产阶级生活形态,展现那个“美好年代”;被称为“日本的拉蒂格”的石塚三郎,以拒绝成熟的方式,拥抱“未成年”的精神状态从而获得幸福感;罗伯特·弗兰克用粘贴原版照片的方式亲自制作了仅三册手工摄影集《黑、白及物》,内含妻子玛丽·弗兰克裸露胸部给刚出生的儿子巴勃罗哺乳的照片,探寻“私”表现的可能性……他们都在“私”的意义上进行着探索,表达和实践着自我意志,这些都是“私摄影”可能性的探寻,而私摄影突破必然性表达而走向可能性,其归结的一个核心依然是:什么是私?如何表现私?
这是涉及到私的本体性问题,饭泽耕太郎从“摄影家们”着手,通过对中平卓马、深濑昌久、荒木经惟和牛场茂雄四位摄影家的经历和作品分析,探寻私摄影的本体论。在他看来,“私”对于中平卓马来说,具有双重性,它既是一种恋物癖式的偏爱对象,也是“一种憎恨与诅咒的目标”,而这便造成了中平卓马极端分裂的“私”之相位。和对于“私”的理解的分裂状态一样,中平卓马成为一个摄影师也是一种困难的选择:“犹豫究竟是做一个诗人,还是做一名摄影家”,最后他成为了摄影家,却以一种诗人的视角来看待被拍摄物——他的这种诗人性其实是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干预和超越,作为一个新左翼文化鼓动者和影像上的激进主义者,中平卓马以“革命”的方式看待那个时代里应该呈现在照片上的物,满是汽油油渍的新宿街头、反射着冰冷光芒的电话亭、下街中那些宛如飘浮在空中的亡灵一般的少女们、一半融黑暗之中的自卸式卡车车篷,《挑衅》中的这些物带着冷静的客观性和被解构的诗意,他对于摄影的一个观点是:“我所认为的记录,首先是对我活着的每一刻的即时记录。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它是自闭的,是从断绝对自身的执念出发的。”
“对我活着的每一刻的即时记录”,在这里,即时记录的对象是“活着”的我,这种状态是自闭的,也就是说,中平卓马是将活着的自己封闭在照片里,隔绝了和外面世界的联系,但是他却将照片世界无限扩大,甚至让照片中的我成为影像世界的主宰,隔绝而封闭,在“粗颗粒、晃动”的照片里,中平卓马建立了“我我=摄影=世界”的等号关系,在“纯粹私摄影”中表达自我。从认为大众传播纪录的影像“一切都是幻影”的《记录这一幻影》,到“拒绝任何阴影,拒绝任何情绪潜入其中”的《植物图鉴》,再到1973年将所有胶卷都付之一炬,甚至在1977年淫恶日酒精中毒导致逆行性失忆症之后重新进行创作,中平卓马似乎就一直在自闭的世界里寻找极端的、极端的“私”性——在失忆之后渐渐恢复中,他只是醒来后吃完三餐,显影完作品烘干,然后再去睡觉,一种只是“活着”的状态,是生硬死板的,是机械重复的,但是却是纯粹的私性,“我相信朴素的、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最基本摄影行为,反而能够更准确地捕捉拍摄对象。”
中平卓马的确表现了私摄影的可能性,那个被自闭的自我便是可能性的实现和展现,但是这种在失忆症之后“活着的我”是不是在机械重复中变成了物?也就是说,自我在中平卓马的拍摄中反而被物化了。这是不是一种“病”?同样的,深濑昌久的“私摄影”也是在“无法挽救”中完成的,和中平卓马前期将摄影和政治相联系、后期表现世界的直接性不同,深濑昌久所关注的是“生命这种东西所直面的最残酷的、极限的状况”。从他最初在自己家从事摄影拍摄的“杀猪”,到之后拍摄同居女友怀孕期间的裸照、性行为、死婴,深濑昌久都是在深挖生命的残酷性,而且赤裸裸展现在照片中。与妻子鳄部洋子的相遇,他更是将这种残酷性发挥到了极致,《游戏》就是由“屠”“寿”“戏”“冥”“母”“谱”六个部分构成,展现“赤裸的私”,后来他甚至完全彻底地将洋子每日的生活记录下来。
这是一种展现生命本真的私,但是这本在和洋子的婚姻已经产生了裂隙时拍摄的摄影集,依然在展现最隐秘的生命状况,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把私摄影应该具有的情感元素都抹除了?洋子写下的一句话是:“十年间,他一边与我一起生活,一边只是在镜头中注视着我,他所拍摄的我,毫无疑问,只不过是他自己而已。”而深濑昌久自己也不回避这种自我的投影,“我总是以拍摄照片样的名目,将自己所爱之人牵连进来,结果,包括我自己在内,谁都无法获得幸福。”离婚之后深濑昌久拍摄了“乌鸦”,更是成为“只是他自己而已”的写照:黑压压地在空中展翅飞舞、两眼放光警觉地聚集在鸟巢里、在雪地上留下清晰的足迹、滑行飞过东京人行横道的那些乌鸦。饭泽耕太郎认为,“鸦”系列不是简单的动物照片集,而是投映在乌鸦身上的深濑昌久“自己的内在心性”,按照深濑昌久自己的解读,“我自己就是乌鸦”。
曾经的妻子,现在的乌鸦,以及之后继续拍摄“家族”的解体与崩坏的《家族》和《父亲的记忆》,都是在解构中完成了对于自我的命名,而在这些照片里,因为显示了“自己的内在心性”,所以物被自我化了,但是这绝不是深濑昌久探索的终点,从1989年起,他开始拍摄“私景”系列:他伸长握着照相机的手臂,将自己的脸或者身体的一部分拍摄在画面之中。“在这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把自己放入所有的场景中进行了拍摄。我发现,我在镜子中所看到的与用肉眼看到的情况大有不同,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仿佛是身后那像幽灵一般出现的场景与我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某种被透视法引出来的东西。”实际上,这个出现在镜头里、被定格在画面中的“我”已经不再是作为主体的我,而是变成了被拍摄对象,甚至成了“物化的我”,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个我不是为了自己看见,而是为了不看见,就像1992年6月的那个晚上,深濑昌久喝完了酒在走楼梯时不幸摔倒失去了意识,直到饭泽耕太郎的这本书出版的2000年他依然无法正常回归社会——就像他拍摄的那个身后有幽灵的自我一样,在照片呈现的场景里“失语了”,而我也只是变成了一个存在的物。
如果说深濑昌久的自我失语和物化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被动后的病态隐喻,那么荒木经惟的自我非符号化存在,则变成了对于自我的一次实验。和妻子阳子在新婚蜜月中拍摄的《感伤之旅》是“私摄影”的代表作,“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用私小说来形容我的摄影是最贴切的。……日常就这样简单平淡地渐渐远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仿佛感受到了些什么。”环游京都、福冈县柳川、长崎的旅行,荒木经惟拍摄下了阳子的生活和身体,尤其是给人巨大冲击的是荒木和阳子做爱的场面——荒木经惟是一边与阳子交合一边拍摄的照片展示的阳子裸体,既不是美学的人体,也不是色情的肉体,而是一个男人眼里真切的、可触摸的活生生的女人裸体。这是荒木经惟站在“拍与被拍”的关系里对私摄影的一次实践,但是当自己隐藏在照片深处,当阳子出现在画面里,是不是也如深濑昌久的妻子洋子所说,照片里的一切“只不过是他自己而已”?“我与他一起生活了十多年,有时候会觉得他这样的存在很像某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携带照相机的男人。”阳子的这句话似乎也回到了深濑昌久式的自我投影里,但是荒木经惟拍摄阳子的裸体,在她逝世时拍摄死去的面容,都是在制造一种开放性,甚至不朽性——正是将“妻子之死”这个不可挽回的事态,不加任何修饰地、原原本本地展示了出来,才使得摄影具有了永恒性意义。
但是这其中的自我即使是作为照片中物的投射,即使是站在画面背后,他依然是一个包含情感的存在状态,但是当荒木经惟开始拍摄“荒木经惟们”的时候,那种自我和深濑昌久拍摄“活着的自我”一样,已经在去符号化过程中物化了:在照片里的荒木经惟们戴着黑框眼镜,留着八字胡,他出现在任何一个位置,却似乎不再是主体,一种点缀,一种游戏式的存在,“一旦想要抓住他,他便会‘嗖’的一下从指间逃走,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存在。”——在他的《伪日记》里,一百八十七张照片有十九张照片里出现了荒木经惟,正是这些复数的、随时可能消失的“荒木经惟们”成为了荒木经惟的一个他者:“他正是通过这样的摄影行为,在持续不断地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真正的唯一的‘我’,真的存在吗?面具背后的‘真实面孔’是不存在的。”
这种追问带着质疑,是一种对自我的解构,而牛场茂雄的照片里隐匿着的自我,则是他在“他者”的客观呈现中突出自我的存在意义。和荒木经惟不同,牛场茂雄一出生就患有疾病,甚至医生断言他活不到20岁,所以他一直活在死亡的预感中,正是这种“死亡着”的进行状态,使牛场茂雄想要在摄影的镜子里存在,“他被封闭在一个蛮横无理的牢狱里,在身体无法动弹的状态下,他一定会对自身立场有所意识。”这个镜中的他者就是自我,是带着病患意识的自我,是非普通存在的自我,是other更是self,“我让我的身体包裹在从意识周边刮起的风里,步入这熟悉的街道中。然后我就在这街道上拍摄照片。”这些街上的静物不再是客观的、静止的存在,牛场茂雄将路人、广告牌、楼房,甚至颜色和光线、对话和噪音等包含进去,就是让整个世界都变成“在不透明的漩涡中不断增殖的生物”,从而变成身体的一部分,物的身体化和自我化,对于最后只活了36岁的牛场茂雄来说,就是让生命在有限中激发另一种存在,使得生命本身焕发出更私有的光辉,使之具有更有厚度的时间,也让自我的体验更加丰富。
中平卓马拍摄自闭和活着的自我,深濑昌久让自我展现生命的残酷性,荒木经惟制造非符号化的“荒木经惟们”,牛场茂雄则在隐匿中凸显时间的厚度和生命的丰富性,不管是照片里的他们还是被投影的自我,也不管是物化可消失的自我,还是作为他者的自我,他们都在探寻着“私摄影”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都是在创造着作为主体的摄影师和作为客体的拍摄对象之间建立关系,但其实,对于私摄影来说,其存在、发展甚至引起争论,除了主体客体之外,除了本体论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作为照片存在意义的观者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拍摄者拍摄的目的终极意义就是为了让人看见让人阅读,这是一种必然公开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私摄影才成为一种可能——不管是自闭性世界还是残酷性展示,不管是自我是他者,还是他者即自我,如果不是为了在公开层面留给观者一个位置,摄影的私性意义就完全没有了意义。所以当摄影师面对一个不可控、无法挽回的场景进行私摄影拍摄,还是凝聚着自己的意志走向极端的私性,其实都是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私’不仅仅是‘我’的持有物,也能通过摄影这种开放的媒介,扩散到世界之中。”
如此,正如饭泽耕太郎所说,当私摄影变成一种公共空间的表达,变成对于观者的传递,实际上包含着“吞噬破坏摄影家自身的危险”,因为那种私很可能不再是自闭的、残酷的、直接的、物化的私,在公共性中,私已经不再自由,所以不如放弃对私的直接关照,不如寻找一种忘我状态,“反而能够将‘私’从远方拉回身边。”乌鸦可能是映射了我之存在的乌鸦,乌鸦也可能表达共性情绪的乌鸦,甚至,乌鸦只是乌鸦,我也只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