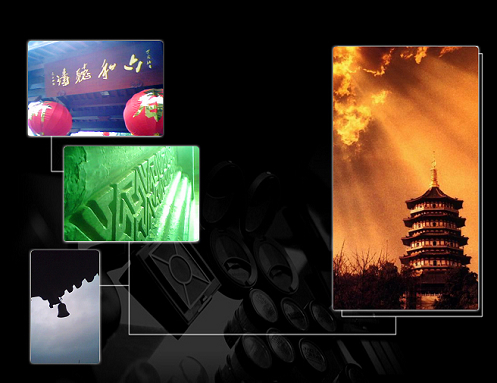2009-01-30 烟雨六和塔

“人立青冥最上层”,月轮峰南望便是宽阔钱塘江,顿时豪放,这就造就了六和塔拥有一个雄壮的境界:塔因江而造,塔因江而凌,六和塔宛如一个孤独者,在江畔度过近千年,阅尽人世故事和英雄沉浮。
今日阴雨,这样的天气登临六和塔实在有些不当,人说杭州只有西湖最美在其雾,而要在六和塔上阅尽江上风景和大桥流动车行,自然需要一个阳光能穿透空间的日子。而在烟雨中,六和塔略显神秘,冬日的寒意还未消褪,江风徐来,微微打颤,飞檐翘角上挂着的104个大铁铃已沉寂,仿佛历史也一起消逝在这个阴霾日子。
儿子要来看六和塔并非是他本意,若干天前,他想来杭州看的是保俶塔,而这也仅因为保俶塔的来历和他父亲的名字有关,因为雨天路滑,保俶塔自不必去了,而选择的六和塔还是基本满足了儿子看塔的心愿:两座塔的建造者均为同一者,自然这名字都和他的父亲有关。
保俶塔和六和塔虽然建造者一样,建造时间不远,但似乎是两种不同类型:六和塔依江,保俶塔临湖,一个豪放一个婉约,连外观形体也基本对应这样的属性,而六和塔可入内登高,保俶塔却只能依仗山势,内不可进。曾有人评价杭州的三座名塔:六和塔如将军,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老衲。
六和塔似乎为英雄而生,也似乎为英雄的归寂而存。
|
六和塔所在地原来是五代吴越国王的南果园,塔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970年),是钱弘俶舍园所造,同时还建造了塔院,建塔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钱塘江的江潮。“钱王射潮”虽然是一个传说,但是在钱王奋斗史中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奠定了钱王的统治地位,而家族中对钱江潮水的治理一以贯之,这种对自然的征服颇具英雄气概,也使六和塔不管在外形环境还是在内在理念上,都具有一种雍容大度的英雄气概。
儿子难得来好兴致,说要登上去看看,于是提携下登塔观景。木质阶梯和砖石阶梯混合着,两侧、顶部都是一些图案和花纹,未及细看,而站在哪一层上远眺钱塘江,心境自然开阔了,极目而望,仿佛那江水不在远处,而是突然奔袭而来,崇敬也会成为一种恐惧。当手摸着那些塔墙和扶梯,仿佛摸进了历史表层,让人有一种很不平整的凹凸感。拾级而上登临最高处,然后返回,我们一步一步计算着阶梯总数,201,这是一个纯粹数字,没有任何象征。
资料表明:六和塔塔高近60米,外看13层, 塔内只有7层。塔内由螺旋阶梯相连。塔内第三级须弥座上雕刻花卉飞禽、走兽、飞仙等各式图案, 刻画精细。构思精巧,结构奇妙,从塔内拾级而上,面面壶门通外廊,各层均可依栏远眺,那壮观的大桥,飞驶的风帆, 苍郁的群山, 赏心悦目。 宋郑清之有诗句云:"径行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清乾隆皇帝游此,兴致大发, 为每层依次题字立匾,名曰:初地坚固、二谛俱融、三明净域、四天宝纲、五云覆盖、六鳖负载、七宝庄严。
是为“七级浮屠”。而六和塔所承载的除了造就如钱王一样的英雄,也成为英雄的归寂之处。关于六和塔,不得不说两个传说中的人物,一个是“行者“武松,另一个则是鲁智深,同为梁山英雄,也同样选择把六和塔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
征方腊结束后,独臂武松拒绝回汴京,在六合寺出家,八十岁善终。在上世纪90年代末写的《行者武松的非文本生活》中,我写道“我觉得我身上以前那种英雄的东西仍在生长,那是一种孤独的感觉,那是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它慢慢地生长,在六和寺这样氛围中,我感受到它正破土而出,为我的孤寂生活带来一点回光返照式的激情。”生活在英雄主义时代的武松把六和塔当成是英雄的回归,而其实,那是英雄的自我缅怀。武松永远是一个孤独的行者。相对来说,鲁智深的圆寂更多是一种宿命,“听潮而圆,见信而寂”的偈言让他永远安眠在钱塘江畔。武松、鲁智深因为六和塔而寻找到了归宿,而六和塔则见证了英雄的寂寞,同时因为英雄而陡生了几分豪迈。
“孤塔凌霄汉,天风面面来。江光秋练净,岚色晓屏开”,六和塔取义“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敬”,所追求的是天地四方、和合无诤,虽在烟雨之中,仍能强烈感受到历经千年、几度修葺的六和塔依然闪耀着人类理想主义的美丽色彩和不懈追求。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