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30《二心集》: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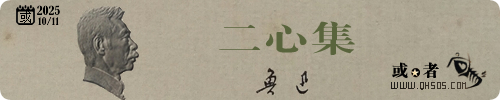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现在,是日本占领了东三省的现在;现在,是军阀却要“膺惩”中国民众的现在;现在,是反动文人却用“歌舞界的精髓”来“促进同胞的努力”的现在;现在,甚至是用“奇女子救国”式的古典传奇“为国增光”的现在……现在,就是黑暗中国的现在!
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了东山省,对于中国来说已经走到了国难当头的一步,鲁迅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对中国发动侵略,就是走出了“膺惩”中国军阀的第一步,而他们就是把中国军阀当成是他的奴仆,而“膺惩”军阀也意味着“膺惩”中国民众,因为民众就是军阀的奴隶,另一方面,这也是日本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出现了“青年援马团”——起先是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在日军进攻龙江等地时采取了抵抗行动,也曾得到了各阶层爱国人民的支持;而在上海,青年们组织了“青年援马团”,他们要求参加东北抗日军队对日作战;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加以阻挠破坏,最终使得“青年援马团”解散。
在鲁迅看来,青年援马团无疑就是中国的“堂·吉诃德”,“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虽然他们以精神的力量在显示着强大的决心,但是这也是中国的一种态度,“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而这些“堂·吉诃德”的出现,带来的是嘲笑、诧异,如此,反衬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甚而至于,在中国的黑暗现实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远路的文人学士”,他们大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这些传奇式的古典做法就是为不抵抗主义者辩护,“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这是一种文人的可耻;而另一方面,如胡展堂告诫青年,让他们要养“力”勿使“气”,要注入“国难声中的兴奋剂”,于是出现了“爱国歌舞表演”,他们说,“是民族性的活跃,是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同胞的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的,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等大明星们开始了立奏奇功的表演——在鲁迅看来,这无疑是“国难声中”的沉滓,泛上来的是明星,是文艺家,是警犬,是药,泛上来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且有很省力,但是,“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沉下去还是黑暗的中国,甚至是更黑暗,而黑暗之于中国,不仅在于让中国的“堂·吉诃德”保守嘲笑,不仅是“奇女子救国”和“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团结的荒诞剧,更在于出现了“友邦惊诧”论:当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各地学生因反对政府不抵抗政策而到南京请愿时,国民党竟然通令全国静止学生爱国行动,甚至在十七日命令军警逮捕和枪杀请愿学生,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打伤百余人,发出了“友邦惊诧论”,认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鲁迅极为愤懑,“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人家占领领土,却还说是友邦,国人爱国,竟要镇压,这便是黑暗中国最黑暗的时代!但是此种黑暗之外,中国文艺界一样进入到黑暗之中,“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杀人不是文艺,文艺却在杀人:一九三〇年的“民族主义文学”,假借的是“民族主义”,其实是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是“宠犬派文学”,“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说他们的特色就是“叫”和“恶臭”,锣鼓敲得最起劲,是一种叫,虽然没有直接地咬,但是却散发着恶臭,“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而且他们还为帝国主义“为王前驱”,是流尸文学,也是流氓政治,“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
“民族主义文学”之外,鲁迅还对梁实秋的人性文学展开论战,他们的交战从一开始是对于翻译的不同观点,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说鲁迅的翻译是“硬译”,而硬译“近于死译”,他认为这比“曲译”还要不得,““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为此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法是不完备的,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文艺变革的时代,需要一种“新造”的精神,唐译佛经,元译上谕都是一种生造,“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而当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吸收外国文学作品,就需要新造,甚至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梁实秋对于硬译的批评,鲁迅对于硬译的必要性解释,似乎都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的争论,鲁迅在回复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列举了严复“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的观点和赵景深“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观点,认为严复的翻译讲究信雅达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是不现实的,他分开了不同的读者,有些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些是略能识字的,有些是识字无几的,有些则是在“读者”范围之外,所以不能单纯追求信雅达,而是要根据中国的文或话,“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以这样的方式,“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但是对于赵景深派的“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观点,鲁迅是采取了嘲讽的态度——因为赵景深就是沿袭了梁实秋的看法,在《几条“顺”的翻译》中,鲁迅说,“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他认为对于自己硬译的翻译法,无论是梁实秋还是赵景深,都是在攻击自己,所以他反击道:“我们就已经可以决定,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而在“硬译”的纷争之外,鲁迅对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的观点提出了疑义,梁实秋提出文学是不是有阶级性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否定阶级性,就是抹杀阶级性,从而凸显人性。为此,鲁迅认为,人性阶级性不可能超越阶级性,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在喜怒哀乐、恋爱上并没有两样,但并非如梁实秋所说,“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因为文明是以资产为基础的,当富人爬上去了实现了人生的要谛和人类的至尊,文学就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何必还要表现“劣败”的无产者?再者,如梁实秋所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所以估量文学要看作品本身;第三,梁实秋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阅读和鉴赏力和阶级无关,是“天生的一种福气”,那么无产阶级也会有这样“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所以文学家要创造,并不单为皇室贵族服务,也应该为无产阶级服务,“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实际上,梁实秋否定和抹杀文学的阶级性,在鲁迅看来,是因为痛恨无产阶级文学,痛恨他们以文艺为武器,而这种痛恨竟也滋生了“好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鲁迅说,梁实秋“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这种心理在“资本家的走狗”中更强烈地表达出来,当冯乃超批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并称他是“资本家的走狗”时,梁实秋自云“我不生气”,“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而鲁迅认为,“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于是他把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的梁实秋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并且在走狗前加了一个“乏”——“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
梁实秋的观点,代表的是新月派的观点,鲁迅抨击他就是批评他们所谓“严正态度”就是“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这种针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以眼还眼”法还有张资平的“小说学”,“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还有那些“智识劳动者协会”,鲁迅说:“‘“亲爱的劳动者’呀!你们再替这些高贵的‘智识劳动者’起来干一回罢!给他们仍旧可以坐在房里‘劳动’他们那高贵的‘智识’。即使失败,失败的也不过是‘体力’,‘智识’还在着的!”当然,还有对鲁迅个人进行攻击的,常燕生在《长夜》月刊中认为“鲁迅及其追随者,都是思想已经落后的人”,又说:“鲁迅及其追随者在此后十年之中自然还应该有他相当的位置。”刘大杰在同是《长夜》中说:“鲁迅的发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创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变换变换生活,以后恐怕再难有较大的作品罢。我诚恳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开书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国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
“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文艺,“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文艺,“好政府主义”的逃避文艺……这些都是“杀人的文艺”,所以在满是抨击、围攻的黑暗中,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在鲁迅看来是“惟一的文艺运动”,是荒野中的萌芽,“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但是对于鲁迅来说,困惑依然存在,“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当时的各大报纸上甚嚣尘上,新月派、创造社都讥笑他的“投降”,把他看成是“文坛贰臣”,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梅林格曾经有过一个观点,他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如果有人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一定会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所以当鲁迅以此将这本集子取名《二心集》,似乎就自认为是“文坛贰臣”——但也并非从此就成为了无产者,这种“二心”在鲁迅看来是战斗的重新开始,是改革的必然,是在左翼文艺中创造真正的“文艺的武器”。
但是左翼文艺如何在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所以他认为,左翼文艺需要“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当革命队伍的战士们因为各自不同的目的,“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所以队伍就会变得纯粹,所以批评家就要是那些在革命中能撕掉先前假面的人;左翼文艺需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他认为左翼不能成为右翼,不能关起门来做文章,“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他认为,左翼文艺需要“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不能像梁实秋、成仿吾、钱杏邨等人那样,“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左翼文艺需要彻底的革命家,需要纯粹的战士,需要在社会上经历痛苦的破坏的建设者,需要懂得社会科学的批评家,鲁迅对左翼文艺这“惟一的文艺”充满了期待,尽管会曲折的成长,但是对于中国黑暗的现实来说,就是一种真正创造的力量。而当一九三一年左联五烈士用血书写了抗争的文章,在鲁迅看来,他们才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前驱,“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一方面他们的血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所以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死书写了革命文学的篇章,“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