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12 地震,仅仅是名词的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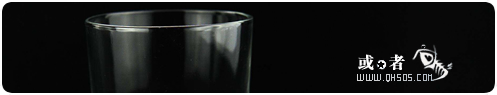
梦里的语言不是由名词构成的,语言在梦中只使用动词。
——《哈扎尔辞典》
我把语言带进了梦里?还是我在梦里生成了语言?附属或者剥离,对于一个已经记不清梦里发生一切的人来说,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不管是创造,还是说话,不管是记忆,还是虚构,其实那一刻当大地发出震动的时候,当动词被夹进现实的时候,我只是得到了一个早已被命名的指称,一个在传说中出生的名词。
4.2级地震,是在早晨醒来时听说的一个敏感词,“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2017年4月12日2时25分,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市(北纬30.08度,东经119.34度)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5公里。”这是官方的通报,只有当我打开手机打开这一个特殊的早晨的时候,它才是那些让人震惊的动词。其实,当梦境完全离开身体,当现实如约而至的时候,一切和曾经的无数个日子一样,和以后的无数个早晨一样,丝毫没有特殊性。
起床,拉开窗帘,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再习惯性地拿起手机——及物动词,现在时,一系列的动作象征着新的一天开始。但是却如一场梦一般,延续着所有迷幻的特色。先是阿柳的微信:“刚才从睡梦中被车库门咣咣作响惊醒,疑似地震,上网一查,果然发生在临安附近,4.2级。”时间是2:52分;接着是表姐发在朋友圈的一条信息:“今天早上2点27分怎么会有地震的感觉?怕!”时间是6:11分;再接着,是那些被红点标注的群里、朋友圈,关于这一场4.2级地震的播报。
 |
| 标注在传说里的地震 |
梦果真醒了?醒来是不是又是另一场梦?或者说,这场地震在手机上烈度甚至超过了现实?不管是起初的3.9级,还是最后的4.2级,地震这个词完全闪烁着梦境的特质,在被一双手控制的世界里,他们似乎在现场,摇晃、震动、不安,甚至恐惧;但更多的似乎还在和我一样与现实分不清的模糊地带,他们说,灾区人们过着幸福平安的和谐生活,他们说,我大概经历了一场假地震……调侃、搞笑、娱乐,仿佛对着一个远道而来的传说,即使看上去完全是现实的装扮,也露出一副玩笑的面容,所谓的经历,大约也是身在一种自我虚幻的情境里。
但终归是发生了,似乎还在发生,各种报道、各种消息铺天盖地,而且还有所谓的余震,只是级别太低,根本无法感觉到。这是震源深度15公里的浅源地震,这是主震-余震型地震,即使三级地震应急响应启动,即使各部门纷纷行动,但是传说却依然是传说,甚至这一个现实的传说也可以在那被记载的历史中完全被埋没。“杭州临平山,晋武帝时(281-289年)岸坠。”这是《杭州古代地震史述》上的记录,那一场地震发生在西晋,小山“岸坠”是对于地震的完全描述,所以杭州地震史,就是从西晋间震塌一座小山包开始写起;而杭州历史上烈度最高的地震,发生在吴越国宝正四年(929),有四本史籍都记载了这次地震造成的损害,《吴越备史》和《十国春秋》称“居人有坏庐舍”,《钱氏家乘》则说“居民庐舍倾圮”,《诚应武肃王集》说得最严重:“庐舍倾圮甚多”,后两本典籍中,还有赈灾的记载;《民国杭州府志》记载,1512年3月25日、5月22日、6月18日、7月20日、8月11日,一年中连续发生过5次地震,均有地声出现,“有声”“轰然有声”;自1971年有仪器精确测算后,杭州地区共发生3级以上地震14次——所以如果把现实放在历史的坐标里,这一场4.2级地震完全改写了杭州的地震历史。
历史可以被重写,而当所有的震动变成一个事件,一组数据,一种标注,它似乎只在大地的深处成为一个动词,而现实只是一个静态的名词。而在传说的世界里,在梦醒之后的早晨,我也被安放在无法亲历、无法体验的名词体系里。并非是要无限接近这一个动词,只是当身边的现实准备了一个空着的位置,期待一种创造的时候,我却是缺席的。2009年5月在采访四川灾后重建的时候,似乎是离地震最近的现实,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那一瞬间,那片土地是暂时安静的,但是那个原本平和的夜晚突然晃动起来,几乎所有人都跑出了房间,在空地上集合。但是一切的发生都在我之外,当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才知道刚刚发生了强烈的余震。没有感觉,没有体验,仿佛是隔离在现实之外,仿佛就活在传说中,动词如此之近,我去以一个名词的固有方式远离在场。
历史是一场梦,现实是一场梦,他乡是一场梦,故乡也是一场梦,原来是活在不曾醒来的世界里,布满了被指称的名词,他们说这叫地震,他们说这叫余震,连同我自己,都已经无法抵达现场,无法复原只使用动词的梦。可是那个梦醒之后的凌晨,那个大地发出震动的瞬间,我却创造了动词:口渴而醒来,看见床边的闹钟显示的是2点10分,起来在餐厅拿起杯子,杯子却空空如也;再寻找旁边的水壶,拎起,做出倒水的动作,却也是空空如也;再走进厨房间,拿起热水壶,做出注水的动作,依然是空空如也。拿起是一个动词,寻找是一个东西,倒水是一个动词,甚至失望、返回、入睡,都是一系列正在发生的动词——在梦境之外,语言只使用动词,但是却不创造一切,甚至连水这个名词也不存在。
没有水,没有名词,“因为在水下,肉身感和肉身是不可分割的,这两者只能合为一体。”是不是在无水的诡异中我一定要经历动词的世界?一定要在肉身的在场中感知震动?从起床到入睡,从现实到梦境,我一定是跨越了2点25分的震动时刻,但是为什么依然毫无感觉?为什么发生的行为无法传递?是不是看见和经历,是不是梦醒和入睡,是不是寻找水都只是一个名词的寓言?在场而不说话,我像一个指称世界的事物,像静止的第三人称,在被去除了现实的梦境中,成为一个“他”,“那时,我们熟睡的眼睛驱走了人间的字母。”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