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12《该死的女人跳舞》:活在自足的世界

11分钟,黑白,无对白。这是一个沉默的世界?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存在?已经拍摄了彩色电影的伯格曼为什么要拍一部黑白的短片?这是一种回归?回归却以单纯的女人构筑了一个单一世界,男人在哪里?男人在干什么?“该死的女人跳舞”,一种片名的解读,似乎并不是沉默的,而是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在充满了愤怒、讨伐和诅咒的声音中,该死的女人,既是道德、法律和现实意义上鄙弃,也是“应该死”的一种宿命论安排。
因为是男人在传递着“该死的女人”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当背后的控制者被抽离,这种愤怒、讨伐和诅咒,对于女人来说,是不是无奈地直面“该死”的结局?这是一个从开放到封闭的空间转型,起初两边透着光,光进入其中,门就在暗处;然后走进来一个女人,而此时的空间里已经存在了两个女人,一个是成年的女人,进来的女人站在了她的身后;接着再进来一个女人,她也靠近了里面的女人;在一个女人进入,再一个女人进入的过程中,三个女人的位置和状态发生了改变,而此时空间内的光线变暗,变暗预示着那扇开放的门被关上,于是开放的空间变成了封闭的存在——是外面的男人将她们推进了这个空间?是外面的男人制造了“该死的女人”?
封闭的空间就是一个被石壁包围的空间,它是坚硬的,它是冰冷的,它是棱角分明的,当然它也是关闭了光线的黑暗世界。在这封闭的、黑暗的、冰冷的世界里,女人伸出下垂的手,沿着石壁从上到下抚摸,她们现出痛苦的表情,她们做出挣扎的动作,他们寻找突破口却一无所获。当女人面对物世界的囚禁,她们如何解脱?于是跳舞,一种动态的呈现是为了打破静寂,一种身体的舞动是为了解构物的坚硬,而一双手,开始构筑自己触摸的世界,不是沿着石壁触摸,而是触摸着彼此的身体——身体之于身体,是一种变动,左侧或右侧,位置的更改是一种探求;手之于手,是一种延伸,手抚摸她的头,手抚摸她的身体,手张开十指,手握紧为拳头,而且手也可以敲击石壁,一种反抗的语言形成;于是,身体保护着身体,手保护着身体,手保护着手,或者伸向光亮之处,或者两只手交汇在一起,或者手遮住惊恐的脸。
| 导演: 英格玛·伯格曼 |
三个女人,三个身体,三双手,这是“该死的女人”,她们或者是走向死亡的女人,或者是死而复生的女人,在黑暗、封闭构筑的世界里,她们其实用自己的舞蹈叙说着女人的反抗,“该死的女人”是在回击着“该死的男人”。但是,在这女人舞蹈的世界里,因为一个小女孩的存在,让整个空间变成了自足的世界。小女孩没有过多的痛苦,没有太多的挣扎,她的脸上甚至带着隐秘的微笑,她是自由的象征,甚至她本身就是一个脱离了男性世界而存在的象征,而小女孩在女人面前更是制造了属于女人的希望。她的手中拿着一个娃娃,或者抱在怀里,或者和它一起躺在地上,或者和它说话。娃娃是关于生命的符号,在伯格曼的电影《生命的门槛》中,就出现了一个娃娃,它曾经是小女孩的最爱,但是在女人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娃娃掉在了地上,后来医生将它捡起来。被丢弃的娃娃,被捡起的娃娃,这是命运转折的过程,当三个女人面对“生产”这个和女人有关的问题,她们需要的是一种爱,在爱的世界里,生命才是一种值得。
所以娃娃指向的是生命本身,而小女孩和娃娃在一起更是生命的双重象征,当她的手一刻也没有离开娃娃,更是对生命本身的关爱,而这种生命哲学也影响着其他三个女人的态度:她们或者是想要孩子的恋人,或者是生了孩子的母亲,或者是因为孩子被抛弃的女人,所有的女性角色都和孩子有关,而小女孩本身就是一个孩子,她是纯洁的,她是无邪的,她不懂得女人的痛苦和挣扎,正是这种从她身上流露出天生的爱,使得被封闭在这里的女人不再直面死亡,而是直面爱之遗失和获得:小女孩靠近她们,四个人抱在一起,而娃娃成为了他们之中的第五个,于是在爱的抚慰中,女人闭上了眼睛,然后用手遮挡住自己的目光:当目光不再扩散,她们的世界里不再有他人,在解构了“他人即地狱”的宿命论之后,男人制造的困境将化为无,男人的封闭将变成自救的力量,男人说出“该死的女人”的诅咒将变成一种生,有自己的身体,有自己的双手,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爱,这就是自足的世界,而跳舞也变成了对于自我的另一种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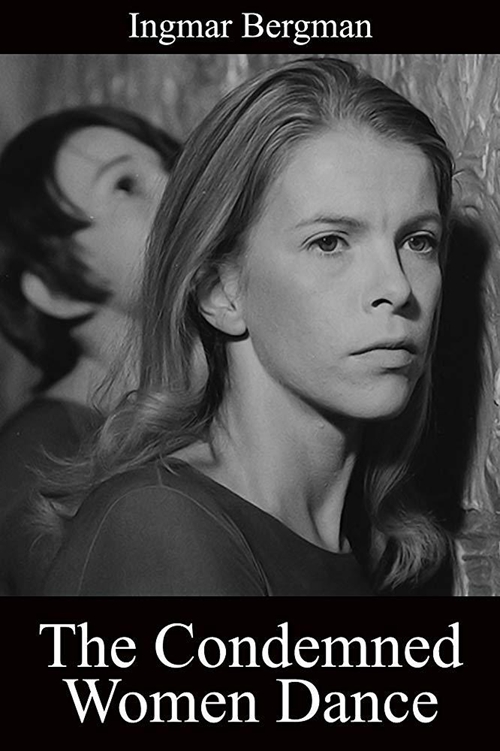
《该死的女人》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