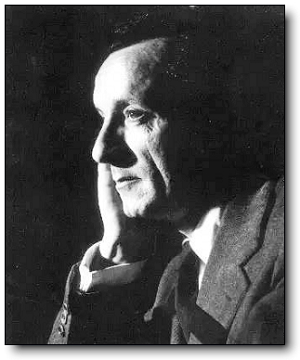2017-12-24 《行为的结构》:作为生命的意识被预设

假定一个眼睛被蒙住的被试者向后移动一定的距离,随后我们要求他再走向从前的地方,不管是正向走还是侧向走,不管是小步走还是大步走,他都成功地到达那里了。在这种情形下,是什么在安排和控制他的活动?我们如何表现其生理基质?
——《第一章 反射行为》
眼睛被蒙住,他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意味着取消了给定的物理空间,或者说暂时取消了一定的空间感,那么对于被试者来说,这就是某种刺激的产生,但是当刺激产生之后,反应如何获得,兴奋的位置如何找到,神经环路如何建立,一系列“如何”其实设置了一种可见者的系统,也就是在眼睛不被蒙住的情况下,被试者可以顺利从后退的位置走到原点,也就是轻易建立了反射行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失去了可见性,被试者还是“成功到达了那里”,在这个过程中,谁安排了他的行走轨迹,使得他像正常人一样建立起完整的反射系统。
梅洛-庞蒂的疑问并非仅仅是一种反应的秩序问题,在他看来,被蒙上眼睛的人找到原点并非是因为自己偷偷留下了视觉印记,也并非是一种理智在起作用,当被蒙住眼睛的被试者后退一定数量的步子之后,并非是实际产生的肌肉收缩中形成了活动的形式,而是在他的意识中留下了“数量”——作为整体的数量,包括步子的数量,方向的数量,而这些数量组成了一种“所经历的空间”,当这种整体被记录,而且必须被记录在“各个中枢”里的时候,他才能根据这些数量重新建立刺激,重新产生反应,重新获得位置,重新打通神经环路,最终成功走向终点。
“由于兴奋本身已经是一种反应,所以它不是从外部引入机体的一种效应,而是机体固有机能的最初行为。”这或者就是一种关键,因为被试者蒙上眼睛而后退,然后再回到原点,这种后退和前进的过程就是完成了一种预设,假如只是让被试者在蒙上眼睛之前看见到达目标的距离,然后再蒙上眼睛,这种兴奋和反应并不一定会“成功到达那里”,也就是说,他缺少一次从原点后退的体验,也就失去了“机体固有机能的最初行动”。这样的对比的意义在于为反应的发生寻找一个秩序问题,也就是在反射反应中,是不是存在一种“使它们能够合理地进行这些感受器替换的一般的东西”?当没有后退的被试者走向目标的时候,他的行为意味着刺激只是紫再德、独立于机体而获得界定,也就是刺激变成了一种纯粹物理的实在,尽管其中也有判断,也有推论,也有数量意识,但是这种刺激显然失去了其作为生理或生物的实在性。
而梅洛-庞蒂如此对比而提出的反应秩序,就是要把它引入到神经机能中,而且是作为整体的神经干预,而不仅仅是一种本能,一种理智活动,“任何器官反应都预设了兴奋的整体转化,这种整体转化给予每一兴奋以其并不独自拥有的属性。”而这种整体性就是赋予机体一种生命力量,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行为结构:“生物学的目标是把握使某一有生命之物成为一种有生命之物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基本反射的重叠或者某一“生命力量”的干预,而是行为的某种不可分解的结构。”被眼睛蒙住的被试者是梅洛-庞蒂对于反应行为的一种观察,而在整个反射行动中还涉及到刺激、反应的位置、反射环路等。对于反射,经典反射理论认为,“它是某一确定的物理动因或化学动因对于某一定位确定的感受器的作用,它通过某一确定的通道引起某一确定的反应。”这种理论在梅洛-庞蒂看来是一种“地形学”的观点:兴奋的位置决定了反应,而刺激必定通过其各种属性的反应而起作用,神经环路被隔离出来。
很明显,这样的反射是一种“纵向现象”,它是对于物理和生理事件的线性描述,刺激往往被当成因果律的原因,而是一种在经验论意义上恒常的、无条件地在先的东西,而机体则变成了一种被动的结果,也就是它只是“执行由兴奋位置和源自这里的神经环路为他规定的事情”,而且机体的被动性也使得关于意向、价值、效用的观念统统作为主观的东西予以抛弃,看起来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研究,而其实是否定了事物内在的规定性,机体的行为只是一种结果。
梅洛-庞蒂从反射行为本身入手,他的目的是为“纵向现象”寻找到另一种“横向现象”,也就是在反射行为中建立一种新的秩序。经典的反射理论把反射行为分解为因果律之下的线性过程,这在梅洛-庞蒂看来,是一种原子主义的理论,它是单一的,机械的,可分割的,甚至是动物意义上的。从反射的不同组成部分来分析,当刺激产生的时候,并非是机体只是成为刺激的结果,也并非是刺激的每一部分都有反应的某一部分与之对应,现实的情况是,当人拿着捕捉工具的手随着动物的每一次挣扎而活动时,机体并非是被动的,并非只是成为结果,而是参与了行为形式的构成,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动作回应外部刺激的同时,人也“借以使我的感受器受到那些刺激的影响的动作”而被自己感受到,也就是说,机体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刺激的原因,而这个观点韦赛克早就有了命名,他说:“机体是刺激的创造者。”也就是说,对象的属性和主体的意图是混杂在一起的,“而且还构成了一个新的整体”,而在梅洛-庞蒂看来,行为可以是环境的某种结果,但是它一定是“全部刺激的首要原因”。
在兴奋的位置中也是如此,当不同的反射发生时,并非只有与数量相等的“私有环路”相一致而取得了兴奋的位置,“而是代表了同一种神经器官的向机能的多种样式。”而神经的反射环路在化学条件、分泌条件、植物性条件的多元构建中,也使得反射器官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一条预先的环路到另一条环路也不再是简单的替换,而是在大脑影响的干预下,“为了重新组织行为,把行为提升到了一个高级的层次,生命的层次,而不仅仅是联合、瓦解预先建立起来的装置。”所以最后在反应行为中,被蒙着眼睛的被试者能够成功返回到原点,就是因为,“任何器官反应都预设了兴奋的整体转化,这种整体转化给予每一兴奋以其并不独自拥有的属性。”就如韦赛克在《反射规律》中所说:“反射运动的诸形式乃是生命的木偶戏……是机体在其站立、行走、格斗、飞翔、抓拿与吃喝时,在活动与繁衍中实现的各种运动的形象。”
经典反射理论的破产,就是线性因果律的破产,就是原子主义的破产,而梅洛-庞蒂建构的反射体系就是这样一种秩序:
我们必须把神经系统的传入区域看作力场,它同时表达了机体内部状态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力量根据一定的优先分布模式趋向于自我平衡,并且从身体的运动部分获得这一结果所特有的运动。随着这些运动的进行,它们引起了传入系统状态的某些改变,这些改变反过来又引起新的运动。这一动态循环过程确保了人们为了说明实际行为所必需的灵活调节。
| 编号:B83·2170516·1389 |
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反射行为,当人实施高级行为的时候,这样一种秩序又如何建立?梅洛-庞蒂从巴甫洛夫的反射学入手,考察了他的反射理论。巴甫洛夫在高级行动中的假设是:“机体中,一个复合刺激把每一基本刺激所引起的那些过程作为其实在部分包括在内,或者说,每一部位刺测激都拥有其自身的功效。”刺激变成了复合刺激,这是对于刺激的多元化观察的一个入口,也是走向行为科学意义的一种努力,但是梅洛-庞蒂认为,巴甫洛夫的复合刺激说,看起来是综合了刺激的各种原因,看见了产生反应的多元途径,但是,这显然是另一种偏见,因为他把整体兴奋看成是有没一部分的刺激所产生的兴奋的总和,也就是他建立的是个体和整体之间简单叠加的模式,而在行为分析上,他采用了心理学的假设来阐述生理学的观点,在梅洛-庞蒂看来,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生理学”,而且还有着明显的原子主义的影子。
梅洛-庞蒂从病理学的研究出发,寻找行为的“中枢区域”,这是对于原子主义“去中心化”的一种否定,而这种中枢区域就是将行为嵌入到身体而成为建立反射高级行为的“整体性机能”一个遗忘性失语症的患者,他丧失了命名的能力,也就失去了“物体和词语被理解为某个范畴”的能力,这种能力布和戈尔德斯坦称之为“范畴态度”,海德格尔称之为“符号表达”能力,沃尔康姆称之为“中介化功能”的缺陷,失去了这样的能力,患者是一个只剩下具体而直接的经验的人,但是他却并没有丧失词语,也就是说还能运用自动语言,在梅洛-庞蒂看来,他还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的行为“比正常人的行为更加密切地依附于环境中的某些具体而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病人的疾病不直接涉及行为的内容,却涉及到了它的结构,而疾病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被观察到的事物,而是被理解的事物,“因此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分析类型,它不再去孤立某些元素,而是要理解某一整体的状况及其内在法则。 ”
|
| 莫里斯·梅洛-庞蒂:身体真正成为人的身体 |
而这种整体状况及其内在法则就是要建立一种高级行为的中枢区域,某些行为依赖于中枢皮质,不是因为它们由某些在这里有其开关和驱动的相同的基本运动构成,“而是因为它们隶属于相同的结构,在相同的观念下被归类,处于相同的人性层次。”反射的高级行为真正所需要研究的不是结构中的行为,而是行为中的结构,而正是这种借助于整合和协调的概念,可以纠正原子主义。梅洛-庞蒂从空间知觉、颜色知觉和语言生理学的例子来验证整体性的重要性,而这种相互依赖,相互联合而形成的整体性,就是的行动具有了某种“自动性”,它的规律是:“只要刺激的前面一些元素被给出,它就把这一规律显现出来,就如某一曲调的那串起始音符确定了这个曲调整体的解决方式一样。”就像反射的产生一样,机体并不只是结果,它也是刺激的原因,就是在混杂中形成了整体性、自动性的行为结构。
梅洛-庞蒂把行为的形式分成三种,一种是本能意义上的混沌形式:“行为要么与情景的某些抽象方面联系在一起,要么受制于某些非常特殊的刺激的特定情结。”第二种是“可变动形式”:“其行为是以相对独立于它们在其中得以实现的那些质料的结构为基础的。”混沌形式体现的是行为的本能意义和信号意义,它们只是实现了一种从原因到结果的单向行为方式,而只有在“象征形式”出现之后,行为的结构才具有了一种开放性的整体。梅洛-庞蒂对于象征形式的注解是:“它把‘各种刺激’从我本身的视点所参与的那些实际关系中解放出来,从永久地被确定的那些种类需求所赋予给它们的功能值中解放出来。”一种解放,是关系的解放,是功能的解放,“随着象征形式,出现了这样一种行为:它为它自己表达刺激,它向真理、向事物本身的价值开放,它趋向于能指与所指、意向与意向所指的东西之间的相符。在这里,行为不再只是具有一种含义,它本身就是含义。”也就是说,行为不再属于一种自在秩序,而是属于自为秩序,在这种秩序里,行为的主体不是把自己的规范强塞给世界,而是成为“非现实化自己”,并且成为了“他我”,这种基于整体性协调能力上的交流变成了“反思”:“行为因此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也就是说,就如同所有其他对象一样,它是被思考之物,而非自在之物。这就是反思所告诉我们的。”
反思而为我思,自我而为他我,自在而为自为,“行为不是一个事物,但它更不是一个观念,它并不是某一纯粹意识的外壳。”很明显,当行为具有观念意义,具有自为特性,具有我思功能,实际上就是要突破行为的实体主义,也就是说,行为主体不再是一个单纯物理学的存在,也不是生物意义的存在,而是在物理场、生物场和心理场这三个行为所处的场建立辩证的物理秩序、生命秩序和人类秩序。物理学揭示了机体的“事实结构”,生物学揭示了“原则结构”,而将三者协调而构建的整体性中,机体的总体性变成了一种“现象”)——超越实体的现象,成为“现象身体”:“现象身体的各种身势和姿态应当有一种特定的结构,一种内在的意义,它一开始就应当成为向某个‘环境’衍射的各种活动的中心,成为一种物理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轮廓,成为一种特起的行为类型。”
内在意义是作为生命意识的意义,“我们在生命的名义下指明的东西就是生命意识。”而意识只有一种“作为观念的处所所预设”的意识,才能将生存的整体被关联起来。意识作为预设,那么人的知觉意识在心身关系中保持怎样的地位,一种观点认为,被知觉对象的生理表象是必然地被置于大脑中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实在论的态度,梅洛-庞蒂认为,这只不是一种科学中的伪笛卡尔主义,因为就像实在论对于因果律的困难一样,那种必然性、内在性的知觉是强硬塞进人的自然结构中,“在这个世界中勾勒出人的身体并最终引入心灵。”而真正的笛卡尔式分析,应该是回到对于人的经验的清算和描述,首先应该去除在外部对它进行说明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以素朴意识通达“事物”,从而构建知觉意识这个预设的全部意义。笛卡尔在心灵中让上帝成为世界联结的中心,而借助于笛卡尔式的分析,梅洛-庞蒂则把意识看成是那个中心,这是意识的一种意义,“意识似乎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世界的中心,为所有关于世界的断言所预设,另一方面它又受到世界的制约。”被世界制约就是作为世界的外延而出现,这是梅洛-庞蒂对于行为结构的一种革新意义,“有深度的不是含义的观念而是结构的观念,是一种观念与一种存在的难以觉察的结合,是质料借以在我们面前开始拥有一个意义的偶然安排,是处于诞生状态中的可知性。”而作为构成对象之一的身体,自然被整合到客观世界之中,而且,身体之存在,梅洛-庞蒂赋予了身体一种生命属性,“丧失了意义的身体很快就不再是活的身体,以至于重新回复到一堆物理-化学物的状态中,它不过是在垂死状态下通向了无意义。”这种身体意义也是超越实体而成为“现象”。
从反射寻找行为的形式,从形式研究行为的结构,当意识是现象的意识,当身体是现象的身体,梅洛-庞蒂的整体性世界就是要抛弃把“心理”看成是实在世界的唯物论,抛弃把意识当成生产性原因的唯灵论,抛弃把机体的行为分解为彼此独立线性结构的原子主义,抛弃把心灵塞进身体的伪笛卡尔主义,“我们的目标是理解意识与有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自然的关系。我们在此把自然理解为彼此外在并且通过因果关系联接起来的众多事件。”行为的结构是联结,是协调,是自为,是人之为人的整体性,“在这一情形中,身体机能被整合到了一种比生命层次更高的层次,于是身体真正成为了人的身体。”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798]
思前: 《想起了你》:世界如一场幻觉
顾后: 《通货膨胀》:非经济的技术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