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11《烽火岁月志》:为有牺牲多壮志

最后的字幕:“1962年7月5日,阿尔及利亚在牺牲了一百多万烈士之后,获得了独立。”这是电影呈现的最后结果,如果说独立是目的,那么争取独立的漫长历史则是过程,如果说独立是胜利,那么牺牲的一百多万人则是英雄,作为非洲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电影,穆罕默德·拉赫达尔-哈米纳呈现的“烽火岁月志”就是对这一漫长的历史的书写,就是对一百万牺牲者的颂歌,而在西方世界获奖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种电影史上的“独立宣言”,但是从过程到结果所书写的“烽火岁月志”,在史诗般的呈现中,却也导致了一种虎头蛇尾的结构毛病。
哈米纳1934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曾到捷克斯洛伐克接受电影学习,回国后开始执导电影,1966年导演了电影《奥雷斯山上的风》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9年之后的这部《烽火岁月志》摘得了金棕榈奖,他也由此成为了非洲电影的杰出代表,在其二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一共执导了6部电影,前后获得过四次金棕榈奖提名,1986年随着电影《最后的画面》拍摄完成,哈米纳的电影事业也画上了句号,2025年5月去世。可以看出,哈米纳接受了欧洲电影的理念,学习了西方电影的手法,他又将这些理念和手法运用到表现阿尔及利亚民族性的故事中,而这些电影又相继亮相戛纳电影节,摘取了金棕榈奖,获得了西方社会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哈米纳就是将西方电影技术和艺术为我所用,从而在民族电影的事业上树立起了标杆——《烽火岁月志》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成为如何走向独立自主的影像化表达。
但是对于这片土地来说,从苦难、贫穷、受到压迫的现实中找到出路,远比电影所呈现的要复杂,“烽火岁月志”以史志的方式贡献了一部沉甸甸的文本,电影分为六个章节:灰烬的岁月、推车的岁月、余烬的岁月、大屠杀的岁月、烈火的岁月和“1954年11月11日”——最后一个章节定格在具体的历史时间,和电影最后的字幕表现的结果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而前面五个章节形成的“前奏”则是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所遭受的苦难。《灰烬的岁月》引出的是干旱问题,阿尔及利亚的小村子遭受了干旱,艾哈迈德和村里人一起参加了祈雨仪式,他们呼唤真主能保佑这片土地,但是即使天上布满了乌云,坚守了一天一夜的人们还是没能迎来降雨,土地干裂、牲畜死亡、粮食无收,有人发现了一些泥水,但是人们聚集在那里最终还发生了争斗。终于天下起了雨,人们欢呼,人们狂喜,虽然还有争斗,但充沛的风雨还是给了人们足够的希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们再次遭受了干旱,面对颗粒无收的庄稼,艾哈迈德终于决定离开这片土地,酋长和村民恳求他不要离开,因为离开意味着切断了和祖先的脐带,执意离开的艾哈迈德对他们说的是:“我受够了这一切。”
| 导演: 穆罕默德·拉赫达尔-哈米纳 |
以《灰烬的岁月》开篇,哈米纳所呈现的苦难是干旱,这是人和大地之间共存关系的破裂,这是人和上天依附关系的解体,这甚至是人了祖先血脉关系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段岁月所反映的是自然强加于人的一种苦难。而随着艾哈迈德带着家人来到城里投靠表哥,自然所带来的苦难也变成了社会意义上的苦难,《推车的岁月》所表现的就是战火所笼罩下的阿尔及利亚,它是法国的殖民地,而纳粹德国正在占领法国,作为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也笼罩在战火的阴霾中——而且并不仅仅是战争的威胁,还有殖民者对他们的压迫。艾哈迈德和表哥在采盐场工作,孩子给艾哈迈德送来饭餐,只是因为艾哈迈德坐在采盐的石头上,就被白人工头毒打;表哥在干活时中暑,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助最后活活死去;城里发生了伤寒疫情,城市各个出口因为防疫要求而被封锁,疫情在蔓延,大街小巷堆满了尸体,艾哈迈德的孩子也被感染,他抱着孩子去找防疫点的医生,由于缺医少药,医护人员根本顾及不过来,艾哈迈德偷偷拿了一包药,当他踩着尸体逃离,眼前早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这一“岁月”中,哈米纳的叙事采用了一种并置结构,“疯子”米洛是整部电影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在艾哈迈德从村里来到城市的时候,米洛就站在城门外的墓地里,“这个世界上唯一安全的就是墓地,看看这个天堂吧……”当城市里的人成批死去,他又在那里高喊:“没有活着的邻居,他们都被扔进了共同的坟墓。”米洛是一个疯子,或者正是在这种苦难的岁月里,他才是最清醒的:现实不是天堂是地狱,而真正的墓地却是死者的天堂。当传来战争的消息,当局开始征召阿尔及利亚人进入战场,一边是被迫服兵役的士兵在列队训练,另一边则是米洛在墓地里指挥着死去的“幽灵”,它们构成了并置关系,而这种并置关系强化的正是人间地狱化的惨状。而艾哈迈德也在目睹了苦难之后,从离开土地的自觉变成了争取权力的自由,当再次遭遇干旱,当人们再次因为水而发生争斗,艾哈迈德站在两列队伍面前,“难道我们还要为殖民者留给我们的那滴水而流血吗?”因为干旱而抢夺水源,这和“灰烬的岁月”所呈现的矛盾一样,但是艾哈迈德却已经在苦难中得到了成长,这不再是和水有关的斗争,这是殖民者压迫人而导致的流血,从水到血,以艾哈迈德为代表的阿尔及利亚人开始觉醒,但是这种觉醒依然遭到了镇压,哈米纳再次呈现出一种并置结构:当二战走向尾声,德国纳粹变成了战俘,他们被押上了列车,而艾哈迈德因为煽动阿尔及利亚人闹事甚至炸开了水闸而被拘捕,他也被押上了同一辆列车,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牢狱生活,当德国俘虏和阿尔及利亚“犯人”押上同一辆车,这种并置正是和米洛指挥幽灵具有同样的效果:对法国殖民者的一种巨大讽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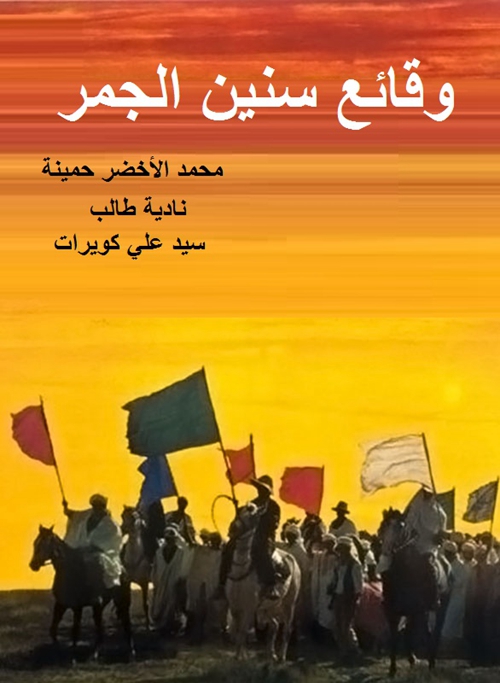
《烽火岁月志》电影海报
当艾哈迈德从监狱中出来,进入的是“余烬的岁月”,“余烬的岁月”和“灰烬的岁月”似乎没有区别,它们所呈现的就是战后阿尔及利亚更深重的苦难,侵略者被赶走了,但是殖民者还在,殖民者所扶持的当地统治者还在,正如米洛所说:“活着的人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仍然是迷途的羔羊。”而已经在苦难中醒来走向自觉的艾哈迈德也遭遇到了新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流放者拉尔比来到了小镇,他每天去警察局报道,因为他是一个假释犯,而他的出现代表着阿尔及利亚的战斗进入了新阶段,可以说阿拉比代表的就是革命者,他召集镇上的人,提出了革命的目标:不是和当局者进行谈判,而是要进行武装暴动,也由此,烽火岁月志进入到了“大屠杀岁月”。在阿拉比揭穿了当局投票选举的丑闻之后,在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点之后,在开始武装暴动之后,阿拉比被射杀,而当局更是实施了残酷的镇压,在广场上他们骑着战马挥舞着战刀,向革命者和无辜者砍去,鲜血染红了广场。
如果说贫穷、苦难导致的是普通百姓的死亡,那么在对抗殖民者的斗争中死亡就变成了牺牲,而面对牺牲,艾哈迈德也再次成为自觉的反抗者,他扑到了骑兵,他挥起了战刀,他砍杀了殖民者,而其他人也在他的感召下进行了反抗,镇压者和反抗者的尸体堆满了广场,“大屠杀岁月”既是一段血腥的岁月,也是让死亡变成牺牲的岁月。从自觉到自由,从死亡到牺牲,阿尔及利亚革命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烈火岁月”。但是这段本应该是艾哈迈德在烈火中燃烧的故事,这段应该从个体的反抗变成群体的解放的叙事,哈米纳却反其道而行之,让“艾哈迈德”成为了一个虚设的符号,而“疯子”米洛则成为了叙事的主角,他带着艾哈迈德的孩子跋涉千里,寻找已经成为革命者的艾哈迈德,并最终在革命者藏身的山谷中找到了“艾哈迈德”,只不过一场战斗刚刚结束,艾哈迈德为了掩护同志而牺牲,枪声没有消失,屋子门口留着一摊鲜血,那就是艾哈迈德的鲜血。在这里艾哈迈德没有现身,他的革命故事也没有在镜头中表现,但是当孩子面对鲜血面对父亲的英勇事迹,默默流泪,也在内心得到了革命的教育,他将成为阿尔及利亚新的战士。
哈米纳在这里把具体且个体的艾哈迈德变成了一种更广泛意义的象征符号,他既是孩子的父亲,也是革命的“父亲”,他既让孩子得到了成长,也激励了更多的革命者,唤醒了更多沉睡着的民众,这也许就是“烈火岁月”具有的意义。但是这种“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叙事却让“烽火岁月志”逐渐变成了一种意象的传达,在众多的“岁月”构筑的苦难志、反抗志、革命志之后,直接迎来了“1954年11月11日”,这是革命纪念碑的落成仪式,但是殖民者并没有离开,“英雄归于法国”的背后依然是没有独立的阿尔及利亚,而对于接下来的革命斗争,在具体的艾哈迈德缺席、“艾哈迈德”只是成为一种象征的时候,哈米纳通过米洛传达出继续革命的理念:“愿主保佑赐予我的疯狂,这疯狂比犁铧还锋利,锈迹和岁月都不能被玷污,我承受这痛苦是有福的,它的火焰在千家万户燃烧……”
从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苦难者,到具有反抗精神的革命者,从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个体,到汇聚成洪流的群体,从岁月中不断成长的觉醒者,到唤醒更多人的牺牲者,哈米纳的“烽火岁月志”所完成的是不断升级的革命叙事,最后精神的传达取代了叙事,有血有肉的形象也被象征符号所代替,于是历史直接进入了被归档的总结:“1962年7月5日,阿尔及利亚在牺牲了一百多万烈士之后,获得了独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