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24《迷影》:创发一种观看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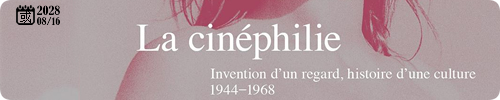
充满挑衅意图的哈里特·安德松手里拿着烟,双眼炯炯有神地攫住了摄影机的——同时也是观众的和男性的——目光长达25秒之久,直到她仿佛是在对眼前的一切掷出这句震耳欲聋却又沉默无声的诘问:“你们凭什么审判我?”
——《第八章 恋女与恋影》
披散着头发,微闭着双眼,一种享受阳光的表情,以及解开两个纽扣的上衣,露出右侧的肩膀,呼之欲出的身体半掩着。图书的封面,是柏格曼的电影《不良少女莫妮卡》的剧照,演员哈里特·安德森的手上没有拿着烟,目光也没有朝向摄像机,更无法想象她发出的那句诘问:“你们凭什么审判我?”安托万·德巴克引用的那个镜头和图书封面的剧照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带来的是关于“观看”的两种面向:当安德森在图书封面上微闭着双眼,她是被看的对象,就像《不良少女莫妮卡》这部电影一样,提供了观众看的内容,微闭拒绝了她对摄像机和男性的看,仅仅是被看;但是,当安德森在德巴克的引用中以“目光炯炯”的方式攫住摄像机和男性的目光,她是在被看的时候同时进行了“观看”,而观看之后发出的诘问更是指向了观看的对象,由此,被看和“观看”构成了一个互逆的过程,它构成了德巴克所叙述的“迷影”的双重结构。
柏格曼镜头下的不良少女莫妮卡,莫妮卡的扮演者安德森,安德森在展示身体之后透过屏幕的目光,巴德克把它们看成是“迷影情色症”的一个标本,它是电影中的女性,它是女性的身体,它是被看见的影像,“对一个影迷而言,这些跟女性有关的东西,最终都将变为其欲求的对象:他既收藏它们,也交易它们,他日思夜想的都是它们,甚至还跟它们发展出恋爱的关系。”而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影迷燃烧崇拜电影的欲望之火的鼎盛期里”,巴德克将其看成是“恋物的要件”——“莫妮卡”安德森只是其中之一。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好莱坞电影的发展,玛丽莲·梦露可以说是进入影迷视线并成为迷影观看的第一个身体,《飞瀑怒潮》中玛丽莲的“赤裸”之身成为法国电影圈中被观看的情色标本,这个标本既是理想女性的神话,也是堕落的象征,它以“过剩的身体和过剩的真实”体现了堕落自身的视线途经。但是玛丽莲的电影和身体对于法国迷影世界来说,毕竟是一种异域的存在,它是好莱坞的代表,但是当柏格曼在《不良少女莫妮卡》中让安德森“裸体”展现,法国观众第一次以内视的方式发现了欧洲的身体。
“伯格曼确实走得很远,这是影史上破天荒头一次有一部片能够如此公然地展现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极度自信的女人,不仅如此,她对目身的裸露、情欲及其对男人的影响力,同样非常有把握。”实际上,《不良少女莫妮卡》并不是在电影的地域空间中开创了恋物的时代,它更是将看和被看推向了一种双重构建的阶段:一方面,“莫妮卡”的身体公然展现在观众的视线里,它是被看的内容,它是情色的投影,甚至巴德克将其命名为“解放”的标志物,“鉴于莫妮卡是银幕上第一个从明星恋物传统中获得解放的女性形象,她的出现,乃影史上现代女性首度被创发出来的时刻。”而另一方面,当“莫妮卡”的身体被看,最后一个镜头里目光炯炯的她对着摄像机长达25秒,这25秒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你们凭什么审判我”的无声诘问变成了“莫妮卡”对观众的欲望、对欧洲电影的审视、对法国电影审查制度的一次观看——不仅“莫妮卡”的被看见是“首度被创发出来的时刻”,她看见摄像机和男性目光的25秒同样是一个开端,看和被看构成了巴德克“解放身体”的双重叙事。
正是由于有了首度和开端,“恋女和恋影”的第三个标志出现了,“这个事件指的是1956年12月碧姬·芭铎的横空出世。”碧姬·芭铎从《上帝创造女人》的第一个镜头就开始裸露,这种裸露构成的事件是:导演在此展示的是一副如假包换的身体。当碧姬·芭铎频频在新浪潮电影中出现,甚至给为《艺术》和《电影手册》的“青年土耳其人”给“认养”了,巴德克认为,“在她身上,他们势必看到了当下世界的脉动:真实至上的时代氛围越发无法接受那些由巴黎片厂所推出的电影。”这是一种发现,它具有的意义在于,碧姬·芭铎让他们看到了一副“现代的身体”:它以反常规的方式叙述了身体语言,同时电影对其自身特性的展示打破了法国电影的传统品质——那些一向追求文学改编、戏服传统、心理刻画、“优良”演技、“华美”布光或以主题为重的法国电影,在碧姬·芭铎的“现代的身体”面前,的的确确变成了只是看的伪电影。
玛丽莲来自异域的身体代表的是“美国的身体”,“莫妮卡”则开创了看与被看双重构建的“解放的身体”,而碧姬·芭铎对传统的解构构建的事一个“现代的身体”,三个女人,三种身体,在“恋女与恋影”中书写的迷影情色症其实正代表着迷影的三个阶段、三种方法,“这些令人捉摸不透的女性,凭借自身那复杂、晦涩,甚或是古怪的特性,为新浪潮电影带来了现代性的面向。”它甚至在形式实验上形成了电影的“千面镜”,“就新女性的身体而言,这副身体乃其母体,而从恋物的角度来看,它则是激起了另一种男性的欲望。”身体被打开,身体被看见,身体也在看见,迷影的这面“千面镜”也成为巴德克对于电影文化史书写的一种“观看方法”。在《绪论》中,巴德克把“迷影”就定义为“一种观看方法的创发”,“迷影”首先是一种态度,是对电影的极致之爱,从影迷变为“迷影”就是这种极致之爱的表达;迷影当然也是一种行动,它是在观看之后对崇拜对象的一种私密性行动,或者通过文字作品表达,或者在推崇电影中推崇导演;私密的迷影最终会成为公开的迷影,这是迷影群体性的构建,在深度的阐释中,漆黑的放映厅甚至变成了“礼拜堂”——从态度到行动,从私密性到群体性,巴德克由此提出了对迷影的研究将纳入到“电影文化史”的范畴,“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便是要将电影重新引入史学研究的领域,盼能借此重新发现原始资料的实质性,甚至是一种观看的愉悦感。”
电影文化史,在巴德克看来其实是电影断代史,1944-1968是这段历史的生卒年份:从德国占领期间法国影院里茁壮成长开始,到1968年“五月风暴”中在政治的震荡中四分五裂并最终烟消云散。不管是对迷影的定义,还是对迷影历史的界定,巴德克对于迷影最重要的部分并不在于此,他认为迷影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精神,那就是“创发”,一方面创发的对象是那些让他们爱到疯狂的电影,“他们对这种电影的拥护有时甚至接近盲目。”另一方面,“创发”具有一种创造的能动性,他们创发的其实是“日后终将实际拍出来的那种电影”,比如戈达尔、特吕弗、侯麦,身为“青年土耳其人”的主要代表,又是新浪潮的主要旗手,他们曾是迷影的代表,他们也是电影的导演。而不管是对已经完成的电影疯狂的爱,还是对将要拍出的电影的无比激情,巴德克认为,“创发”问世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观看”:“学会了去看一些通过自身人物最终学会了到底该怎么去看的电影。”在这里,观看就是一个双重构建的过程:它是看,看电影,看正在上映的电影,正在看电影;它也是被看,在看的过程为他人之看留下位置,在他人之看中让自己看见,看建立了目标,被看容纳了内容,“说到底,学会如何看,究其本质,即在创造某种看的方式。”
| 编号:Y23·2220919·1869 |
看与被看双重构建阐述的是关于观看的“创发”方式,巴德克对于这个方法论的书写,其实回到“恋女与恋影”就是提供了三种视角:玛丽莲所展现的是“美国的身体”,它所创发的是对于异域影像的观看;“莫妮卡”所代表的是“解放”的身体,它是法国电影对于自身的审视和突围;碧姬·芭铎所投影的是“现代的身体”,它指向了法国电影的现代化选择。三种身体其实是三个文本,三种态度,三个阶段,巴德克正是通过对法国迷影三个不同“身体文本”的阐述,书写了1944-1968的“电影文化史”。第一个阶段是对以“美国的身体”为代表的异域电影的观看,1946年7月10日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在巴黎马尔伯夫影院公映,由此引发的争论是迷影观看的第一个事件。而实际上早在1945年萨特就对这部电影发表了评论,他对片中过度“文学化”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叙事导致了“过度做作的视角”,偏离了美国经典电影所具有的简单、明了的特质,萨特的批评反映的是“萨特式的艺术”,即“电影是解放人类意识的最佳模式”。当两年后这部电影在巴黎上映,身为《电影手册》的核心,安德烈·巴赞却聚焦电影的本体论上,他认为电影既不是写作也不是描绘,“它仅仅是去呈现”,这是电影真正的力量,也是电影真理之所在——巴赞的观点是对电影作为“庶民教育”奠基磐石理论和实践的一次延伸。
无疑,1947年关于《公民凯恩》的争论,是法国迷影对异域身体文本的一次交锋,巴德克直截了当指出,“尽管在这次对垒中,没有一方是真正的赢家,但那条将电影文化一分为二的裂痕却就此产生。”一分为二就是关于美国电影的态度,或者反对,或者用户,最终形成的是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巴赞在电影的“观看”,主要强调电影的基础是写实主义,“唯有在记录真实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出其绝对的真理。”巴德克把安德烈·巴赞称为“一个戴天鹅绒鸭舌帽的圣徒”,对于“新浪潮”和青年土耳其人以及迷影圈来说,他就是精神之父,而他和萨特的论战作为“观看”的第一个标志事件,也开启了对异域电影的审视。美国好莱坞之外,是乔治·萨杜尔代表的“法国的斯大林电影”,作为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认为,“苏联电影在斯大林的全力推动下,已然走在重生的道路上,不久后肯定就能再次获得人们的青睐。”讨厌好莱坞电影拥护斯大林电影,萨杜尔甚至勾勒出了“三个黄金时代”,他在《法国文学》发表电影评论后来甚至变成了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当然他的个人崇拜也遭到了巴赞的反对,巴赞发表《苏联电影中的斯大林神话》,“以一种绝不妥协的姿态去破译战后苏联电影中那种理想化斯大林个人魅力的机制之运作方式”——双方的论战引发了“法国电影界的斯大林危机”,但是后来的萨杜尔以吊诡的方式实现了转变,他最终成为了法国新浪潮的重要推手。
“希区柯克事件”是法国迷影史上另一个重要事件,戈达尔捍卫希区柯克,他把巴赞的理论运用到希区柯克身上,“从戈达尔的论述来看,希区柯克确实独一无二,因为在他身上,标榜风格化的表现主义和攸关场面调度以及演员表演的写实主义竟能彼此结合在一起。”对戈达尔发起反击的是皮埃尔·卡斯特,而青年土耳其人对戈达尔的支持使得重心发生了偏移,从而得出了一个彻底革新过的电影观念:作者的思想能借着“场面调度”而在电影中逐渐成形,戈达尔认为,“化身成形的思想/懂得思考的形式”构成了一部影片绝对的美。巴德克认为,“希区柯克事件”所争论的是希区柯克的场面调度问题,虽然还是对好莱坞叙事的一种审视,但是已经对法国电影产生了一种本体论的抉择,“这个观念抛弃了过去那种二元论原则,代之以一种充满原创性的主张:一部影片的内容,即是它的形式。”希区柯克路线“是以一种唯灵论的电影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创了一系列的“宗教电影”,青年土耳其人以及新浪潮最后在这场论战中胜出,以特吕弗为代表的青年影评人从此走上了从看到被看、从迷影到创作电影的转变之路。
1954年特吕弗在《电影手册》第31期上发表《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这篇长达15页的文章“以一种无人能及的雄健笔锋将发生在电影这门艺术中的断裂期给勾勒了出来”,断裂的一端是法国的电影传统,特吕弗将其并以为以前自己一篇文章的标题:并不存在法国电影;断裂的另一端则是法国新浪潮,新浪潮抹去法国电影的传统,特吕弗则完成了“疯狂一击”,甚至开始了“夺权”,“这位骨子里早已是个电影导演的小伙子,赋予了影评人某种绝对的创造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各种观物方式、各种电影流派以及各种品味的观众可以持续不断地接力下去,是它,让重新书写电影史不再只是不可能。”这无疑是特吕弗对“解放的身体”的一次观看,而在这个时期,“法国迷影文化中的富勒式危机”发生,这个危机审视的事法国电影禁片体制;同时还有以《正片》为阵地的罗歇·泰耶尔,在“能够歌咏影像”的书写方式中受到了思想和体制的钳制;贝尔纳·多尔特作为“左派的希区柯克-霍克斯主义者”,以布莱希特主义甚至过多的政治色彩,站在了青年土耳其人的对面,德巴克将其最终被遗忘的原因归结为,“不外乎是他有时甘愿将自己禁锢在一种孤绝的处境中”。
从对异域身体的审视,到对解放的身体的站位,法国迷影史的这两个阶段反映的就是一种观看方式的转变:属于对对象的观看如何走向创发的阶段?而这个问题就归结为一点:如何书写“现代的身体”?这个问题在50年代末至1966年,关涉的是《电影手册》现代之路的选择:埃里克·侯麦和雅克·里维特之间的对峙,也是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侯麦的古典主义,即那种可望复苏好莱坞电影的古典主义,是他被迫纳入自己的万神殿的那场新浪潮运动的前景,里维特则将赌注押在欧洲电影的先锋势力上。之后新浪潮的“新电影”的横空出世,各大电影节出现的革新精神,《手册》影评人打垮黄色封面时期的古典理论工具,这一系列行动就是打开了观看的另一个进口,“《电影手册》,以及法国迷影圈的一大部分,已然开始与大时代的脉动同步了。”但是在这个选择之路上,迷影最终从朗格卢瓦事件走向了一种对于观看的迷失——1966年雅克·里维特根据狄德罗小说《修女》改编的同名电影遭到了禁映,法国电影的审查制度已经不仅仅针对电影本身,它构成了对文化自由的一种戕害,“对影迷而言,该事件同时是个警讯:是否到了该从影院出走的时候?是否该停止继续对黑暗中那些光影运动的迷恋?是否该到外头的世界去看看,并学着与时俱进?”两年后发生了朗格卢瓦事件,并最终成为了“五月风暴”,战斗开始了,另一个时代也由此开启:“电影介入政治事务从此成了家常便饭,观影群体和电影类型纷纷走向碎片化,然后,是电视的大获全胜。”
政治性觉醒对于电影来说,其实是一种对于“现代的身体”的无情阻止,迷影也最终选择了出走,巴德克认为,正是1966年的出走,这段“电影文化史”画上了句号,而伤感的是,看与被看,私人之看和群体之看,争论之看和创发之看最终只剩下了“迷影精神”,它们在电视和广告的侵袭中已经支离破碎。但是当德巴克还把“迷影精神”当做一种永恒存在,当德巴克对政治以及电视和广告进行批判,于他内心来说,迷影的“创发”没有完全消逝,究其本源来说,这就是对电影的爱,即使“全影像”代替了电影,即使“新观者”取代了迷影圈的观者,但是如“莫妮卡”面对镜头发出的诘问,关于电影:“你们凭什么扼杀我?”德巴克为迷影留下了最后的创发位置,“迷影作为宿命,他将披星戴月,坚韧不渝,至死不言休。”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987]
思前:《她说》:说他,说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