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10《荷尔德林之狂》:这是生命纯粹的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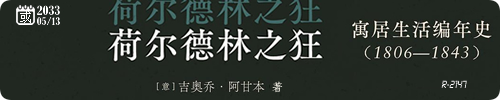
在我们的作品中,使用编年史这种文学形式具有额外的意义。正如《半生》一诗的标题所预言的那样,他的一生被一分为二:前36年,从1770年到1806年;后36年,从1807年到1843年,他像个疯子一样躲在木匠恩斯特·齐默尔的家里。
——《槛》
从1770年出生到1806年6月被送到图宾根的奥腾里特教授诊所,一共是36年;从1807年5月3日从奥滕里特的诊所出院住到木匠恩斯特·齐默尔家中,到1843年6月7日晚“轻轻地、平静地死去了”,也是36年,荷尔德林生命就这样整齐地被一分为二,与前半生在更广阔的世界四处游荡、关心外界和时事相比,后半生的36年,荷尔德林在内卡河塔楼里过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吉奥乔称之为“像个疯子一样”的生活,为什么阿甘本会选择后半生的36年作为“编年史”的样本而不是荷尔德林一生?
一分为二既是荷尔德林人生经历的自然划分,也是阿甘本对于历史书写的一种人为分段,而这就涉及到“编年史”被赋予的“额外的意义”。副标题是“寓居生活编年史”,阿甘本在这里的命名就涉及到荷尔德林后36年人生具有的两种特殊面向:寓居生活和编年史记录。他在书的“槛”中阐述了编年史记录具有的特殊意义——“槛”是门槛,它既是一个分界线,区别了内部和外部,但也意味着不内不外的悬搁状态,阿甘本在哲学研究中所感兴趣的正是这个具有典型悖论性的区域:既是区分也是悬搁,它就是我们特殊经验的所在。而阿甘本对于“荷尔德林之狂”的分析,也是这一特殊经验的注解。本雅明在《将故事的人》中区别了历史学家和编年史作者,历史学家把人物相关的事件看作和历史潮流相联系的某种“印记”,这一印记在历史潮流中才具有意义,所以他们会核实每一种资料的来源,会对事件进行解释。而编年史作者则把历史事件的叙述建立在“玄妙莫测的天意设计”中,他们提供的解释也不是和具体事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它们嵌入到这一天意设计中,或者这种看起来是天意的设计,恰恰是放弃了对可验证的解释,“对编年史作者来说,世界大事是由天意决定还是纯属自然并无二致。”
当然,编年史坐着并不是叙述自然而然的事件,在阿甘本看来实在质疑一种历史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在政治史和自然史之间,编年史作者插入了第三种历史,这种历史似乎既不存在于天堂,也不存在于尘世,而是近距离地观察这两者。”所以和历史学家相比,编年史坐着既不编造任何东西,也不需要核实资料来源的真实性,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用口述的方式记录——包括他们自己的声音,偶然听到的声音。声音构成了“口述”,口述抛弃了语言的定义和概括,在这个意义上,编年史所书写的就是关于生命的主旨,它是不解释的记录,它是不伪装的真实,它是不求证的自然,它所体现的就是把特定的生命看做是一个“人物形象”,只有这样,生命构成的情节才会归为,“并以其偶然的真实性一一显现,这意味着它们放弃了能够提供该生命真相的任何伪装。”而荷尔德林在后36年的塔楼生活就是对“真理形象性的最坚定的验证”,就是在放弃认识中保持它的原生态和未加修饰的认识可能。
但是阿甘本并没有给编年史一种完美的意义呈现,尤其在真实性上,他认为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无论如何,编年史的真实性最终将取决于它与历史上的编年史之间的张力,这让我们永远无法对编年史进行归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只是作为编年史作者给了一种呈现“人物形象”的可能性,“编年史是否比历史更真实,以及真实到什么程度,读者可以自行决定。”那么,阿甘本的编年史是不是讲述了关于荷尔德林的“第三种历史”?在1806-1843的“编年史”中,荷尔德林有一个特殊的处理方式,即1806-1809年的四年,他除了记录了和荷尔德林的“声音”之外,还将历史大事年表以及歌德的生平并置,比如1806年的历史事件有1月法国废除革命历、7月莱茵王公联盟成立、8月普鲁士国王与俄国英国结盟向法国宣战、11月战败的普鲁士和法国签订停战协定;比如摘录了歌德观看《歌剧世家》的日记、与黑格尔的通信、给路登教授通信谈及《浮士德》悲剧的意义……很明显,阿甘本引入历史大事年表和歌德生平,就在于为荷尔德林的编年史提供历史背景:7月莱茵王公联盟成立意味着荷尔德林居住的小邦洪堡被并入了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荷尔德林的朋友辛克莱尔由此担心自己会失去为侯爵服务的职位,8月3日,他给荷尔德林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要求她将儿子送回纽廷根;而在9月11日的时候,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的公爵夫人卡洛琳给她的女儿写信中就说到了荷尔德林被送走的情况,“他竭力想从马车上跳下来,但照顾他的人把他推了回去。荷尔德林大叫着,挣扎着,抓伤了那个人;由于他的指甲太长,那个人浑身是血。”而歌德的生平更多体现了他在战争中的担忧,当10月法国军队洗劫了魏玛,歌德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月里,都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对自己的个人、法律和财务状况作出了新的安排。
可以说,并置的历史年表提供了一种宏大的“德国历史”,而歌德的日记则提供了和歌德同样对德国民族进行书写的荷尔德林可能的命运遭遇,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的并置就是为荷尔德林的“编年史”提供历史的“声音”,这些历史的声音让编年史有了自己发声的外部条件。但是奇怪的是从1809年之后这种并置被取消了,从1809年至1843年的34年编年史都成为荷尔德林单向的声音,对此阿甘本在“序”中给出了一个理由,“我选择不将这一历史年表延伸至1809年以后,因为在我看来,与荷尔德林的居住生活并列的模式已经足够。”也就是说,在1809年之后荷尔德林自己的生活也足以构成完整的编年史真实的“声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前面的并置似乎也没有多少必要。而从1809年之后,阿甘本通过荷尔德林写给母亲的信件、留下来的诗作,以及他人对荷尔德林生活的描述,呈现出一部关于多声部的编年史,这也正体现了他所说不做解释、不去求真、不需伪装的真实,也在原生态中接近了荷尔德林的“人物形象”。但是,这样一份编年史所记录的作为人物形象的生命,是不是就能阐述“荷尔德林之狂”具有的意义?
| 编号:B89·2250705·2324 |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应该从阿甘本的“尾声”中找到答案,而这篇“尾声”所阐述的正是副标题所揭示的特殊面向:寓居生活。什么是“寓居生活”?阿甘本从词源学进行分析,“寓居生活”就是按照习惯去生活,其中的德语动词wohnen意思是“渴望”“努力”,它和德语中的“幻想”“喜悦”以及拉丁文中的“爱”有关,所以阿甘本认为在德语中,习惯的“养成”在词源学中和快乐、喜悦有关,幻想和疯狂也和快乐、喜悦有关,这就回到了“赫尔德林之狂”的阐述之中,荷尔德林之狂其实就是一种在寓居中的快乐和喜悦:荷尔德林的很多诗作都使用了“寓居”,而这种寓居就是荷尔德林的一个短语,为其写作传记的魏布林格曾抄录下来,后来海德格尔将其阐述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阿甘本看来,荷尔德林后36年的寓居生活正是一种“诗意的栖居”,一种在疯狂中追求快乐和喜悦的生活,“人不能成为自己或拥有自己,他们只能居住在自己的地方。”
除了荷尔德林在前36年的诗作中写道了“寓居”之外,后36年的生活更强烈地体现出“诗意的栖居”:1843年1月,乌兰特和日耳曼学家阿德尔贝特·凯勒,以及克里斯托夫·施瓦布拜访了诗人,他们发现诗人“满足而宁静”,荷尔德林为他们写了一首关于冬天的诗,其中有“美丽的意象和思怨”,但是“缺乏连贯性”,在阿甘本看来,荷尔德林这种“缺乏连贯性”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内聚性”,按照荷尔德林此前的说法,恰恰是对“无限联系”甚至“无限统一”的追求,“因此,诗歌的秉性决不是被统一的事物的单纯对立,也决不是对立和变化的事物的单纯关系或统一;对立和统一的事物是不可分割的。”在寓居生活中,荷尔德林的“习惯”生活呈现出一种“痛苦的极致”,但是正是在痛苦的极致中追求“单纯的确定性”,从而以漂浮不定、无法占有的样态达到“无限联系”和“无限统一”,也就是说,寓居时代的荷尔德林抛弃了语言的连贯性、去除了表达的逻辑安排,在“缺乏连贯性”中停顿以达到这种联系和统一,“它只是标志着诗行和思想之间的僵局,这些诗行和思想彼此相随,不允许在一个与下一个之间插入任何逻辑协调的可能性。”这就是一种回归语言本身的“纯粹的话语”。
同时阿甘本对荷尔德林在寓居时代自我命名的“斯卡达内利”进行了分析,施瓦布拜访了荷尔德林,希望荷尔德林在诗作中签名,荷尔德林恼羞成怒,“我的名字是斯卡达内利”,同样费舍尔给荷尔德林看他出版的时机,荷尔德林大喊:“是的,这些诗是真的,是我的,但名字错了,我从来不叫荷尔德林,我的名字是斯卡达内利或斯卡利格·罗萨。”虽然对此的解释有很多,但是阿甘本认为,荷尔德林之所以给自己不同的命名,就在于他以“自愿的、可归因”的行为当成自己寓居的生活形式,这就像是他对待疯癫的态度,他不是拒斥,不是否定,而是“心甘情愿接受”,而这就是以自我命名的方式构建一种“习惯”,一种寓居的习惯,一种诗意的栖居的习惯,是一种他人并不拥有的“有”。所以寓居生活必然表现为自我意愿、自我命名、自我习惯的诗意的栖居,必然表现为和外部世界隔绝所具有的夸张、断裂、停顿的疯狂,“他的一生预言了一些他那个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否则就会陷入疯狂。”
阿甘本将“荷尔德林之狂”看作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很明显,体现了荷尔德林的生活态度和将生活当做诗歌的纯粹追求,或者说,是荷尔德林选择了疯狂,那么,后36年的塔楼生活到底是一种疯狂还是一种疯癫?或者说,荷尔德林后半生是不是真的患上了病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显然,阿甘本之所以以“荷尔德林之狂”作为编年史的标题,偏向于认为这是疯狂而不是疯癫,更不是精神病,甚至将其看成是在书写一部真正的“田园诗”:“那么塔楼之诗——西方登峰造极的、无与伦比的诗歌遗产——严格来说,就是田园诗。”在“序”中阿甘本阐述了“荷尔德林之狂”的内核,而这种疯狂在前36年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只是在我们自己的东西上,在民族的东西上,我们永远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因为正如我所说的,自由使用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最难的。在我看来,您的天才促使您对戏剧形式进行了史诗般的处理。从整体上看,这是一部真正的现代悲剧。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悲剧,在完全沉默中离开生者的国度,被装进某种容器,而不是为我们无法控制的火焰付出代价,被火吞噬。
这是荷尔德林于1801年12月写给博伦多尔夫的一封信中的话,这段话在阿甘本的这部编年史中构成了解读“荷尔德林之狂”的真正钥匙。荷尔德林在这里讲到了从希腊文化转向而面对“民族性的东西”,在1803年写给威尔曼斯的信中就说到了他转向的计划,“希腊艺术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因为它一直依赖于民族性的便利和偏见,我希望通过进一步突出它所否认的东方元素,并纠正它在任何地方出现的艺术偏见,以比以往更生动的方式向公众展示希腊艺术。”荷尔德林是如何实施他的计划的?阿甘本首先在荷尔德林“逐字逐句”的翻译中进行解读,荷尔德林痴迷于“直译”,直译的目的是完全要和希腊文相对应,这种极端的“超文字性”偏离了原文,甚至被认为是翻译的错误,但是在阿甘本看来,却是一种“诗学典范”:它将“陌生化”的翻译置于“本土化”的翻译之上,恰恰在传递着语言无法传达的内容,恰恰是对传统偏见的颠覆,它所形成的张力就变成了“创造性错误”,所以荷尔德林之狂所表现的执著就在于一种创造,“执着到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形式和艺术上的卓越,以换取一种破坏性的、不正常的、极端的、不可理解的诗歌方式。”
荷尔德林之所以以偏执的方式追求纯粹和艺术,更在于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异乡人”,而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诞生,“哲学首先是人被其他人所放逐,是哲人生活的城邦中的一个异乡人的处境,而他却继续居住在这个城邦里,坚韧不拔地向一个尚未存在过的民族讲话。”荷尔德林生活的时代是德国民族寻求独立和自我的时代,而这又往往意味着被抛弃,所以荷尔德林以异乡人的方式寻找民族性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就是在人民对他疯狂的诊断中坚持寻找他的“德意志之歌”,这就是荷尔德林哲学中所提出的“反思”,他从费希特的“我”的立场中发现了分离,这种分离就是反思,“在反思中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分离,统一性被假定为应该存在的东西……分离实际上意味着反思和假定。我不是一个实体,它只存在于反思之中。”荷尔德林就是在创作实践中,把反思交给了诗,“所有夸张中的夸张,诗歌精神最大胆、最崇高的尝试——如果它能成功实现的话——就是捕捉诗歌的原始统一体、诗的我、诗中的自我;通过这样的尝试,它将同时取消和保留其个性和纯粹的对象、统一的和鲜活的、和谐的和相互活跃的生命。”荷尔德林在现代悲剧中对死亡的放弃、把喜剧看成是“崇高的嘲讽”、在《俄狄浦斯备注》中提出“神圣背叛”的概念,都构成了“荷尔德林之狂”的文本,当然阿甘本认为荷尔德林在最后36年的寓居生活才真正构成了疯狂中的生命本体,“荷尔德林在他的塔楼中度过的36年中,他的生活和诗歌不正是顽固地、模范地、滑稽地追求着这一点吗?”
也正是从这点上理解,阿甘本放弃了荷尔德林到底有没有疯的判断,“最重要的是,事实上他想成为这样的人——或者说,在某一时刻,疯狂对他来说是一种必然,一种他无法回避的东西,以免他成为一个懦夫”,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阿甘本对这一判断的悬置,而是像荷尔德林自己所认为的那样,阿甘本并不认为他疯了,而是书写了“荷尔德林之狂”。但是这种把疯狂理解为自主的、反思的、创造式的行为,是不是陷入了一种悖论:如果荷尔德林的确按照自己的计划呈现了一种疯狂,那么他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结果,他的寓居生活都是理性的样本,但是他的确生活在一个丧失了理性的世界中,也就是非理性的寓居反而变成了理性的计划。一方面,阿甘本对荷尔德林哲学、政治、文学上的论述,所有的材料都来自于前36年,也就是说,在没有疯癫之前,荷尔德林的确在构建一个即使感性也是在理智范围的思想体系,而另一方面,后36年的寓居生活在阿甘本提供的编年史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完全在病理意义上的疯癫。
1806年,荷尔德林在被送往图宾根的奥腾里特教授诊所时,按照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的公爵夫人卡洛琳的描述,他大喊大叫、挣扎着抓伤了人,还在餐桌上把面包扔向了女侯爵的表妹脸上;在住进齐默尔家的时候,齐默尔描述道:“大量的血液涌上他的头顶,他的脸变得像砖头一样红,似乎一切都在困扰着他。”在齐默尔看来,他丰富了自己的想象力,“却损害了自己的智力。”后来有一次荷尔德林暴跳如雷中大喊,“我不是大师,我是国王的图书管理员!”1822年7月威尔赫姆·魏布林格首次拜访了荷尔德林,他是后来荷尔德林传记的作者,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见到这位德国伟大诗人的情况,“看到最杰出、最有灵性的人——人性最丰富、最伟大的一面——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在他直观感受中,荷尔德林“连最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不知道”,后来魏布林格多次拜访,但是每次都“战战兢兢地站在疯狂的荷尔德林身旁”,有一次荷尔德林不断重复向魏布林格说:“殿下,教皇陛下,大人,阁下,父亲大人!最尊贵的先生,请接受我的顺从。”1826年荷尔德林的母亲去世,荷尔德林根本没有什么反应;1832年,符腾堡州内政部发布了一份关于图宾根市精神病患者状况的报告,其中关于荷尔德林的病因被描述为“单相思、疲惫不堪、过度热衷于学习”……
他人在回忆中的描述、官方记录的病情报告、荷尔德林写给母亲的信,这些都构成了阿甘本“编年史”的真实声音,而这些声音无不传递出荷尔德林疯了的信息,或者这种疯癫是间歇性的,或者他人的描述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不可否认荷尔德林已经偏离了正常思维,甚至就是一种患病的状态,这种非理性的寓居生活的确构成了荷尔德林真实的生命状态,阿甘本的编年史也成为了“人物形象”的一个文本,但是将其病态的生活看作是一种诗意的栖居,看成是对生命本质的主动寻求,似乎也成为了一种误读,就像阿甘本最后所说,也许“只能胡言乱语”。但是不管如何,阿甘本用编年史展现荷尔德林本真的生命状态,本身就构成了对“赫尔德林之狂”的解读,就像荷尔德林人生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疯狂甚至疯癫就是一种“风景”:
当时光飞逝,一页页翻过时,大自然仍在徘徊,
这是纯粹的完美,是上天的光辉
人也是如此,就像树冠上盛开的花朵。
——《风景》(1748年5月24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