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13《野草》: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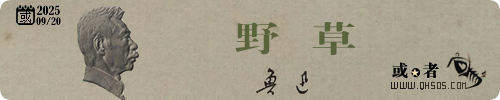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题辞》
烧尽一切野草,便是死,连同乔木,便是生命之死亡,而这死亡在地火的运行、奔突和燃烧中,“并且无可朽腐”,当一切都已毁灭,世界寂然而成最后的死亡?但,那地火来自于何处?又去往何地?地火在运行、奔突和燃烧之后,是不是也是自身最后的毁灭?但,那坦然、欣然,那大笑、歌唱之我又是谁?坦然、欣然之后,大笑、歌唱之后,是不是也是我之为观者的最后死亡?
地火、野草、乔木,以及我,组合成关于死亡的四重意象:野草和乔木是“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的产物,它们发芽,它们生长,它们终将死去,但是野草和乔木却是不同的存在,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野草,“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没有地火,也将是死亡,是朽腐,而乔木,高大的存在,根也深,花也美,也并非会遭践踏,遭删刈,或者并非容易死亡而朽腐——那乔木或者是如“以叶草作装饰的地面”,是以“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作衬托,而独在那里向上挺拔;但那地火运行而奔突,喷出而燃烧,会将一切的野草、乔木,以及一野草作装饰的地面摧毁,死是它们共同的归宿,是难以逃离的命运;而我之观者,是看见了野草的朽腐,是看见了地火的喷涌,是看见了死亡的降临。
而在这野草的世界,分明还有另一种死亡,野草吸取露水,吸取“陈死人”的肉和血,夺取它的生存,“陈死人”是在野草死亡之前就已经死亡——“陈死人”是谁?是过去的生命,当他们已经死亡,这死亡代表“它曾经活过”,当陈死人已经死去,当野草朽腐,一种死和另一种死,又构成了死亡和朽腐的双重叙事,而所有的死亡,所有的朽腐——连同地火的最后毁灭,都将构成我之观望的世界之死,在死亡面前,“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因为,“我对死亡有大欢喜”,死亡代表着它曾经活过;“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朽腐代表着“它还非空虚”——只有不曾活过、空虚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死亡,才不会让我坦然、欣然,不会让我大笑、歌唱。
于是,必有乔木,必有“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它们是我憎恶的存在,是《秋夜》里飞过的恶鸟,是《求乞者》中“自居于布施之上者”,是《风筝》中得到完全胜利的精神虐杀者;他们是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咒诅的人们呵,这使他痛得舒服。”当他们制造了“人之子”的死亡,“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他们是《这样的战士》中“举起了投枪”的战士,“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他们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强盗打开一个窗洞,傻子也跟着砸泥墙,奴才却把他们赶了出来,“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于是主人夸奖他,奴才是更好的奴才。
钉杀了“人之子”和“人之神”的刽子手,“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的战士,成为更好奴才的奴才,是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是乔木,当地火运行奔突,最后熔岩喷出,烧尽之后,甚至朽腐都已不再。而野草呢,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夺取它的生存,而当自己生存时,最终遭践踏,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这死亡却意味着曾经存活,意味着它还非空虚。秋夜中夜游的恶鸟飞过,那细小的粉红花却还开着,“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还瑟缩着,而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的,还有枣树,“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知道梦,知道季节,知道自己,墙外的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依靠而存在,是曾经存活,是非空虚。像那雪一样,在无边的旷野中,在凛冽的天宇下,它们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却“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而在“好的故事”里,先是如野草朽腐的不好的故事,“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不见了,在上面交错成“永是生动,永是展开”的美不见了,编程和了碎影,甚至碎影也不再了,“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生动、展开的碎影之死,好的故事之死,昏沉的夜是野草一般的寂灭。甚至,地火也一样会变成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用温热可以将它惊醒,使这遗弃在冰谷中的死火重新燃烧,但燃烧便是灭亡,带出冰谷,“我将烧完!”
必然的死,是因为曾存活,因为非空虚,而成为另一种活。《过客》中那走向坟地的过客,是不是在走向死亡?他是不知的,只是往前走,一个人走,“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但是听到了老翁喊他,“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是听到了自己,但是走向这作为终点的坟,不需要指引,也只有一条,但女孩说那里是有很多的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过客是不会转身回去的,因为回到那里,“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不回去,却要走向终点,不是要看见死亡,也不是要诅咒带来死亡的人,“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这力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终于消失在一种终点的稳当里。
大约很多人是连过客都不是,他们是想要看着野草朽腐的“看客”:广漠的旷野中,一男一女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其中,“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看客围观着,希望着对立之中看见杀戮,看见热血,看见死亡,但对立还是对立,裸身还是裸身,一种寂然持久地发生,于是看客感到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最后慢慢走散,在干枯中失了生趣,而男人和女人依然对立于旷野之中,提着利刃干枯地坐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杀戮没有发生,看客纷纷走散,于男女的他们而言,不死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而看客,早就制造了自己空虚的死,不曾存活的死。死而不死的小粉红花的梦,死而不死的冰谷之火,死而不死的过客,死而不死让看客死去的裸身男女,是“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的野草般存在,死亡而朽腐,朽腐而非空虚。即使像地火一般烧尽了它们,也是无可朽腐,也在延续着死而不死的生存。而在这死而不死的世界里,将有人坦然,有人欣然,有人大笑,有人歌唱,而在这坦然、欣然、大笑和歌唱之前,却是“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的境遇,“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沉默而充实,开头而空虚,是如何一种悖论,是如何在反逻辑中建立逻辑?““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是如死一般的世界,悲哀、苦恼、零落、死灭,但是却会变成药酒,只有沉默才能觉得充实,只有开头才感到空虚——像野草一般,吸取着陈死人的血和肉,自己也将遭践踏和删刈——一种朽腐的死是建立在另一种空虚的死之上的,所以沉默在开口中沉默,充实在空虚中充实。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他者之死是必吸取的血和肉,而自我之死则是牺牲,“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未生存要生存,空虚要非空虚,在《影的告别》里,“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不愿意去,便彷徨于天地,不愿彷徨,便在黑暗中沉没,但是一切都是“独自远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全是黑暗,影是没有了,但是黑暗和虚无,却是“实有”。
“实有”是人之存在,《墓碣文》里,正面的刻辞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离开!……”狂热和寒冷,天上和深渊,看见无所有,无所希望得救——这悖论般的存在是要从中找出自己,而这自己却要从“自啮其身,终以殒颠”中获得,却要在离开而死亡中复活。而背面残存的文字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食其心,想要知道本味,但本味又如何知道?早已经是死尸,将会朽腐,还如何有本味?于是,死尸从坟中坐起,“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死亡而朽腐,那种曾存活和非空虚,是在黑暗和虚无中变成实有,是在成尘中见微笑,是死尸识得本味——一个活着的人还不如死尸成尘?在《失掉的好地狱》中,看见的魔鬼是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魔鬼使用了人类的威严才叱咤了一切的鬼众,如此,“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人类于是整顿废弛,先给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砺刀山,使地狱全体改观,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所以当鬼魂门失掉了好地狱,也都是人类的罪恶,于是魔鬼赶走了地狱中的死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而人如何从失掉的地狱中走出,最终成尘而微笑?如何又在朽腐中识得本味,在黑暗和空虚中看见实有?
进入梦,离开梦,进入离开的梦,离开进入的梦;死人的梦,活人的梦,活人死去的梦,死者存活的梦,梦是一个连环,梦是一个寓言,梦是非空虚的实有。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我梦见自己在做梦”,梦见了小屋,梦见了森林,梦见了夫妻和孩子,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以及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以及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梦见自己做梦,莫比乌斯环一般,最后“将十分沉重的手移开”,梦便醒了,梦见自己做梦的梦便醒了;《立论》中,梦见在小学讲堂上请教立论的方法,“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被大家合力暴打,说谎说要富贵,却可能得到好报,“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那么,就说孩子“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狗的驳诘》中,梦见自己像乞食者,一条狗叫了起来,骂它是势力的狗,狗却嘲笑人类,“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只有人分清了这许多,包括生与死,愧不如人的狗分不清,却不感到羞愧,而人只有最后逃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死后》是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死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该死在哪里?“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死了,不再有人祝我灭亡,不再有人祝我安乐,“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于是,死后第一次哭,眼泪留下来,“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我于是坐了起来。”
梦见自己做梦,梦见自己活着,梦见自己死去,是实有?是空虚?是朽腐的死?是曾经的存活?却是“一觉”,“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是以我之生者关照我之死者,是以我之死者反衬我之生者,不死而死,死而不死,只有些微的醒来,看见了人的卑劣,看见了世事的死灭,野草也罢,地火也好,都在这死亡中归于其位,连同“我”,连同这文字,都成为死亡之梦的全部,“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