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13《资治通鉴(二)》:汉业由是遂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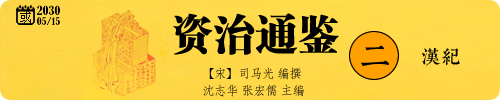
《资治通鉴》第二册记载了《汉纪九》至《汉纪二十八》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前140年辛丑,尽于公元8年戊辰。
【晚而改过】
作为汉朝重要君王,汉武帝相关的历史篇幅较大,在《汉纪九》中,司马光在开篇就说到了汉武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问他们古今之道,百余人中就有广川董仲舒,“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后来董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刘非,而刘非就是汉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号称血气之勇,正是董仲舒用礼仪来约束他,所以连易王都敬重董仲舒。
在这里,礼仪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在面对汉武帝时,董仲舒阐述了他的观点:“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礼乐教化是正治之道,人君就是将礼乐教化贯穿在国家治理中,“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在这里董仲舒强调的便是“独尊儒术”,“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是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的对策的记录,后来在元朔元年,即公元128年的时候,主父偃因为学士们联合起来排斥他,所以没有安身立命之地的他西入关中上书给武帝,早上刚转呈给武帝,晚上就被招入公众拜见武帝,主父偃上书谈到了九项事情,其中八项是关于律令的,而另外一项则是针对征伐匈奴的,“《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主父偃实际上是在劝谏武帝不要穷兵黩武,之后严安也上书提到了这个问题:“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万物蕃也。”徐乐上书中说:“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后来武帝召见三人,对他们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为郎中。
董仲舒倡导礼乐教化,主父偃等三人反对穷兵黩武,殊途同归,对于汉武帝以及西汉王朝来说,都非常重要。而司马光在此也是提出了一种警示,早在《汉纪三》中,他记载了萧何建造未央宫,当汉高祖质问萧何:“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竟然应对以“无令后世有以加”,由此司马光评论说“荒谬”,“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在这里他就提到了汉武帝,“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酇侯启之也!”萧何开头到了汉武帝时因揽件宫室而天下民疲财尽衰败不堪;在《汉纪八》中司马光感叹文景之治“美兮”的同时,也不无警示地指出了武帝的问题,“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但是尽管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官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但是司马光也比较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一方面汉武帝征伐四方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在困难是休养生息,在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方法中,都有人才辅助,所以,“天下信未尝无士也!”同一位君王前后的兴趣不同,但是总有相应的人才为其所用,“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这是对人才的看法,另一方面来说,也是武帝的成就所在。班固在《汉书》中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几乎都是正面的,“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司马光看来,则是“穷奢极欲”之人,甚至和秦始皇相比,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秦朝灭亡了而汉朝却能兴盛?由此他阐述认为,“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上不之察】
汉武帝“晚而改过”,甚至是司马光对他的最正面评价,而对于汉宣帝的过失,主要体现在对霍光和萧望之的态度上。对于霍光,班固在《汉书》中的评价是:“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闇于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虽然也是对霍光的全面评价,但是司马光却深入一步,一方面,他认为霍光在辅助汉室的过程中,的确表现了忠诚,另一方面,霍光没有办法让家族免遭祸患也是不争的事实,司马光认为,“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只有君王才能享有威严权柄,如果位置对调过来,像霍光拥有权柄而不肯归还君王,一定不能逃脱灭亡的原因。这里既指出了霍光专揽大权的危害,另一方面也是对汉宣帝的批评:汉宣帝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上官桀的奸诈行为,他也有能力亲理朝政;到了十九岁即皇位,了解民间疾苦的他也知道此时的霍光广置私党,但是汉宣帝还是授以兵权,使得对大家对霍光的积怨越深,直到霍光家族反叛朝廷,所以司马光质问:“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
这个观点和第一册中认为三家分晋“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汉宣帝无疑也是因为纵容霍光家族而成为“自坏之”的典型。而另一方面来说,霍光之后的霍显、霍禹、霍云、霍山犯下罪行,最后被诛灭全族,汉宣帝又似乎忘记了霍光当初的忠诚,“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所以汉宣帝也是薄情寡恩之人。在《汉纪十九》中,司马光对汉宣帝又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以汉宣帝的英明,让魏相、丙吉当丞相,于定国当廷尉,让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等人占据要位,实在有失偏颇,但这并不仅仅是选材的问题,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百姓方面没有什么才能,盖宽饶、杨恽的刚直性格也并不贤明,但是他们却都被杀,都不能使人心服,“其为善政之累大矣!”除了这个污点之外,按照杨雄的说法,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自取其祸,但是韩延寿之所以能冒犯上官,完全是被萧望之逼迫的,但是汉宣帝“上不之察”,使得韩延寿独受其辜,“不亦甚哉!”
【王道霸道】
甘露元年,汉宣帝认为皇太子刘奭“柔仁好儒”,当有人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提出了反对意见:“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甚至认为:“我家者,太子也!”在此司马光提出了对于王道和霸道的见解,他认为,“王霸无异道。”当初三代之隆,礼乐征伐都自天子出,是“王道”;后来天子微弱,诸侯便讨伐不尊王室者,这就是“霸道”。选择王道还是霸道,一个标准就是:“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所以王道和霸道并非如黑白、甘苦一样是完全对立相反的;而且,儒者既有小人也有君子,如果说俗儒者不可取,那不是还有真儒者吗?“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汉宣帝说太子太过懦弱而不能自立,不懂治国方法,也许还说得过去,但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生不可用,也是太过分了,“非所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听我藐藐】
汉宣帝所说的“柔仁好儒”的刘奭即汉元帝,虽然司马光批评汉宣帝,但是汉元帝在执政期间,真的不懂治国之法。“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司马光发出感慨,汉元帝怎么是这样一个容易受骗却难以醒悟的君王?弘恭和石显诬陷萧望之,这个阴谋诡计看起来的确很难分辨,但是起初汉元帝怀疑萧望之不会入狱,而弘恭、石显却让他不用担心出现意外,后来萧望之果然自杀了,这很明显就是弘恭和石显的阴谋,不管是谁,面对这一结局,也会勃然大怒,但是原地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这也最终导致了弘恭、石显肆意妄为,肆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后来,中书令石显独揽大权,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二人联合执政。汉元帝在一次饮宴时召见京房,京房当时问元帝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什么人?元帝回答说:“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京房进一步问,“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汉元帝回答说:“当然认为他们贤能。”于是京房就说现在有人并不贤能,“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汉元帝便问京房,“今为乱者谁哉?”京房便说:“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京房已经很明显指的就是石显,而汉元帝也知道就是他,但是汉元帝“亦不能退显也”。对此,司马光评价说,京房已经把道理说得很透彻了,但是汉元帝“终不能寤”,实在是一种悲哀,他引用《诗经》说:“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而汉元帝只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实在是一种过错。
而对于佞人石显,司马光引用了荀悦的说法,提出了为政者必须考察的东西:“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汉业遂衰】
“天命不慆,不贰其命。”这是晏婴对灾祸的一种说辞,其实暗指“天命”之变,到了西汉晚期,各种天变出现,除了自然现象之外,汉成帝之死也是充满了诡异,“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晚上还一切平静如常,但是清晨汉成帝穿裤袜起床,衣服滑落便不能言语,到了十刻时驾崩。对于君王这一诡异之死,民间哗然,他们认为是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所致,皇太后诏令大司马王莽,再加御史、丞相、廷尉一起追究审查,赵昭仪自杀。而到了汉哀帝的时候,“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宫。”汉哀帝绥和二年四月继位称帝,此时西汉灾异频发,京城和城郊发生暴动,陇西、北地、西河等地也爆发农民起义,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更受命”思潮盛行起来,而汉哀帝喜好酒色,宠信董贤,曾试图禅让给对方,元寿二年六月驾崩,时年二十五岁,在位仅六年。
所谓“天命”之变,所谓“更寿命”,实际上就是西汉走向最终衰落的说辞,当汉哀帝去世的时候,司马光记述说:“帝睹孝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而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由是遂衰。”汉业遂衰,也给了另一个人机会,他就是王莽,“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从汉成帝开始,王氏家族就开始担任要职,这说明所谓的威福有一个由小到大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九岁的汉平帝继位之后,“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这样一个体系使得“莽权日盛”,而太后也开始听命王莽的摆布,“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师傅,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
【元始元年】
元始元年,为辛酉年,即公元1年,这一年记录在《资治通鉴》中的大事有:
春,正月,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
置羲和官,秩二千石。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秋,九月,赦天下徒。
【符命之起】
元始五年,即公元5年,王莽向汉平帝呈献椒酒,在椒酒中下毒,汉平帝中毒生病,王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丙午时分,汉平帝驾崩,王莽命令年俸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一律服丧三年。后来有人“浚井得白石”,上书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一切都是王莽的计谋,“符命之起,自此始矣。”之后王舜等人一起让太皇太后下诏书,“安汉公莽,辅政三世,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辉光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具礼仪奏!”王莽由此成为“摄皇帝”。但是这并非是王莽的最终目标,“居摄元年”之后是“始初元年”,即公元8年,王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禅,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并下诏书: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新朝建立,还有玉玺在太后手上,于是王舜等人又向太后要国玺,太后怒不可遏地将玉玺扔到地上,“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王莽得到了玉玺,便在未央宫宴请太后,“大纵众乐。”西汉从衰落到灭亡,一切都归于王莽,对于这一改朝换代,班彪的评价是:“三代以来,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宠。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馀载,群小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将西汉的灭亡归于“女宠”,似乎也有失偏颇。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