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16《我们都是马戏团》:我会掉下去摔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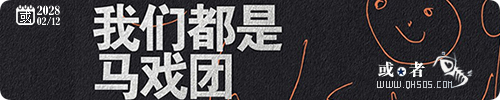
我相信——至少我愿意相信——电影的最大使命就是为观众竖起一面镜子,让人们在里面看到自己和他人,看清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那些我们社会中站在强势地位的人竭力想去否认的情感。
——《每个人都有梦想、欲望和需求》
“百人千影”系列编号之38,今年四月完成了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观影,46部电影组成了“伯格曼文本”——几乎囊括了伯格曼电影生涯的重要电影。当然这只是拉开了观影的一个序幕,之后又下载了伯格曼相关电影,等待有时间补看。已经观影和等待观影,我是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看见了伯格曼的那个马戏团,但是当伯格曼马戏团缓缓拉开表演的帷幕,他真的只是为了底下那些如我的观众,进入他的电影魔术和游戏世界,然后发现和我们有关的故事?或者说,伯格曼拍摄电影所秉承的就是一种观众至上论?
1976年伯格曼撰文指出:每个人都有梦想、欲望和需求,电影就是为观众竖起一面镜子,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故事,发现自己的情感,并与电影的契合中找到自己,甚至伯格曼在提出观众至上论的时候,还对以自己为代表的“站在强势地位的人”进行了自我讽刺,认为社会上拥有话语权的人总是竭力否认观众身上的隐秘情感。这种自损更是凸出了观众镜像对于电影创作的重大意义。不仅1976年的伯格曼持这样的观点,往前看,伯格曼似乎一直强调观众对电影的重要作用:在1960年的《亲爱的可怕的观众》中,他给了观众两个截然不同的修饰词,一个是“亲爱的”,这是和观众有着亲近感的表达,另一个则是“可怕的”,这其中就是距离感,为什么在伯格曼眼中,和观众既有亲近感又有距离感?在这篇文章里,伯格曼在观众面前表达了自己的焦虑感:“有人非常严肃地对待我的游戏,对我品头论足;有人在其中看到了象征符号,由此做出联想,揭露出更深层的含义;有人做比较,有人生气。”不同的观众成为不同的评论者,不同的评论者对电影做出了评论,让伯格曼焦虑的是:观众总是对电影背后的导演做出”盖棺定论“的评价,在这种评价面前,伯格曼
感觉自己“已经死了”,这是一种迷失,就像有人在挂着“伯格曼”牌子的展柜前塞进一毛硬币,伯格曼无疑已经成为了标本,放在了电影史的藏品柜里,塞进硬币,“伯格曼”就会点头或摇头——观众手中的那一毛硬币决定了“伯格曼”的态度,观众至上论就变成了观众决定论!
无论是观众看见了更深层的含义,还是对“伯格曼”品头论足,至少在观众层面来说,他们的确在电影里看见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或情感,它们组成了个体的隐私,这就是镜像——在1961年的文章中,伯格曼以自己的那部电影《犹在镜中》为题,表达了观众镜像的存在意义:“观众有在演员身上看到,自己境况的镜像反射的需求,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用来自外部的光照亮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他不仅仅指导演的自己,还包括电影中的演员,他们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在电影中演绎的故事,在电影中表达的情感,都变成了观众的镜子,观众就是从这样的镜子里看见了镜像,所以伯格曼认为,作为演员,必须要把获得认可的喜悦和为表演奉献的决心当成艺术创作的强大原动力,只有拥有这样的品质,才能更好地满足观众的认知能力,才能让观众看见自己的镜像,“一个没有灵魂知识的传教士只是一个原始药师,一个没有技术功底的艺术家只是一名业余爱好者。”而在1965年的《蛇皮》一文中,伯格曼认为,艺术家最大的优势就是“分享”:与有相同需求的同道分享,“当艺术家和这样的一群人抱团取暖的时候,在寒冷空寂的苍天下,在这个温暖污浊的地球上,至少还有这样一个集体。”虽然是和同道分享,但其实也是和观众分享,而分享的实质就是要让艺术家具有对观众的好奇心,无边无际的好奇心,永不停顿的好奇心,才是艺术永恒的动力。
《我们都是马戏团》,这篇文章发表在1953年的《家庭画报》上,那时伯格曼的电影《小丑之夜》正在院线上映,“马戏团”一方面是电影中的故事设置,马戏团和剧院的关系是故事的核心,另一方面来说,伯格曼以马戏团为喻,就是强调了电影演出是为了观众观看:电影导演,电影演员创作了电影,看起来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是文化界的危险品,捣乱分子,技术灾难。我们都是马戏团,都是人猿金刚,都狂呼乱叫;我们付诸生命地捍卫真实或虚伪,美丽与齷龊,管风琴或奏鸣曲,魔术、小丑、梦想、诅咒……包括那些诋毁我们的人,我们也有无限的权力凌驾于他们之上。”但是所有的权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的实现,那就是立足于当下,就是立足于观众,“如果我们不能在见证奇迹的那一刻把坐在黑暗中的观众吸引住,那我们就是被砍掉枝干、坐失良机的失败者,手中的魔术匣子被搞坏了,我们成了被观众哄笑的失败的魔术师。”甚至伯格曼为了讨好当下的观众,否认了创作的永恒意义,当马戏团的表演只为观众,伯格曼喊出了这样的话:“不,让我们开怀大笑,挺直胸膛,占领马戏团的马车吧,让我们敲起锣来,打起鼓,让子弹乱飞吧。”
伯格曼认为艺术家没有权力凌驾于观众至上,伯格曼否认艺术创作需要永恒意义,伯格曼喊出了“让子弹乱飞”的当下行动宣言,无疑伯格曼的这些观众至上论、观众决定论和观众镜像论,是站在观众角度进行考量的结果,从现实意义上来解读,也许是伯格曼为了电影市场而做出的妥协。1954年他在瑞典隆德大学做演讲时,就针对观众对电影市场的地位做出了评价。他认为,电影是魔术,是游戏,当电影从年幼时沉浸在自我世界的快感变成了面对市场的压力,电影遭遇了最大的困境,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观众,“许多电影上的实验总是偏离观众的需求,这蕴含着明显的危险,忽视观众需求的实验会让电影业发展成为在封闭的象牙塔中的自我阉割。”实验电影只不过是艺术家的自我阉割,所以伯格曼把拍电影看成是一种危险,就像走钢丝一样,电影马戏团想要为观众封上精彩的节目,这也就意味着本身变成了一种极大的风险,最后的结果是:我会掉下去摔死——这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必然。
| 编号:Y23·2220808·1858 |
实际上,伯格曼对观众地位的阐述,在这里已经有了一种微妙的转向,要满足观众的需求,要尊重观众的态度,甚至要取悦观众,不是因为观众决定了电影的成败,而是拍电影必须面对市场,必须面对资金,或者说,电影就是一种产业,观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但并不是全部,当伯格曼怀着“我会掉下去摔死”恐惧,其实是面对市场的焦虑与不安,当电影已经成为工业体系的一部分,稍不注意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女主角有黑眼圈,重拍,几万块打水漂了;自来水厂的漂白粉放多了,冲洗底片上留下了斑痕,重拍;死神不期而至,带走了一名演员,换演员,重拍,又是一大把钱;雷电击倒了摄影棚的供电箱,大家带着脸上的妆容在惨淡的日光中等待,时间一点点过去,钱也一点点消失。”在这里所有的重拍都和观众无关,都是这个工业体系内部暴露的问题。伯格曼对问题重点的转移,其实隐含着另一个线索:如果没有市场压力,没有投资风险,没有收益困境,也许根本不需要从观众需求出发拍摄电影,或者,电影依然是和伯格曼有关的一个梦,一个游戏,一种魔术——观众至上论看起来更像是伯格曼面对压力寻找到的一个理由,但在他的内心深处,那面竖起来的镜子真正让人看见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那个沉迷于其中的我,那个偏执于镜像世界的伯格曼:《蛇皮》中说:“电影成为我的表达方式是件看似天经地义的事,我找到了一个能让世界了解我的语言。”《关于拍电影》中更是强烈指出艺术创作的自我满足:“艺术为艺术,为了我的个人真相,无论是全部的真相,四分之三的或者完全没有的真相,重要的是这是我的真相。”
“对我来说,拍电影是一种个人需求,和应对饥渴一样。”有人喜欢画画,有人喜欢爬山,有人喜欢跳探戈,而伯格曼喜欢在拍电影中表达自我,而这才是伯格曼电影真正的起点——当然,也是他最后的归宿。那么,电影如何构建了关于伯格曼自我镜像?或者说,他走上电影之路的人生是怎样一部真正的电影?《关于<第七封印>》中,伯格曼回忆了自己跟随父亲去布道时的发现:当父亲在教堂宣讲台上布道,伯格曼的目光转向了教堂里面的神秘世界,那里有教堂的穹顶,有厚实的墙壁,有“弥漫其间的永恒的气味”,当阳光透进花窗照在教堂天庭的中世纪壁画上,伯格曼看见了通向幻想世界的道路,天使、圣人、龙、教徒、魔鬼和人,还有伊甸园里的蛇、巴兰骑的驴、约拿的鲸鱼和《创世记》中的神鹰,都成为了孩子眼中的非现实的梦幻,于是,死神和骑士下棋的画面出现了,那段死亡之舞成为挥之不去的影像,于是,受难的耶稣带来了强大的暴力和巨大的痛苦——它们进入了伯格曼的童年世界,它们在伯格曼的内心深处刻下了永远的符号,“多少年后,对于信仰的坚持和疑惑时刻追逐着我的思考。”
这是作为传教士的父亲给童年伯格曼带来的梦幻起点,而在母亲身上,伯格曼的镜像更为复杂和多元,在《告白:我母亲的日记》中,伯格曼回忆说,自己从小深爱着自己的母亲,这是一个美丽得“令人渴望又无法企及”的母亲,一方面母亲的天性是温柔的,当伯格曼不开心的时候,她都会让自己坐在膝上,然后抱起自己,不安地看着伯格曼,久久不放开,“这是我的秘密享受,至今还记忆犹新。”母亲还启迪了伯格曼的创造力,游泳、穿衣、戏剧表演、外出游玩,节日庆典,都是以母亲为中心构筑的家庭活动,“她用坚强和幽默,赢得我们的尊重,她活力四射。”但是另一方面,“后天的教养和她一辈子都不存希望的婚姻生活摧毁了她的天性。”她开始变得严厉、冷漠,而伯格曼也尝到了母亲和父亲联合起来对他的惩罚滋味:用藤条抽打身体,在脸上被扇耳光,“最恐惧的是关禁闭”,于是伯格曼和母亲之间的裂口越来越大,终于他开始离家出走,终于他开始对母亲怀恨在心,“我们太像了,都是冲突性、戏剧性的火爆性格。”
这是一个温柔的母亲,这也是一个严厉的母亲,这是一个启发无限创造力的母亲,这也是一个以惩罚作为手段的母亲——从爱到恨,从令人渴望到开始逃避,伯格曼对母亲的矛盾心态,最后反映在他的电影中,这是伯格曼镜像的最重要一个组成部分——而当母亲去世之后,伯格曼发现了母亲藏着的日记,在日记里他发现了母亲内心的秘密,“这么多年来,母亲毫不留情地记录她的内心感受,尤其是她的负罪感。”日记更是让伯格曼对母亲、对童年的记忆更为复杂多元,这也使得在电影中对人类灵魂意义的探寻更为深入,它和伯格曼在教堂里发现的奇梦世界构筑了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伯格曼其实就是沿着这条路不断发现“真相”——这是从个人真相为起点构筑的人类真相、灵魂真相、信仰真相和存在真相,而电影成为了揭开这些真相的载体。当十岁开始拥有人生第一台玩具电影放映机,当伯格曼开始拥有了最奇特的魔术箱,当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赫拉小姐》成为自己每晚观看的电影,伯格曼真正从那扇门进入了,“我是一名艺术家,一名匠人,我的手艺就是从石头里雕刻出脸、躯干和身体。”雕刻就是从想象变成光影,就是从愚蠢上升到崇高,就是在镜子里看见真相。
于是伯格曼开始了“每部电影都是我的最后一部”的艺术创作,于是伯格曼在光影世界里看见了梦想、欲望和需求,于是伯格曼在完成电影之后对自己作品进行了评论,于是伯格曼开始了“我和我的对话”:他创造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或者是戏剧家或者是记者,他们反过来采访自己,而自己也由此开始了和自我的对话——这是一问一答中的镜像世界,1960年发表在电影杂志《卓别林》上的文章,就是伯格曼的化身、法国电影评论家恩斯特·瑞福对电影、政治、宗教和道德的评论;1994年“英格玛,你何时歇手?”一文,伯格曼和记者安娜·萨兰德进行了对话,而安娜·萨兰德也是伯格曼的化身,他用对话自嘲,更讽刺了媒体的炒作;1956年的《电影画报》中,《给英格玛·伯格曼的六个问题》也成为伯格曼自问自答的典型:关于自己的定位,关于对女人的评价,关于电影《第七封印》,当然最具启示的则是第六个问题:“和您接触过的女人,您见过面或是讲过话的女人似乎都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都是什么印象呢?”伯格曼的回答是:“”
所有的女人都给我留下印象:老的、少的、大的、小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重的、轻的、丑的、美的、乖的、乱的、活的、死的。我喜欢所有雌性的动物:小母牛、大母牛、母猫、母猴子、母猪、母马、松鼠、母鸡、母鸭、河马、冷水鱼、热水狗、老鼠、大象!我爱女人、小鹿、蜥蜴和各种有毒的爬虫。我恨女人,恨不得打死几个或者让她们把我打死(请把不合适的地方划掉)。女人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我在这里混得不怎么样,可我别无去处,而且我也不知道哪里会有更好的去处。
从童年的梦幻起步,制造电影的光影世界,在电影中发现自我的真相,在评论中完成“我和我的对话”,这就是伯格曼“犹在镜中”的电影人生,它以自我为起点,最后又回归自我,这一种人生历程的电影化或者就像伯格曼对斯特林堡戏剧的评论一样,斯特林堡对戏剧实验性的探索就是完成了他的“历程剧”:《幸运儿佩尔的旅行》、《天国的钥匙》、《通往大马士革之路》等戏剧中,主人公在不同的场景中游走,最后返回了出发点,“故事朝着终结的疯人院一步步发展,在与命运相遇之后,故事又辗转回来,朝圣之旅,生命教训,所有的一切再次回到原点,终点成为起点。”这是评论家拉姆对斯特林堡戏剧的评论,而伯格曼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写道:“斯特林堡对历程剧的偏好有可能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吗?他本人就是一个不安的游荡者,至少他是这样总结自己的。”不安地游荡者,出发,寻找,回来,完成的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回归,实践着克尔凯廓尔“重复”的象征意义,而从童年的梦幻出发,穿越电影的梦幻之旅,即使在马戏团中“我会掉下去摔死”,伯格曼最后还是看见了那面镜子,照见了梦幻和记忆,照见了真相和灵魂,伯格曼也完成了人生最后一幕的“历程剧”。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