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07《肖开愚的诗》: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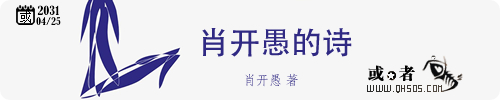
她丰满的乳房挺立,
像是骄傲地谴责爱情。
但她的乳房多余,是她的累赘。
松软着,下垂着,恋爱一张皮。
——《李小红的情欲》
一个行走的人,双臂下垂,双脚踅走,身后留下的是等长的影子,而身前呢?一大片的空白,蔓延至每一个边际,每一丛角落,甚至是无方向的迷失。“蓝星诗库”典藏本,已经变成了精装本,少了当初平装的朴素,设计风格偏向于抽象,但是抽象意味着诗意?当肖开愚以如此行走的方式书写他的诗歌,一个人以及一个人的影子,在向前中,是不是在空白处寻找着虚无和断裂?
《李小红的情欲》让人感觉到一种消解的力量,但显然肖开愚不是通过口水诗戏谑一个女人的独处——是寂寞还是孤独?“情欲”指向一种张开的欲望,她寻找着投射的目标,但是在没有客体的生活中,欲望以诡异的方式返回到自身。父亲在未出生时就死了,一声的爱情只是假象的中学物理老师或电工,读过的几本书里思想已经和陈旧的报纸一同抛弃,除了发黄照片中的他,李小红的生活中还有什么?还有丰满的乳房,挺立着,骄傲着,甚至开始“谴责爱情”,但是,实际上,“她的乳房多余”,是她的累赘,现在松软着,下垂着,是一张皮的爱情的象征,“浪花,甚至波纹,也没有激起,/没有什么请她从躺椅起来。”
这是关于乳房的对比,它变成了肉身的异样,它成为了情欲的写照,当丰满、坚挺的乳房开始松软和下垂,当虚无的恋爱扼杀了情欲,李小红和乳房一样变成了多余的存在,那个她想象过的“另一个人”也是一种累赘,那么整个世界的情欲就变成了自我投射,于是李小红成为了符号,她的符号化就成为了肖开愚在诗中的那句话,“她一个人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就像诗集封面设计中走向空白处的抽象的者。但是在向前成为一片空白中,李小红的情欲是不是也留下了身后的影子?是的,肖开愚说:“她忍耐,徘徊,消耗,/深夜才回家,睡觉。”即使这是一个乳房变得多余的女性,即使这是一个激不起浪花甚至波纹的生活,即使这是“一个人”构成的生活全部,毕竟她还在忍耐,还在徘徊,还在消耗,还留下了情欲的长长影子。
无论是李小红还是情欲,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另一个人,无论是抽象的符号还是身后的影子,肖开愚都制造了一种断裂的存在,这种断裂最具象被体现出来则是失去。早期的诗歌中还有某种宁静的诗意,但是宁静所投射下的影子也到处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它轻易地破坏了一种独处的状态。《黄昏》中属于“我们的时刻”是夜晚的影子所表达的,礼貌而静悄悄,但是,“蓝色带着另一个房间退让,/带着夜晚。而窗外/山峰耸立用黑色/——点亮这盏台灯。”点灯就是一种破坏带来的断裂,就是属于“我们的时刻”的影子的失去;在《海滩上》,她被遗弃在沙滩上,她像被吹掉了一条鱼的骨架,赤裸的色情已经消失了,即使“用自己的骨头战胜了自己的肉”,不色情的她也走向了自我的迷失,“游客走光了,她仍然躺在那里。”《北戴河微凉的秋光中》失去的是人生的意义,“一瞬间你就带走了我的一生。”《抓住你的身体》中失去的是低垂的天空下滑动的飞行器。
都曾经是有,最后都化为了无,《早晨》中肖开愚通过“早晨”构建了排比式的书写,这是蜡烛的早晨、雪球的早晨,说话的早晨,高音喇叭的早晨,四肢运动的早晨,却也是“滚动、爆炸、阴谋家和他的岳母/溃败的早晨”,是“汽车开动/把丈夫拖走的早晨”,早晨开启一天,早晨丧失所有,早晨之后和失去之无构成了对立式的断裂。在对于现实的书写中,肖开愚的“失去”表现在自我和他者两方面。自我面对现实,是不适从,是影子化,甚至是不能失去的失去,“但我,没有什么可供丧失。”我所看见的,我所有过的,都不再属于我,“我所有过的,在我说话时,/就已经消失;没有形状,没有质量。(《在公园里》”于是,“我感到我是一群人”,和一群人一样走进空旷的房间,翻过一排栏杆,聚成一堆恐惧,步行、坐车、进酒吧以及绕道回家,“我感到我的脚里有另外一双脚。(《北站》)”于是,“我们的语言又遗弃了/一个意义”,抱着德汉词典“绝望地靠在门框上”,有人离开,有人留下,从此再无交流的可能,“我们现在当然地/从我们的城市迅速消失。(《在徐家汇》)”
在公园里,在北站,在徐家汇,“在”是一种在场的标记,但是当“在”被纳入到公园、北站以及徐家汇等公共场合的时候,我被吞没,我被消失,“我属于我们”的巨大悲剧性就在与个体之我、独立之我、第一人称单数之我,变成了集体之我们、混杂只我们、第一人称复数之我们,“我属于我们”不是寻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而是被纳入到我们行列的时候,我已经彻底消失了。《星期六晚上》勾勒出了一种自我消失的过程:回家前去逛逛街,这应该是自我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一到街上就消失了,他的消失是我的消失的一个预兆,去电影院看电影,“片子好像都看过”;去商店,看见“两个姑娘在挑选胸衣”;即使回到学校时,也看见路边的林子里“两个孩子走着拥抱”……复数的电影,复数的姑娘和复数的孩子,是“星期六晚上”的“他们”,对于我一个人的存在状态来说,不是更凸显了我之独立价值,而是一种命运的走向是:“我属于我们。”这是“我感到一群人”的另一个说法,它以归属感的建立彻底解构了我存在的意义,“使用人称的/单数时慢吞吞地胡说八道”,这是日子美好的标志,它的意义就是“人称单数”还在,但是在“我属于我们”的日子里,是复数的几条街,是复数的几个乐队,我消失了,连生活的秩序都颠倒了,“否则在高架桥下,/跟着气功师,就得学习用脚/抓背、打拳,反而用手走路。”
无论是“我感到我是一群人”,还是“我属于我们”,肖开愚都在书写一种我被我们所异化的生活,我不再是我,而是“我们”的一部分,这种消失可以说就是被同一化带来的迷失。自我面对现实是“我们化”的迷失,那么当他者面对社会时,又是怎样一种断裂?肖开愚描述了“吃垃圾的人”,他来自外省,来自另外的世界,在垃圾中舔舐“一个罐头筒的裂缝”,就像一个死去的垃圾一样,“他的尸体突然/平放在地板上,颧骨高耸。/漆黑的夜晚他葬入/黑暗的大地。”《宠儿》中的他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在一个小旅店住下,决心/在九十年代成为二十世纪的琉善。”他嘲笑主人和主人的客人,他用海德格尔和李渔武装自己,他被人崇拜和妒忌,“处处的门都向他敞开,欢迎他。/他带着他的小品文,步子轻快。”从外省来的他和从家乡来的他,都构成了一种“离开”而到达的生活,但是离开本身就凸显了迷失感,像垃圾一样的存在或者嘲笑这个社会而受到崇拜,其实他们的生存都一样,都是被他者化而失去了自我。
| 编号:S29·2240411·2094 |
肖开愚在对他者的他者化描述中,多是用现实主义的讽刺笔法,《日本电器》中构筑了一个异托邦的世界,生活在“没有冷和热的日本气温里”,肉和蔬菜在三菱冰箱里已经变成了特殊的恶臭味,还有索尼电视机里的索尼广告,“引诱我们买它的皇帝”;《人民银行》不是人民的银行,“我们不是银行家和银行家的亲戚,/我们不是这座银行要算计的人物。”因为我们是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人民,所以我们变成了和“人民银行”无关的无产阶级,“少于人民又多于人民。”还有被困于《精神科》的他们,当他们带着虚弱的身体“释放出笼”,是一种被正常化的开始?那只不过是另一个“精神科”,“我赞美/伪装阑尾痛的骗子,/虽然只逃走三小时,/毕竟他头脑带有更新世界的狂想,/带着更新世界的狂想出了医院。”和自我面对现实的迷失一样,他者他者化的社会迷失更具悲剧性,它甚至构成了一种自我的骗局,在城市的生活中逐渐迷失却保持麻木。
两种状态都造成了断裂,肖开愚将自我的同一化和他者的他者化作为一种反讽的题材,揭露人前行的空白悲剧。当然,他所呈现的断裂文本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自我的迷失是一种断裂,还有空间造成的断裂,时间意义上的断裂,以及文化异化带来的断裂。空间造成的断裂凸显在肖开愚留学德国期间的几首诗作,2000年4月10日写于Winterthur的Herr Keller家的《楼梯口》一诗中,“蒸笼中的小蒸笼”和“字典中的小字典”构成了生活的两种面向,这是生活习惯的不同,这是语言的不通,但试图打通它们之间的隔阂,但是最后却是一种妥协,“夜里的/末班车出站时,啤酒和葡萄酒/廓清了雾露之奇数。”在《法兰克福一日》中,这种消除隔阂的努力还在继续,它是对一个人生活的打破和重组,“一个人是一个人,不因为联合而垮下脸来,机械,虚假。/一个人是一个人,不因为强大而眼光呆滞,读报,乱搞。/一个人在上班的路上不变成一个按键。一个人脱光了衣服而不消失。/一个人出了城不是一个坑。”但是一个人最终不仅是一个人,而且还是畸变的一个人,“一个法兰克福小伙子的工程舌头悄悄地舔一个法兰克福姑娘的屁眼。”在《布莱希特故居留言》中肖开愚借用布莱希特的戏剧手法创造了一种隔离的状态,“你的坟墓就在你家楼下,/这就是你对死亡的解释:近但是隔离。”在《柏林之刺》中,“中国”变成了无穷的分享,而在德国的下水道里游泳是惬意的,于是,“幸好东方人苦日长,西方人苦夜长——/筷子欢喜一个概念,餐刀绝望一块幻象。”
空间是从此处到彼处的距离,它试图构建一种消除距离的关系,却走向了更深的隔阂。时间也一样,从此时到彼时,也是对于时间的一次连接,但是连接却以断裂的方式表现出来,无论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还是《二月的第一个礼拜天》的模糊性时间描述,还是《1997年12月2日夜》《九七年三月,北京》等被标记为具体的时间,在肖开愚的世界里,他们都是停滞的某一个点:一年结束的等待,越过边境一直往东的行驶,一个中年妇女煮豆浆的初春,在火锅店里的那一天,都不是从过去来到现在,都不是用记忆连接现实,而时间记述的事件也毫无意义,“这是多么大的空虚也填不掉的虚无!你找回了你,我像他的时候就像我自个儿,把早餐往晚上吃。(《二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所有失去的东西都在《失去的影集》里:从黑白照片看见一个纯真的孩子,看见黄继光铜像前对英雄的礼敬,看见田野四月的蓝白色,但是时代造就了别离,时代拆开了记忆,黄继光铜像、批判专栏、蓝灰色学生装、一代人的思想,这些词语都是时代留下的影子,所以最后的选择是:“还是好衣服和好餐馆帮助他们/回到生意场,或是离开中国/并谴责昔日的生活是一场噩梦”,不管何种选择,最后是一个“和我一样微微有些驼背”的现实——肖开愚用隐秘的方式批判了那个时代,但是所谓的选择在拥有时也意味着失去。
空间的隔阂,时间的断裂,对于肖开愚来说,都是他对人类存在的某种洞悉,它延伸到因情欲造成断裂的爱情、时代造成的个体迷失,或者还有所谓文化造成和自然对话的断裂,《艾伦·金斯堡来信》通过美国诗人金斯堡的批判痛击了现代文明的虚伪,又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从旧金山广场到核弹头危机,“我是同性恋者。我的听众已体面地把我忘记。/我的灵魂里没有光。我的感情里没有和弦。/我的腿间没有速度。”所以,“我跳着醉步舞逃离了/图书馆,我逃离”,而在中国,西安的厚重历史变成了致幻剂,李白的山峰剩下光秃秃的意象,但是金斯堡在兄弟加里·斯奈德那里找到了连接点,“登上王之涣架设的楼梯,看见光在平原/绿色在山坡流淌,就像血液在北外礼堂凝固,溪水/从他嘴里溅出。”对现代文明的唾弃,使得诗人作出一个选择:“我愿意回到中国,在江西北部/一个河畔村安家,买两亩地,/酿一窖酒。/噢,克鲁亚克早死。”但是这会成为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归宿?它的自然化只不过是去政治化的逃避,而最后还是回到政治生活中,“1968年,我愿意是亨利·米肖,一个高级将领/1968年,我愿意在天安门城楼上朗诵诗/我从东方回到美国/出版了《行星消息: 1961-1967》……”
对于肖开愚来说,是一种断裂造成的无奈?还是迷失之后对断裂的拥抱?这两个问题其实凸显着一种转向,肖开愚所强调的“我属于我们”的迷失感当然是在批判同一化的现实,但是他反过来又刻意强化外省的存在感,甚至在长诗中架空意象造成叙事的断裂,所以对于肖开愚来说,断裂是一种必然的状态,甚至只有在“我感到我是一群人”中才能拿起反击的武器,才能破灭整个同一化的秩序,这带来的一个最大弊端是肖开愚制造了语言和意象的隔阂,尤其在长诗中,意象的断裂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的表达,和短诗比起来,完全是一种虚无的抒情——《向杜甫致敬》是其中断裂最少的一首诗,肖开愚将忧患诗人杜甫置于当代的语境下,或者说将“杜甫”变成了一种时代的反向符号。这个时代是什么,是郊区的小河流着临时码头的坏血,是家家电视收看一部连续剧,是警察对人性的麻木,“我们所说的和所习惯的绝望,/机关里准备了最佳理由/让喜悦来统治表格”,在这样一种“中国”的现实里,“我看见了另一个人”,他像来自另一个中国,他用声音传播者恐惧,他对现实发出哀告,他在自己的草堂里发出“不要”的喊声,所以这来自另一个中国的另一个人,唤醒了属于我们的我,而且把我的觉醒变成了“我们”的力量,“我不是我一个,是所有/裸露的、脱出躯壳的人的/内疚,我飞翔在城北和南市/凹陷的夜晚,我看见/医生躲进太平间休息/欣慰地犹如自杀。”
只是致敬,只是唤醒,却不是战斗,“不是为了战斗,只是/酒后咬文嚼字。”用诗歌来批判?用文字来抗击?或许是一种武器,或许是一次投入,但是就像永远断裂的现实一种,肖开愚更多表达的是一种虚无主义,“我正在腐烂的肉体并不是一个通向书房的把手,/话说回来,这也不是什么自焚表演的结束。”向前是空白,是吞没,是“我属于我们”的迷失,不如转过身来回到影子的世界,“向杜甫致敬”是向另一个中国致敬,是向另一种批判致敬,影子般的存在,依然是和我的一次断裂,“一行诗/就像一声来自古代的诅咒。”就像李小红的乳房,多余而成为累赘。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614]
思前:【欧也·2024】险
顾后:隧道里藏着“夏天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