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24《普鲁斯特与符号》:叙述者如同一只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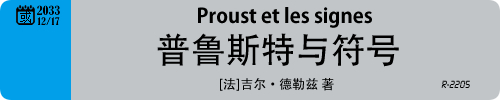
他们不是我的读者,而是他们自己的读者,我的书无非是像放大镜一类的东西,贡布雷的眼镜商递给顾客的那种玻璃镜片;因为有了我的书,我才能为读者提供阅读自我的方法。
——《三种机器》
《追忆似水年华》是普鲁斯特创作的作品,当它被完成,它就脱离了作者而成为读者手中的作品,当读者阅读这部作品,他就变成了自己的读者,而作品也变成了找到阅读自身方法的作品。普鲁斯特用“他们不是我的读者”的否定说法,是一种拒绝?或者他以“接受美学”的方式宣布了作者的退出?当普鲁斯特把《追忆似水年华》交到读者手中,让读者成为自己的读者,看上去是剪断了和作者相关的“读者”的联系,但是入贡贡布雷的眼睛商手中的玻璃镜片一样,它成为了读者自身的工具,读者是通过这个工具而成为自己的读者,是通过工具而阅读自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接受美学却无法否定这本书的工具意义,工具构建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工具创造了自我阅读的方法,正是工具具有输出的机器属性,所以普鲁斯特的这一否定其实变成了对于“文学机器”使用的一种建议,按照吉尔·德勒兹的说法,“《追忆似水年华》并非仅仅是一种普鲁斯特在制造它的同时并且自行使用的工具。”
普鲁斯特提供了供他人使用的工具,之所以这个工具具有读者“阅读我们自己”的意义,之所以一部机器可以让人们做意欲的一切,就是因为机器构建了一种“超规定”,“现代艺术作品是一部机器,并作为一部机器而运转。”就是因为艺术作品作为机器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它生产某些真理,它将真理从我们的印象中被提取出来,在生活中被挖掘出来,在一部作品中被呈现出来,“正是因为艺术作品是一种产品,它所提出的特殊问题不是有关意义,而是有关用法。”工具、用法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是多义的,但是机器生产真理却是一种一,这个一和多的关系构建的是艺术作品的本质,那么,多背后的“一”如何在机器的生产中成为一种“精神性的等价物”?而这个问题就成为了德勒兹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追忆似水年华》的统一性存于何处呢?”
对《追忆似水年华》统一性的发问,德勒兹从书名开始解读,那就是关键词“追忆”,追忆是什么?追忆不仅仅是一种回忆的努力,一种记忆的探索,它就是“追寻真理”,而这个真理就在于时间之中,时间不是“似水年华”变成“逝水年华”那种过去的时光,而是遗失的时光,因为遗失所以要追忆,因为追忆而重现,在这个“追忆”的链条里,德勒兹认为,普鲁斯特构建的时间所表达的不是对记忆的揭示,而是对一种“学习过程的叙述”。在这里德勒兹无疑把普鲁斯特看成是柏拉图主义者,柏拉图就提出了学习就是回忆的观点,在普鲁斯特那里,学习的介入超越了目的和原则,它让追忆转向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而这个转向就体现在《追忆似水年华》所构筑的符号体系之中,符号也构成了这本书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符号由人、物、对象所产生,这些符号不属于同一个类型,呈现出不同的方式,一个人可能会娴熟地破解某个领域的符号,却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领域里束手无策,《追忆似水年华》中有诺布瓦的外交密码,有圣卢和战略符号,有戈达尔和他的医学征候;即使在共同领域之中,不同的符号世界也依然相互隔绝,维尔迪兰的符号对于盖尔芒特来说并不通用,斯万的风格或夏吕斯的密语在维尔迪兰那里也行不通;即使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破解或阐释,符号和意义之间也不具有同一性的关联。
这就是符号具有的“多”,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通过破解与阐释,让我们发现真理。通过对这些符号的破解如何发现真理?德勒兹将《追忆似水年华》分成三个世界,即上层社会的社交界、爱的世界、印象或感觉属性的世界,对应于这三个世界就有三种符号体系:社交符号、爱的符号和印象或感觉符号。社交符号取代实际行动或思想,成为了行动和思想的替代品,所以它是一种不再指向他物的符号;爱的符号在爱者和被爱者之间构建了主观的法则,它体现的是比爱更为深刻的嫉妒,甚至嫉妒就是爱的目的和重点,爱情的命运就成为了“爱而不得”这样的格言,而在德勒兹看来,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存在着一种趋向无限性的“雌性同体”,它使得两性分离衍生出索多姆和戈摩尔序列,最后构成了参孙预言的关键:“两性必将各自消亡。”印象或感觉属性的符号存在着破解之中失败的风险,因为它们自身是不充分的符号,玛德莱娜小蛋糕、钟楼、树木、石板路、手巾、勺子或水流的喧哗,带来了奇妙的愉悦,这种效果已经和符号区分开来了……
| 编号:B83·2251014·2373 |
三种符号无疑都具有超越符号本身、超越物的意义:社交符号带来了造作的兴奋,爱的符号让我们在谎言、分离和消亡中感受更剧烈的疼痛,印象或感觉符号带来愉悦,而在这三个世界和三种符号之上,就必然有更高的符号世界,那就是艺术的符号,它是对前面三种符号的转化,它是要在学习中追寻意义,而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就是“本质”,它指向的就是真理。“真理依赖于与某种事物的相遇,后者驱使我们去进行思索与求真。”符号是相遇的出发点,而相遇的重点就是意义,它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表现的就是时间:逝去的时间、遗失的时间、重现的时间和原初的、绝对的时间,是时间的四种结构,每个符号对应于其中的时间性,这是符号具有的多元性,“每种符号都不均等地拥有多种时间线;而同一种时间线也不均等地交织了多种符号。”但是符号的多元性背后有一种时间的本质:它是一种背离,“一场通往坟墓的奔跑”,也就是说,符号自身蕴涵着作为关联的异质性,只有通过学习,通过和他人的学习,所学习的东西之间不存在相似性的关联。
在学习的过程中,背离和自身的异质性其实表现的是对理智的否定,理智是通过符号辨认事物,理智所追求的是事物本身,这无疑是一种客观主义,它追寻的真理就变成了科学和哲学。但是德勒兹认为,普鲁斯特提出了爱和艺术所构成的隐秘联姻,“一件艺术作品要比一部哲学著作更有价值;因为在符号中所包含的东西要比所有明确的含义更为深刻。”因为符号不提供理智所要求的明确含义,所以它会产生失望,在多种多样的失望面前我们才能不断进行学习,才能以主观性的补偿把艺术作品转化为观念的联想,这种联想是倾听、注视、描绘,是分解对象,研磨对象,最终萃取真理。所以真理作为本质,超越了被指示的对象,超越了明确说出的理智真理,超越了相似性中的再现,本质就是非逻辑或超逻辑的,“正是本质构成了符号和意义的真正统一;正是它使符号无法还原为发出它的对象;正是它使意义无法还原为理解它的主体。它是学习的最终目的,或者是最后的启示。”
也只有在艺术的层次上,本质才能被揭示,因为艺术给予了一个真正的统一体,由非物质的符号和完全精神性的意义所构成的统一体,这就是本书作为第一句话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本质恰恰就是此种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正如其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在德勒兹看来,本质就是一种差异,终极的、绝对的大写的差异,普鲁斯特指出了本质的差异是一种内在的差异,“性质的差异存在于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方式之中,如果不曾有艺术,那此种差异就将始终作为每个人的永恒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认为普鲁斯特是莱布尼兹主义者,本质就是莱布尼兹的单子,每个单子根据表现世界的视点而被界定,而每个视点自身都归结于某种居于单子的基础的终极性质,也就是说,每个主体都表达了绝对差异的世界,它是作为本质而被表达的,本质就不是主体的本质而是存在的本质:本质自身被蕴含于、包含于、蕴藏于主体之中,并构成了主体性,“被包含于本质之中的世界始终是大写的世界的开始、一个宇宙的开始、一种绝对的极端的开始。”所以,本质自身是及差异,而差异只有通过自我重复才能被确立,“此种重复遍及各种多变的介质,并把多样性的客体聚集在一起;重复构成了原初差异的不同等级,而多样性也构成了一种同样根本性的重复的不同层次。”
在关于“符号”的系统里,德勒兹构建了“重复与差异”的理论,符号具有多样性的标准,本质决定了符号与意义的关联,“当本质以更高的必然性与个体性而得以实现之时,这种关联也就变得越来越紧密……”所以德勒兹认为,《追忆似水年华》中最关键的不是记忆与时间,而是符号与真理,不是回忆,而是学习,“《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观念就是:符号、意义、本质;学习的连续性与启示的瞬间性。”所以追寻真理就意味着我们不要成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而要成为考古学家,进入洞穴,破解符号的密语,然后找到意义和本质,这个过程就是经历了入门阶段的学习。所以学习在德勒兹看来构成了普鲁斯特作品的“哲学性”意义,它以和哲学针锋相对的方式建立了“思想意象”:它是偶然相遇的符号,它是给予了思想的事物以必然性,它是一种在自身之中的创生,“创造者就像是嫉妒的、神圣的解释者,他掌管着那些真理显露自身的符号。”
普鲁斯特在符号和意义之间构建的本质统一体就表达为这样一句话:“不存在逻各斯,只有诸多密语。”思想就是解释,就是翻译,本质是有待翻译的事物也是翻译的过程自身,它既是符号也是意义,它蕴藏于符号之中,在意义中展现,这也是普鲁斯特将《追忆似水年华》以及所有作品的读者都看成“他们自己的读者”的深刻用意,每个人都如同考古学家一样和符号相遇,每个人都在对符号的翻译和阐释中追寻意义,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作品本质和真理。这是德勒兹《符号》部分的内容,它出版于1964年,而在6年之后再版时加入了第二部分《文学机器》,如果说在《符号》中德勒兹阐述了“差异与重复”成为了1968年《差异与重复》的导读,那么《文学机器》重点则从普鲁斯特的文本中提出了“文学机器”的概念,而文学机器对真理的创造本质也源于德勒兹在普鲁斯特作品中发现的“思想意象”,探寻了和逻各斯对立的“诸多密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反逻各斯》,反逻各斯就是和逻各斯的对立,就是和雅典的对立:
与观察相反,普鲁斯特提出了感性;与哲学相反,他提出了思想。与反思相反,他提出了翻译。与我们所有官能的逻辑的或一致性的用法(理智先于此种用法并使其集中于一种“总体精神”的虚构之中)相反,他提出了一种非逻辑的、断裂的用法,它向我们揭示:我们永远也不能同时支配所有的官能,而且理智总是延后到来的。同样,与友情相反,他提出了爱情。与对话相反,他提出了沉默的解释。与希腊式的同性恋相反,他提出了犹太式的、被诅咒的同性恋。与词语相反,他提出了名字。与明确的含义相反,他提出了不明确的符号和被隐藏的意义。
普鲁斯特构建的反逻各斯就是符号和象征的世界,“普鲁斯特式的记忆的原创性恰恰正在于此:它来自一种精神的状态,来自联想的链条,但却指向一种创造性的或超验的视点——而不再是像柏拉图那样从一种世界的状态转向被注视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普鲁斯特又变成了“反柏拉图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观点的矛盾,之所以德勒兹提炼出普鲁斯特记忆的联想意义,就在于它是创造性的,是超验的,不是把创造看成是再回忆,看成是思想,而是再回忆和思想本身就是创造,“正是风格以人们谈论经验的方式或表达经验的模式取代了经验,用对于世界的视点取代了世界中的个体,并从回忆中形成了一种被实现的创造。”这是“学习即回忆”的另一种阐述,它击退了逻各斯,击退了理智,而是以异质性、创造性的视点来完成统一,在不一致性、不可共度性和碎片性中保持了多样性的断裂、间隙、空白和间断。
德勒兹提出了反逻各斯的两种形象,一种是箱子,它关涉的是容器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是嵌合、包含和蕴涵的形象,就像人、物和名字,它是一种箱子,从这个容器中获取另一种本质和形式的事物,一种难以界定的内容,之所以它是缺乏共同尺度的内容,所以需要叙述者,叙述者就是通过解释而展开、展现与箱子不可公度性的内容,甚至遗失的内容,所以它是一种重新发现,并可能在发现中抛入不可避免的失望,这种失望就在联想和超越中揭示了缺席与逝去的真理、在场和重现的真理;另一种则是瓶子,它关涉的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或者是不对称、不相通部分的共存,或者是相互分离部分的重新组织,或者是相互对立的道路,所以叙述者的任务就是遴选和选择,每个瓶子中都有一个自我在生活、感知、欲望和回忆,它只是统计学上的总体,“不是为了将它们整体化,而是为了选择。”两种形象,叙述者都展开了行动,一种是解释,他面对的是“有待解释的敞开的箱子”,一种则是选择,面对的则是“有待选择的封闭的瓶子”,它们都构建了一种可能性,而时间就是对所有可能时间和可能空间的横贯,“嫉妒,是多元性的爱之间的横贯线;旅行,是多元性的场所之间的横贯线;睡梦,是多元性的时刻之间的横贯线。”
叙述者当然是作者,是《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但是当他把作品的读者交给他们自己,所完成的就是作为普鲁斯特的叙述者的退场,而将读者自身的叙述者请入,而留下的那个工具就以文学机器的方式生产属于叙述者的真理:第一种类别的机器是对部分性客体进行生产而得到界定的机器;第二种机器则是产生共振,它形成了当下的时刻和过去的时刻,由此产生了艺术的效应;第三种类型的机器是前面两个类别的结合,它产生的是强制运动以及死亡的观念。整部《追忆似水年华》就是通过三种机器的书写实现了生产:部分性对象的机器、共振的机器和强制运动的机器,每种机器都在生产真理,而且是作为时间效应而被生产的,“消逝的时间,通过部分性客体的碎片化;重现的时间,通过共振;另一种方式的消逝的时间,通过强制运动的振幅,这种消逝因而就在作品中发生并成为其形式的条件。”不同的机器,不同的生产,不同的时间,那么再回到本书的第一个问题,这种多元化的真理背后是什么构成了统一性?德勒兹认为,那就是风格,风格归属于本质,它不会来自同一视点,却在事物被分隔而形成的共振中具有相同的效果;它是不和谐的,始于不同的对象,但是它们具有相似性,通过联想的链条而在主观上相连。本质意味着在多样性的混沌中,作品本身的形式性结构构成了统一性,而形式性结构就是横贯性,“它横贯了整个语句,横贯了整本著作中的不同语句,它甚至把普鲁斯特的著作与那些他所热爱的作家结合在一起,奈瓦尔、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
文学机器是反逻各斯的,反逻各斯的机器就是相对于逻各斯作为动物存在的植物,它由相互隔离的部分构成,却通过分离出来的部分进行间接的沟通,它没有总体化、统一化的整合力量,但是它的碎片不缺乏任何东西,这部机器不存在着一个主人公而是存在着配置,“这部机器以某种形态、根据某种关联、为了某种用途或产物而运行。”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提出了叙述者就是一个“无器官的身体”,它不拥有器官,只是具有那些他所期待的器官,德勒兹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就是蜘蛛,蜘蛛看不到、感受不到也记不得什么东西,但是只要在蜘蛛网上有微小的震动,就会传到它的身体里,是它扑向那个方向,“没有眼睛,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它只对符号做出回应,那最微小的符号作为一阵波穿透了它的身体,并使它扑向猎物。”这就是无器官的身体,而《追忆似水年华》就是编织了这张巨大的网,“每一根线都因某种符号的触动而振动:蛛网和蜘蛛,蛛网和肉体是同一部机器。”而那个把读者当成他自己的读者不也在这个蛛网中?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