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24《鲍德里亚访谈录》:写作开启了致命的可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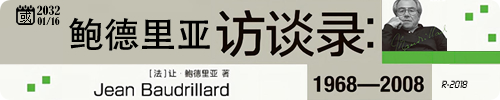
“我生于1929年,恰逢黑色星期五过后,受狮子座和经济危机影响……伴随着现代性的第一次大危机降生的我,希望能活得够长,能见证现代性在世纪末的灾难性转折。”
——《病毒的与转义的》
采访者:皮埃尔·邦塞纳,时间:1999年。生于1929年的让·鲍德里亚那时已经七十岁了,对于人生的七十年,他发明了一种“以十年记的小小神话”来记录的编年表:1929年恰逢经济危机,1939年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9年是冷战的顶峰,1959年则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再过十年是1969年,鲍德里亚认为是“处在留疤运动的阴影之中”,1979年似乎是空白,“我还在寻找这一年的重大事件”,1989年是柏林墙倒塌……从1929年到已经到来的1999年,鲍德里亚让生命有关的刻度和世界大事联系起来,但是当1999年在时间维度上的确来到了“世纪末”,他在1991年接受安·洛朗采访时所说的“现代性在世纪末的灾难性转折”到底有没有出现?
除了按照自己的出生每隔十年记录了一张编年表,鲍德里亚也喜欢对自己作为一个的经历命名,他说在二十岁的时候是啪嗒学家,三十岁是情景主义者,四十岁则是乌托邦主义者,五十岁在跨界,而到了六十岁成为了“病毒的与转义的”——对于这样的自我定位,鲍德里亚想皮埃尔·邦塞纳作了解释:所谓“转义的”,就是把结果当成原因,“颠倒或打断事物的合理展开”,它是对原义的某种改变;“病毒的”则指的是:“不再有原因,只有联结造成的干扰。”具体来说,就是不再是批判性与理性的激进思想,而是扰乱判断和写作的激进思想,一个是颠倒了事物合理展开的“转义”,一个是不再是批判性和理性的激进思想,鲍德里亚将在六十岁时成为的自己概括为这样一种人生:“这既是欲望、梦幻,也近乎颠覆事物或将序列至少无限延伸至虚拟灾难爆发的系统性策略。”
颠覆事物,迎向“虚拟灾难爆发”,这是鲍德里亚真正对自我做出的策略,六十岁即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算不算鲍德里亚所认为的现代性的“灾难性转折”?或者说在70年的人生中他是不是最后就是那个见证者?而实际上皮埃尔·邦塞纳引用鲍德里亚那段关于1929年和出生有关的“现代性的第一次大危机”的说法是在1987年的《冷记忆》中,看看从他说了这句话之后,世界到底有没有出现现代性的“灾难性转折”?收录的访谈在1987年之后的第一篇是《这瓶啤酒不是一瓶啤酒》,这句话来自布莱希特戏剧中的齐非尔:“这瓶啤酒不是一瓶啤酒,但这同如下事实抵消了:这支雪茄也不再是一支雪茄……”从这句话中鲍德里亚“发明”了一个问题:啤酒不曾是啤酒,而如果雪茄曾真的是雪茄,那么被改变的一切是不是具有战争的性质?“如果一方曾是战争,而另一方却不曾是信息,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不平衡……”战争就是如卡勒所说:“一切都不在其位,这就是混乱;在规定的位置上什么也没有,这就是秩序……”
实际上鲍德里亚所说的现代性的危机或灾难,就是一场人类的战争,就是不在其位的混乱,甚至比混乱本身更甚的“在规定位置上什么也没有”的秩序,所以当1991年的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鲍德里亚认为战争并没有在政治层面发生,这只是一种“作为威慑的政治”,在伊拉克的土地上,人们变得消沉,变得愤怒,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微不足道,而且从信息化对现实化的“模拟”角度来说,鲍德里亚认为海湾战争没有事实的演出过程,也没有战争消亡的过程,二重的象征关系根本不存在,它只是由诡辩的技术手段所“实现”的战争,“而它不再发生,因为这里没有事件了。”战争取消了象征关系和事件性,所以1991年的“这瓶啤酒不是一瓶啤酒”。到了1999年,也就是时间意义上的“世纪末”,当鲍德里亚对皮埃尔·邦塞纳说“我仍在这样希望,不幸的是,希望非常渺茫”的时候,当然他并没有见证这一灾难性转折的到来,他只能定义自己是“病毒的与转义的”,来捍卫一种由欲望、梦幻和颠覆事物构成灾难爆发的系统性策略。那么在新世纪的2006年,“9·11”已经过去了五年,鲍德里亚是不是在这场恐怖袭击中见证了现代性的灾难性转折?
鲍德里亚说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亲眼看见两栋楼被建立起来,当“9·11”时它们倒塌仿佛世界的重力消失了,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美国事件,鲍德里亚将其看作是想象力的某种实现:因为从双子楼被建造起来开始,鲍德里亚对它们的唯一要求就是“倒塌”,因为创造它们是一种空无,只有倒塌才能以“势不可挡且宿命般”的方式让空无暂停片刻,“这就是我们透过自己仅剩的、具有重要作用的想象力所能看到的东西……”这就是鲍德里亚在《谋杀现实》这篇访谈录里所讲到的“象征”意义,在他看来,象征总是由“礼物-回礼”的二元关系所阐述,当建筑物建造得越高,就也能体现它“全能的虚拟性”,这就是奇迹般的“礼物”,而越是如此就越是幻想它会倒塌,这就是“回礼”——为什么有礼物必然构建了回礼?鲍德里亚说,很多人都有对可逆性的黑暗欲望,当“激烈的可逆性”在其中发挥作用,它就构成了象征空间,双子塔就是一个在可逆性中产生欲望的存在,“不需要变成恐怖分子”,这一逻辑支配着人类,所以在恐怖袭击之后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只是一种载体,甚至是一场全球性的“表演”。
| 编号:E39·2240905·2176 |
所以,鲍德里亚在这里强调了“重新发现象征”的意义,重新发现象征就是在可逆性、欲望、想象中构建事件,所以希望重新发现象征的鲍德里亚称自己是“否认主义者”而非“否定主义者”,是“幻灭主义者”而非“幻觉主义者”,是“背叛者”而非“伪君子”,是“发泄分子”而非“反动派”,否认主义者、幻灭主义者、背叛者和发泄分子,这些对自我的命名都是鲍德里亚重新发现象征、从而在可逆性中构建欲望、想象的书写的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不是“9·11”更像一场灾难性转折,而是“9·11”所实现的象征是对现代性转折的一次实现。而到了2008年访者让-弗朗索瓦·帕亚尔对鲍德里亚的访谈,提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战”,鲍德里亚认为,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外,第三次则是“冷战”,它决定了共产主义的命运,这三次大战每一次发生都意味着走向了更具包容性和更加独特的全球秩序,但是他认为现在这个过程走到头了,“我们如今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统一系统,一种完整的现实,其中敌人无处不在,也处处不在。”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它是“全球化用以反对自身的战争”,这就是整个系统的自我耗尽,是整体的自我解构,而恐怖主义无疑就是这场战争的强烈隐喻——为什么在“9·11”发生时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是全球的一场“表演”?而第四次世界大战则变成了恐怖主义制造的强烈隐喻?
这就涉及到鲍德里亚的战争观,“9·11”是不需要恐怖主义而实现的一次象征性欲望满足,是在建造而渴望倒塌所构建的可逆性欲望系统里,所以恐怖主义只是一种表象,是实现的“表演”,而在后“9·11”时代,践踏了普世价值而失去合法性的美国在没有自己特定敌人的基础上制造了敌人,而这些敌人是虚拟的,它们是阿富汗,是伊拉克,是恐怖主义,连同恶本身也变成了虚拟的,“最糟糕的是,人们通过宣称要打击这一邪恶,到处制造了传染源:阿富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就好像系统预先创造了自己的漏洞一样。”恐怖主义成为一种虚拟的存在和实现,而这就被鲍德里亚视为“第四次世界大战”,它就是全球化自我消耗、自我解构的战争——那么这是不是鲍德里亚见证的“灾难性转折”?或许从2001年的“9·11”到后“9·11”,都像是鲍德里亚所说和1929年形成呼应的现代性危机,它终结了全球性这一秩序,它制造了自我解构的敌人,连同“美国”这个现代性的符号,也都开始反对自身。但是,鲍德里亚在接受访谈时,却又指出了个体在其中要有所为,“ 我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仍然存在着某种生命力,某种依然在抵抗着的不可化约的东西,一种形而上学方面的独一性。”
个体的生命力和抵抗精神,是鲍德里亚认为是世界的解药,就像自己的写作一样,不可化约的部分不会被普遍化、综合化或沦为任何标准交换的对象,“游戏还没有结束。这也是我的乐观主义之所在……”所以当个体还具有写作一样的抵抗力量,还在寻找着象征意义,还在可逆性、欲望、想象中构建游戏,那么这个“抛锚”的世界并没有真正走到灾难性时刻,“第四次世界大战”也只不过是一个恐怖主义相关的强烈隐喻——这篇访谈发表于2008年,而鲍德里亚的生命停止在2007年,也就是说,这是他生前对话、生后出版的一篇文章,当个体的生命已经停止,鲍德里亚所说的不可化约的生命力和抵抗精神,也并没有随之而消亡,它继续着游戏。个体生命逝世不是终点,文字还在,写作还在,生命力还在,游戏还在,如果以鲍德里亚所说的可逆性构建一种欲望系统,那么从2008年的最后一篇访谈以时间“可逆性”的方式回溯,是不是会发现那种欲望的激情?似乎是一种巧合,访谈录的最后一篇文章是2008发表,而第一篇文章则发表在1968年——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年代,是不是像鲍德里亚后来所说是一个象征的游戏?
这篇名为《僭越是一种政治行动模式吗?》的文章并不能算是访谈,因为当时参与的人除了鲍德里亚之外,还有贝尔纳·科南、洛朗·科尔纳、弗朗索瓦·戈特雷、勒内·卢罗、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埃莱娜·于里,称为对话似乎更为合适,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无法明确区分这些话分别是谁说的。”这是革命和反革命、左翼和右翼所形成的高压?所以对话者被标注为匿名的ABCDEFG:先是B抛出话题,3月22日楠泰尔的大学生召开大会呼吁法国政府释放两天前因参加反越战活动而被拘押的六人,他们还占领了校长办公室,这一事件就是著名的五月风暴的导火索,B在对话中认为这是一种在“更高层面上进行言说”的表达,它解构了编码,解构了现存的句法和词汇学,这就是一种僭越,“正是这类干扰在我看来是重要的,因为它恰恰摧毁并打破了禁忌。”对于这个说法,一开始参与进来的是ACD,C认为它是以街垒、墙上的涂鸦的方式进行表现和书写,“它们拥有一种具有超现实表现力的诗意内容,而墙面则是明确的元素,是新的能指。”D认为僭越是新的“诗歌语言”,但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在政治话语中如何得到把握;A在让B对“解构”再作阐述之后认为,建制作为镇压,它的显现只能通过“诗歌工作”,“即试图从来自建制、空间、大厅、楼层、门、禁忌的现有材料出发解构语言。”再回到B那里,他认为僭越作为解构不是纯粹的毁灭,而是在编码内部的操作中,“我们走出了意指,进入了意义。”而僭越禁忌就是大学的真实功能。
随着话题的展开,在C说到出现了年轻学生和和工人两种价值系统时,E第一次参与了进来,他认为年轻人已经拥有了新的沟通渠道,“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信息之外,朝年轻工人讲话的更多的是媒体、工具、街道、骚动,以及类似的东西,而非著名的意识形态内容本身。”在B不同意D认为学生系统所针对的是镇压系统而不是剥削系统时,F参与进来,他认为应该修改阶级斗争的传统概念,当工会不再质疑价值系统和等级制度,反而是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异化;而在B说到,“剥削和异化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中展开的形式,而是一些相互交错的元素,异化将会继续,并且发展仍旧深重的剥削。”他建议异化经验和剥削经验要进行统一,G根据这个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部分这些批判工会的人都完全不清楚工会的内部组织……”在这场对话中,他们涉及了僭越的本质,革命的意义,异化和剥削的经验、政治组织的模式等等话题,对“五月风暴”进行了自己的观察,但是要分出他们分别代表谁,存在着难度,看起来B更像鲍德里亚,但是在匿名状态中要给他们重新命名,这样的意义何在?或者这场对话就是一个游戏,就是在匿名的状态中构建可逆性的欲望空间:谁都可能是谁,谁也可能不是谁,可能和不可能就是“可逆性”的最浅显意义。
什么是可逆性?1993年鲍德里亚在接受塞尔日·布拉姆利时说到了摄影给自己带来的愉悦,“那种愉悦?”塞尔日问道,鲍德里亚把摄影的愉悦描述为“沉入一个表层的、明晰的世界”,它不仅是美的而且是诱人的,它是被显现的,也是意欲显现的,"一种物质、一道光线、一个情境、一片风景、也许还有一个轮廓,但没有脸庞,没有相似性,没有意义和心理学……我不得不在其显现的时刻,也就是在它具有意义之前捕捉它。”摄影是主体对一个物体的凝视,也是一个物体让自己被看见的可能,所以和电影创造了神话、场景的“图像”不同,摄影的主体接近零度,也就是说主体消失了,客体成为了必要,这种颠倒就是一种可逆性的表达,而鲍德里亚也罢这样的颠倒看成是写作的本质,“通过写作,你可以终结某物、使其消失,这一消失拥有直接的病毒效应……写作也会直接走向事物的显隐模式。”写作从来不是建构性的,也不是再建构性的,它开启了“一种致命的可逆性”。
2003年鲍德里亚在和奥德·朗瑟兰解码《黑客帝国》时,就认为电影将虚拟变成了可见的幻觉,一切本属于梦、乌托邦和幻想之类的东西都轻易“实现”而展示给了人们,所以即使他的《拟像与模拟》这本书的封面出现在电影中,而且剧组也邀请鲍德里亚参与之后的几部,他也拒绝了,“系统、虚拟、矩阵,这一切也许都将回到历史的垃圾桶之中,而可逆性、挑衅、诱惑则是不可摧毁的。”在这里鲍德里亚认为构建了电影的系统、虚拟和矩阵都是技术呈现的东西,都会最后消失,只有可逆性、挑衅、诱惑则是无法被摧毁的,鲍德里亚的拒绝就是在这些不会摧毁的东西中写作,或者说用写作在维护和制造不可摧毁的可逆性、挑衅和诱惑。写作如此,对于命运也是如此,“宿命唤起了我的激情,但并不是这种功能主义式的、灾难性的宿命。还存在另一种宿命。我指望的是一种可逆的宿命,是一种可逆性的力量,这一力量存在于命运之中,为的是对这些过程喝倒彩,为的是反抗这些过程。”
从1968年到2008年,40年的15篇访谈构成了鲍德里亚的另一种书写,按照洛朗·德·叙泰的说法,这是在鲍德里亚写下作品之外,“一部宏大的口头作品”,它由课程录音、电视节目、广播节目以及无数发表于全世界报纸杂志的访谈构成,他认为口头作品不仅给鲍德里亚带来了愉悦,也给读者带来了愉悦,“除了重新发现鲍德里亚所带来的愉悦,我们在本书中读到的文本也提供了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下,或面对着新颖问题和疑问的情况下发现的鲍德里亚为我们带来的愉悦。”而实际上,访谈和独自著述的作品相比,是即兴的,偶发的,片段的,甚至是被打断的,主宰者永远是发问者,即使有鲍德里亚进入自己阐述空间而深化内容的时候,也会被访问者拉回来,而且很直接进入下一个论题,在这个意义上,这反而是属于访谈者的游戏,带来的是访谈者的愉悦,主客体被构建起来而不再是平等的对话,所以在这里真正的可逆性很少被表现出来,它更是对可逆的阻止,更像鲍德里亚在1991年的访谈中所说的“屏幕”:屏幕不是镜子,不存在屏幕的对面,不存在矛盾的深读,不存在精神,当然也就缺少了指使判断、愉悦、欲望得以可能的场景,你问我答,你说我说,“这里没有反射,只有折射,毋宁说只有一种从一个屏幕到另一个屏幕的折射。”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