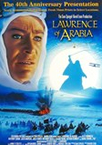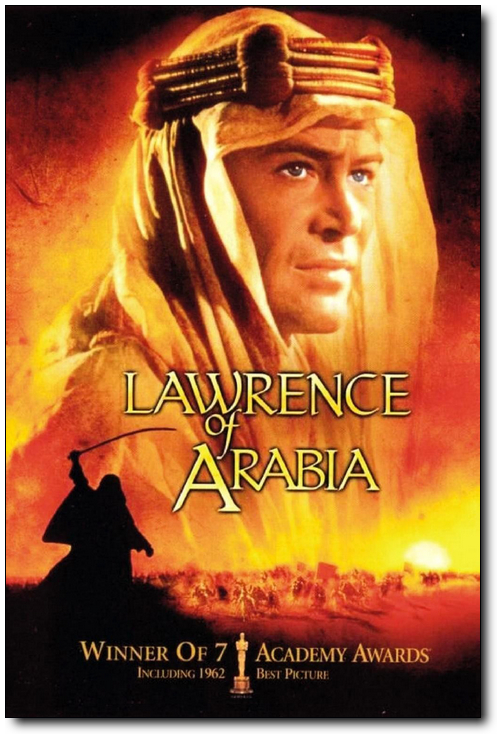2013-07-02 《阿拉伯的劳伦斯》:死于传奇的英雄

他的一生都在蜕变,都在挑战被注定的命运,他的一生都在书写传奇,却被最后的孤独所吞噬——T.E.劳伦斯,他曾是牛津历史系毕业生和英国军队里的文职小军官,他却用二十天时间穿越沙漠成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他给野蛮、贪婪的阿拉伯民族带去了自由和理想的荣光,却无法走出自我救赎之路;他经历了战争经历了枪炮和刀刃的洗礼,却死在一次摩托车的意外事故中;他的故事写在历史文本里,是伟大的纪念,亦是自我的嘲讽,他的一生是英雄的传奇,却也是孤独者最后的挽歌。T.E.劳伦斯(1888-1935),他的名字和铜像被摆放在圣保罗大教堂供后世瞻仰,但是对于冒险、征服、解放和自我牺牲的人生之路来说,“Leave me alone”或许才是他最后的人生注解。
这不是关于奴役和解放的历史叙事,这也不是关于成功和失败的个人奋斗,在战争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是崇高的,也可能是荒谬的,而对于个人来说,任何人都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意味着默默无闻的死亡。当自由和理想最后换来新的殖民和统治的时候,当英雄面对胜利却只想逃避和离开的时候,那些欢呼、膜拜,那些敬佩、瞻仰,以及被捧上英雄宝座的荣誉,到最后都变成了尘埃,跌落在地,宛如那被征服又重新吞噬生命的荒漠,容纳着生与死、爱与恨,以及伟大与渺小。
对于劳伦斯来说,沙漠是他一生的写照,是他个人英雄史诗书写的开始,这里有充满质感的沙丘,有壮美的日出和落日,有辽远的夜空,这里的风景无与伦比,但是沙漠仅仅是背景,它装扮着人生路过的风景,却也暗藏着死亡的陷阱。劳伦斯的荣光的一生从沙漠开始,也在沙漠终结,他升腾和超越以及最后的沉沦和离开都像是沙漠的一种隐喻,从平凡人物到英雄,再退回到普通人,他用四次沙漠之行完成了这样的人生曲线。
作为英国士兵,劳伦斯的职责就是执行命令,而对于他的第一次沙漠之行完全是职业意义上的,“真正的战场不在这里而在西线。”当艾伦比将军对他下命令的时候,西线、沙漠,对于劳伦斯来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或者只是对敌的一个地理坐标。当执行任务时间从六个星期延长到三个月,劳伦斯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沙漠之行会带给他一生的蜕变,也未曾料想背后隐藏的危险和荒谬。他的任务只是去了解麦地那的阿拉伯费瑟王子在那里对于战争的想法,看上去是一次对于任务的简单执行,当他用军人的“敬礼”接受任务,踏上沙漠的时候,他的随从只有一个贝都因的向导,以及带在身边的手枪。对于他来说,沙漠上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这里有落日,有夜空,有贝都因向导交谈中了解的奇闻趣事,甚至,他们在沙漠中狂奔和嬉戏,一切都充满了某种娱乐意义。但是那一声枪响却让劳伦斯陷入了迷茫,陷入了关于生与死,文明与野蛮的醒悟。哈里斯水井在必经的沙漠深处,当贝都因向导从水井里取水的时候,他们原本轻松、欢快和娱乐的沙漠之行一下子改变了,远处的那个模糊的黑点变成了骑士,变成了危险,而当贝都因向导用劳伦斯送给他的枪瞄准他的时候,他却被提前击中。“这是我的水井,哈齐尼人不能在这里取水。”这是这个名叫阿里的人对于此次枪杀行为的解释,在阿拉伯的不同部落里,每一处水井都象征着部落的领地,不容侵犯。哈齐尼向导之死对于劳伦斯来说,是一种价值体系的瓦解,他以为阿拉伯是一个统一的称谓,却隐藏着不同的利益,而在这些利益面前,随时可以杀戮。他对着阿里大叫,并且愤怒地对阿里说:如果战争不停止,阿拉伯民族就永远是可怜的、野蛮的、贪婪的民族。
|
| 导演: 大卫·里恩 |
 |
如果劳伦斯第一次带着向导穿越沙漠是一次冒险的话,那么第二次穿越沙漠欲拿下阿卡巴则是一次征服,这种征服既包括对恶劣大自然的征服,更重要的是对于阿拉伯部落和“游击队”的征服。尼法德沙漠几乎无人能够穿越,这里有无尽的沙丘,有炎热的太阳,有恶劣的狂风,甚至是一条“朝圣者”者之路。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劳伦斯还是义无返顾,用他自己的毅力和勇气,带上阿里在内的50人向着未知的危险挺进。而在行进中,他们几乎不能呼吸,几乎不能休息,而终于有一天跟随他们的贾西姆掉队了,劳伦斯没有犹豫,要返回去寻找贾西姆,阿里劝他不能回头,他说,贾西姆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是天注定的。但是劳伦斯似乎不相信“天注定”的命运安排,只身返回沙漠。而当奄奄一息,几乎丧失了所有希望的贾西姆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看到前来救护的骆驼以及骆驼上的劳伦斯时,他仿佛看到了救世主,看到了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劳伦斯变成了他心中的信仰,也变成了50位阿拉伯游击队心中的英雄和“神”,“没有什么是注定的。”劳伦斯将贾西姆救回来时,对阿里这样说。而对于劳伦斯来说,他解救的不是沙漠中的迷途者,而是那些永远相信“天注定”宿命论的迷途者,而也在这刻,劳伦斯在英雄般的欢呼中完成了自我命名,他成为真正的“阿拉伯的劳伦斯”。
那时,当阿里问他的名字时,劳伦斯告诉他,自己不是艾尔·劳伦斯,只是劳伦斯,那个带有父亲贵族血统的姓被劳伦斯删除了,这是对他自我的一次否定,因为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私生子,父亲没有去母亲就将她抛弃了,所以在他成为沙漠英雄的时候,也告别了自己他带有羞耻的出身,而也只有完成那些英雄传奇般、乃至奇迹一般的事迹才能抚慰他那理想主义者的自尊心。那个夜晚,阿里烧掉了劳伦斯的军装,而穿上阿拉伯酋长衣服的劳伦斯用这样的仪式最终完成了自我命名,他告别了过去的历史,也告别了英国军人的身份,头巾、服装,以及佩戴的短刀都让他成为另一个阿拉伯领袖。而接下去对于奥达部落的指挥才是他最后征服的完成。由于在沙漠里取了奥达部落的水井,50人的游击队同样遭遇部落间的冲突,他率领的游击队武器是刀,而奥达部落的武器是枪,他们骑的是骆驼,而奥达骑的是高头大马。他们的冲突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水井矛盾,而是对于征服的理念,劳伦斯对奥达说,进攻阿卡巴,是为了赶走那里的土耳其军队,只有土耳其人在,你们永远是被统治的奴隶。所以他答应奥达,在攻下阿卡巴的时候,就会获得那里大吧的黄金,金钱,是对于奥达部落最好的诱惑,当最后奥达答应率领自己的部队加入劳伦斯的征服计划时,劳伦斯似乎已经显出了出色的统领作用,而真正深入人心,真正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还有对于贾西姆“法律”意义上的惩罚。在两个部落共同开拔阿卡巴的路途中,贾西姆杀死了奥达部落中的一个仇人,两派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对于奥达部落来说,惩处贾西姆是一个“法律”,是必死的戒律,所以他举起了枪,对准这个他曾经冒死从沙漠里救下的青年,对他说:“我要执行法律。”随后枪声响起,贾西姆被打死,在那一刻,融入阿拉伯部落“法律”的劳伦斯才真正成为阿拉伯部落的一员,尽管他说,我没有部落,才能站在中间调和他们的矛盾和冲突,才能用枪打死触犯“法律”的罪人,但实际上,他已经是阿拉伯法律的执行者,已经不折不扣成为“当地人”,甚至也完全接受了他们“天注定”的宿命论。贾西姆之死,又称为一种被注定的命运,劳伦斯从沙漠里解救他,是一种注定的生,那么这次被枪杀,这是一次注定的死,“让他生,又让他死,这是注定的。”劳伦斯的手主宰了阿拉伯人的命运,这样的征服或者才是信仰意义上的,从装扮到道义,从英国的劳伦斯到“阿拉伯的劳伦斯”,他完成了真正的蜕变。
|
|
| 《阿拉伯的劳伦斯》电影海报 |
这样的蜕变使得劳伦斯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对于阿卡巴的攻击,当奥达在阿卡巴没有发现黄金的时候而质疑劳伦斯是骗子的时候,劳伦斯遵守诺言,答应在10天之内给他五千个金币。而对于劳伦斯来说,攻下阿卡巴只是完成了最初的征服,他又带着法拉吉和杜德离开阿卡巴,前往英国将军艾伦比驻扎的开罗,一方面是为了告诉他们已经拿下了阿卡巴,另一方面要从阿卡巴的征服开始新的征程,或者说阿卡巴只是他解救阿拉伯民族“英雄主义”事业的第一步,所以穿越西奈半岛前往开罗成为他的第三次沙漠之行,这一次的主题则是:解放。在这一次沙漠的穿行中,他丢失了指引方向的罗盘,而恶劣的大自然继续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在途中杜德被流沙吞噬,而劳伦斯眼睁睁看着杜德消失在漫漫沙漠里,或者他只有眼泪只有无奈,他一直是个征服者,但是在大自然面前,他的征服也永远弥漫着死亡。到达开罗之后,劳伦斯并没有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拿下阿卡巴的奇迹在用过将军眼里,似乎无足轻重,甚至在艾伦比将军看来,他成为“不自律、不整洁、不守时”的军人,虽然艾伦比答应为征服阿卡巴的劳伦斯举行授勋典礼,但是说实话阿卡巴对于英国作战战略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他们的目标在土耳其军队驻守的重镇大马士革。而在劳伦斯看来,阿卡巴是他必须回去的地方,那里有他的领袖意义的征服起点,也有对于奥达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从阿卡巴开始,阿拉伯才是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所以他要求艾伦比给他5千兵器,给他金币,以及武器、车辆和大炮,将阿拉伯人武装起来,才是他心目中阿拉伯走向独立、自由的真正开始。而对于艾伦比将军来说,他代表的英国利益认为:给他们大炮,就等于让他们独立。”所以对于劳伦斯来说,征服的意义被无情解构了,而依靠英国的力量似乎永远不能让阿拉伯人独立,所以接下去劳伦斯的行为从一个精神领袖慢慢成长为一个实干的英雄,他带领阿拉伯人炸毁土耳其军队修建的铁路,破坏他们军事物质的运输,也抢夺火车上的各种战略物质,那些钟表、衣服、雨伞,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充满了好奇,而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阿拉伯人的这种掠夺实际上预示着他们仍然没有走出野蛮、可怜和贪婪,仍然是一个弱小民族。
而对于劳伦斯来说,悲剧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来自英国这样一个“文明国家”,但是他又是阿拉伯部落的一个英雄,他见证了他们的野蛮和落后,他更想将他们带向一个文明的彼岸,但是个体的力量永远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几次沙漠的征服,他几乎都是赤手空拳,用自己的勇气和毅力完成了沙漠之行,完成了英雄的自我定义和阿拉伯人的膜拜,但是这样的征服和解救完全变成了疯狂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为了不使自己变成野蛮人,他崇尚仁慈反对杀人,所以不管是对于贾西姆的惩处,还是眼睁睁看着杜德被流沙吞噬,虽然都和自己有关的死亡,甚至他将他们的死亡归结为自己的过错,在他心里充满了无奈,充满了对于天注定命运的喟叹,但是反对杀人并不能成全他心目中那个伟大的复兴计划,在炸毁土耳其列车的时候,死亡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尽管他挥舞着双手大叫“Stop!”但是阿拉伯人还是用他们从土耳其军队抢来的枪炮打开杀戮,而想制止杀人的劳伦斯也被幸存的土耳其伤员打伤了右手臂,在那一刻劳伦斯才意识到自己的仁慈在战争中多么的荒谬多么的幼稚,那一刻伤痛的不是手臂,而是自己的心。美国记者班德利问劳伦斯两个问题,一是他们在战争中希望获得什么?二是沙漠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你?劳伦斯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自由,而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说:因为沙漠干净。
但是,沙漠是不是真的是干净的?从他第一次带领向导穿越沙漠的时候,就被告知,在沙漠里只有两种人可以得到享受,一种是贝都因人,另一个则是神,而你两者都不是。劳伦斯似乎从几次的沙漠之行中慢慢成为这两种人,但是实际上他既要想成为贝都因人的领袖,融入他们,又想成为神,解救他们,所以对于真正的沙漠,他是个人的英雄,他尴尬地见证了死亡,他也实施了无奈的死亡,最后他甚至也加入到了杀戮的队伍中,将那些土耳其士兵杀死在沙漠里,双手沾满鲜血的劳伦斯才意识到沙漠是永远不会干净的。当在实施炸毁土耳其火车的行动中,由于意外,法拉吉被引爆器炸伤,劳伦斯为了不让法拉吉落到土耳其军队的手里,无奈举起了枪将法拉吉打死,看上去这仍然是拯救,但是对于曾经充满仁慈之心的劳伦斯来说,是一次颠覆。而之后因为假装阿拉伯人而被土耳其军队抓获的时候,劳伦斯在受到肉体的惩罚之后,这种颠覆才真正深入他的骨髓。尽管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但是劳伦斯永远有着不能更改的身体特征,蓝眼睛、白皙的皮肤、流利的英语,土耳其将军说,人不可能永远穿着制服,身上的伤永远证明他的军人身份,所以在遭受虐待的肉体惩罚之后,劳伦斯的精神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他对阿里说:“我已经完了,我不是阿拉伯人,我是个平凡人,我要回到艾伦比那里,我要做轻松的事。”从英雄变成了俘虏,对于劳伦斯来说,这是荒谬的复兴之路,这是疯狂追求自由换来的代价,要做一个普通人颠覆了他心中的那个伟大计划,而跌落到地上的那一刻,他完全又变成了一个柔弱的英国文职小军官。
其实,对于劳伦斯来说,这只是个体的一次牺牲,但是他的梦还没有到最后溃败破碎的境地,直到他见到大马士革的那一幕幕,才让他真正看到了失望,看到了自我的弱小,看到了拯救的荒谬。劳伦斯还是穿着阿拉伯服装,比艾伦比军队提前到达大马士革,并且在费瑟王子的授权下成立了阿拉伯议会,临时接管大马士革,但是议会的办公场地只是混乱,只是争吵,像一个大集市,像又打上了那种野蛮、可怜和贪婪的烙印,而实际上作为英法合约的一个部分,大马士革仍是合约中被殖民的一部分,没有工程师,没有消防队,没有电话,而那里的旗帜也仍然是英国的旗帜,在开罗的将军们曾经承诺“英国不想统治阿拉伯”,曾经答应“大马士革可以作为阿拉伯议会所在地”的时候,他们真的会把自由还给阿拉伯人吗?对于劳伦斯来说,他钟爱阿拉伯的原始与干净,他希望带给他们自由,也希望借此摆脱令他沦为边缘角色的英国社会,实现他英雄主义的梦。但是大马士革的争吵、混乱和充满殖民主义的气息让他彻底绝望,费瑟王子说:“年轻人制造战争,战争的本质就是年轻人的本质,未来的勇气与希望。老人则维持和平。和平的罪行是老人的罪行,不信任与戒心。” 实际上,所谓的战争即和平,所谓的自由也是新的统治。“沙漠里的血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实际上也宣告了劳伦斯沙漠之梦的终结。“我再也不去沙漠了。”劳伦斯的绝望变成了一种麻木,是的,解放大马士革是他率领的阿拉伯人提前一步,但是他仍然是一名英国人,有着蓝眼睛、白皮肤的英国人,有着文明社会洗礼的英国人,也会向英国国旗敬礼的英国人。当劳伦斯最后脱下阿拉伯领袖的服装,重新穿回英国军装的时候,关于自由的梦想,关于解放的计划,关于英雄的征战都回到了原点,沙漠还是那个沙漠,那个干净与肮脏同在,死亡与救赎共存的沙漠,而阿拉伯也还是那个充满暴力的争斗,充满复兴渴望的沙漠民族。当一切又恢复如初,对于劳伦斯来说,“天注定”就完全变成了自我命运的写照,望着那些远去的阿拉伯人,望着远去的沙漠,坐在军车上的劳伦斯心头只有一句话:Leave me alone。
劳伦斯是孤独的,他是孤独的私生子,他是孤独的士兵,他是孤独的英雄,他也是孤独的失败者,那个沙漠像是他命中注定走不出来的世界,门口永远竖着那块牌子:危险,就像若干年后他骑着疯狂的摩托车在路边看到这一块牌子,但是内心的不羁以及对命运的抗争仍然是他自我超越的动力,但是天注定的悲剧是他一生走不出的宿命,那辆他最爱的摩托车Brough Superior载着他走向未知的地方,他曾说:“对速度的追求是人类的第二兽性。”所以在摩托车的速度中,他死了,如同所有已经写好的传奇。
从冒险到征服,从解放到自我牺牲,劳伦斯的四次沙漠之行分别指向麦地那、阿卡巴、开罗和大马士革,这是他一生的路线图,而这些经历将他的人生之路慢慢割裂开来,而其实,大卫·里恩也用这部电影完成了自我的一次命名,作为他一生最高的成就,《阿拉伯的劳伦斯》由最好的剧本、最好的表演、最好的摄像和最好的音乐构成,被一个最严苛的完美主义的导演用天才和魔法熔合成了一部长达四小时的巨幅史诗。获1962年第35界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音乐、最佳剪辑和最佳音效共七项大奖、并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和最佳改编剧本三项提名的这部电影也创造了电影史上的一个传奇,但是对于这样的传奇,对于后世可以瞻仰的某种经典,《阿拉伯的劳伦斯》却在现实中又用断裂解构了这样的传奇,216分钟的电影成为个体阅读史上最长的电影,从最初的这里,到之后的这里,还有这里,以及最后的这里,不断地缓冲、停止,以及继续,就像劳伦斯的人生一样,在伟大与孤独,在经典与荒谬中被割裂成不同的片段。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