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22 公交车上的理想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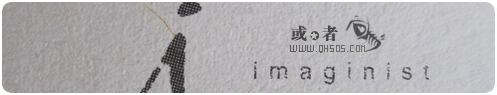
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在与你们个别交谈。
——《博尔赫斯谈话录》
引文来自《博尔赫斯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之一种。早上6:10的时候,它就在我的手上,我没有打开这本书,它是封闭的,是平面的,是形式的。而这一句写在封面上的话,在这个冷清的早晨,正被我以右手拇指和食指夹住的方式接触着,它不逃逸,不隐藏,直接面对着户外、街道、空气和手指的温度。而句子其实是片段的,1980年3月,博尔赫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对话时,这一句话在关于沃尔特·惠特曼的“是否这样,我们是否在此孤单相聚?”的引文和疑问之后,在博尔赫斯语气稍作停顿和省略符号之后,转向另一个意思:“我们是孤单的,你和我。意味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那并不存在,当然是这样。甚至我自己也或许根本不存在。”
但是那个引文和转折是被关闭在第150页中,打不开意味着它只在1980年的时间里说话,只在被关闭的“理想国”里说话。在这个雨后的清晨,其实站在公交车站台里,仿佛是被封面的这句话注解了,空空的街道,空空的天空,空空的车站,不存在人群,人群是一个幻觉,所以当只有一个句子裸露在封面上的时候,没有人交谈,没有人相聚,甚至也没有人引用。
没有人群的早晨,世界仿佛就是一个人。公交车缓缓驶进车站,车门打开,上车刷卡,听到的是一声清脆的“的”,走进车厢,里面除了司机没有一个乘客,一个早晨,一个车站,一节车厢,一声“的”声,以及一个乘客,都是单数的叙事。我坐在老弱病残专坐上,看着打开窗户的外面世界,心里记下的是那些呈现复数状态的数字:K9路车,从上车到下站一共16个站点,行驶时间大约35分钟。
是第二次乘坐公交车,是一次之后的另一次。本来都是步行从家到单位,行走、穿越、快步,是一个人的路线,是一个人的状态,甚至那些流淌的汗,那些看见的物和人,那些转弯、直行,以及打开的Endomondo数字,都是和一个人有关。但是昨天出门的时候遇到了大雨,终于在撑着伞的场景里等待一辆公交车,而今天没有雨,但是有着一本385页的书,一个“想象另一种可能”的理想国,在一个老弱病残的座位上,在空空荡荡只有一个乘客的车厢里,其实手拿着这本理想国,让那句引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总是有一些不合时宜。我尽量使它像我昨天撑起的那把伞一样,变成随身携带的工具,遮风挡雨,而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
一个站点之后是另一个站点,上来几个乘客,从西到东,从南往北,公交车也依次穿过街道,路过站点,行驶在自己的路线上。上来的是孩子,是奶奶或者外婆,是上班的女人,是去医院的老人,他们坐在我的前后左右,彼此不认识,我抱着那本书几乎是塞进了衣服里。窗外变幻的是不同的风景,车上出口处写着“下车请按门铃”,每当一个站点到达,广播里总会提示“开门请当心”、“下车请注意安全”,而在斑马线前,也都会礼让行人——或者在另一个时间里,步行的我就走在属于自己的斑马线上,看见一辆从未坐过的公交车,看见它停下,让我先行,而那时我失望了抬头看看公交车的司机是否微笑着点头。
“想象另一种可能。”公交车的理想国似乎并不只是拿在我的手上,那些温馨提醒,那些斑马线前的礼让,似乎都在想象之后变成了现实的一幕。我坐在老弱病残的位置上,拿出那本书的时候,其实瞥见了关于理想国的那个大大的标识“i”,流线型,像一个运动的人形,正在书脊的位置站立,“i”是Imaginist,也是“I”,是想象,也是自我,是的,一个文本的“理想国”就在我的世界里,不存在的人群,其实不是寂寞,不是幻觉,而是从人群中可以分离每一个自我,可以确定每一个存在,他在用手指夹住的书本里,在公交车的某一个专坐上,也在礼让的斑马线前。
理想的“I”,真实的“I”,我从公交车的座位上站立起来,从不认识的人群中抽身出来,从“开门请注意安全”的广播声中下车,拿着“理想国”,拿着博尔赫斯的谈话,拿着一句被自己不断看见的引文,重新走向一个人的目标——35分钟,是公交车车厢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时间,是从等待的起点到抵达的路程,其实也是自己曾经步行的时间,一个人,一群人,其实是契合在这个早晨,“是否这样,我们是否在此孤单相聚?”当惠特曼的这句话被抽出在引文之外的时候,疑问其实就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人群终会不断下车,不断散去,不断离开,而唯有那个理想国一样的”I“,在1980年的3月,变成一个瞎眼的老头孤独的沉思。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