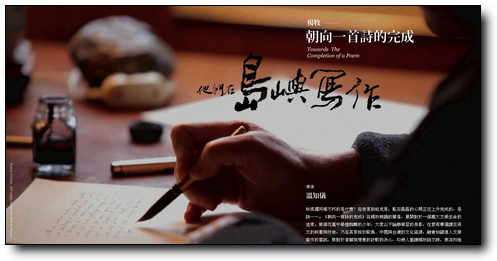2015-07-22 《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星是惟一的向导

他掀帘,我凝神佯作不知
接吃犄角边上子,棋路
使的是风月荡漾的招式:你从何处来?
——杨牧《妙玉坐禅》
我是“认识自己归路”的我,他是在凝神佯作不知中掀帘的他,而在使用“风月荡漾的招式”的棋路中,“你从何处来?”纠缠勾斗的棋局似乎不是三个人的世界,我和他之间或者之外的你,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之后的第二人称,是一种分离,还是一种共存?是一些生,还是一些死?其实,那棋盘无非是宇宙,而那棋子,也是满天星斗,佯作不知也罢,风月荡漾也好,最终是要落下来,前胸炙热的身,还是冰雪在负的心,都随着那凌晨的满天霜,而最后寂灭成“朝姑苏飞坠”的命运。
谁是妙玉?谁又在有我有他却又无我无他处坐禅?你从何处来,亦是你从何处去,空留我和他,也空留一个棋局。而当一首诗变成如宇宙的浩淼与无际的时候,总会有一颗星的位置,佛珠缠绕是一种救赎还是一种束缚?肉身挣扎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迷失?在中间的那个人是独自舞蹈的你,一生都在我和他的托辞里“突围”。突围成诗,成文,成人,那一颗星便是一个人的向导,也是一个人的归宿,那个人叫杨牧。“有一个人,有一个动作”,这是杨牧设下的一个棋局,那里有“妙玉坐禅”,也有“郑玄寤生”,那里有“林冲夜奔”,也有“马洛饮酒”,中国古典,或者域外经典,历史典故,或者小说虚构,那个人总是在做着那件事,而经典,而无限。而对于一切的书写者来说,一个人其实是诗人,一个动作其实是写诗。
|
| 导演: 温知仪 |
 |
对于杨牧来说,宇宙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空间。时间的维度里,他学习古英文,喜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他以回溯的方式寻找文学之源,寻找诗歌之根,莎士比亚、《诗经》,仿佛就是诗歌宇宙中的那些年轮,“我自己思考,思考这圈圈怎么长大。”年轮是时间的印记,而在杨牧的眼睛里,它们都长出了诗歌的枝叶。而在空间的维度里,他用世界眼光为自己找到那一束光芒,选择比较文学就是架设中西文化的那一座桥梁。所以在无限之时间和无限之空间里,杨牧的宇宙迸发出诗歌实验的力量。爱荷华大学的创作班,柏克来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台湾《联合报》做副刊编辑,以及台湾大学任教、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创办、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任院长,对于杨牧来说,是对于宇宙之光的探寻,也是营造文学宇宙的努力。
|
|
| 《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海报 |
宇宙的奇幻,就在于变化,就在于多元,就在于创新。他在人称代词“面具”世界里寻找一种游戏的快意,他在“安达路西亚”掉落的声音里制造跌宕,他在《岁末观但丁》的韵律中挤压自己。“已经快20年了,我在形式上的企图比在主题上的企图还要更清楚一点,我就是要用文字来捕捉钢琴或者小提琴等乐器的音乐。对于抒情诗来说,音乐是第一位的。”在2009年的花莲太平洋诗歌节上,杨牧这样解读自己的创作之路。形式上的探索比主题的阐述更清楚,并非是一种形式主义,而是要在形式之美中营造诗歌的音乐之美,意境之美。世界是音响的世界,诗歌是音律的诗歌,这是书写所追求的一种极致,却也是要走向一种无穷和无限。
无穷而无限,在诗歌的意义上是永恒。“我想把汉字挂在一个最好的位置上来创造文学,文学不分这个文学那个文学,文学应该是更普世的东西。”就像那个宇宙中的星辰,也需要在浩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国界,没有时代,对于杨牧来说,这却是诗歌的永恒意义,当日文翻译上田哲二朗诵杨牧的《花莲》,配以日据时代的画面,那些孩子,那些山水,那个穿红衣的女子,是日据时代的复活,却在原住民语言、客家人语言中达到了融合,多族群文化是对于地域的跨越。当华盛顿大学的德文系教授Jane Brown朗诵杨牧的德文诗集《Patt beim Go》中的诗歌时,世界的维度、诗歌的意象在不同的语言中被扩展。“他兼取中西方诗歌的特点,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他的诗中呈现的世界主义,让我们有一种回到家的亲切感。”
从世界回到家,从无限回到一个点,其实世界主义对于杨牧来说,也同时意味着对于当下的人文关怀。在岛屿写作,注定要转向台湾的现实,而对现实的质疑却总是带着超越地域的形而上意义。《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直击台湾问题,却并不用愤怒的语言探讨公正,“早熟脆弱,如一棵二十世纪的梨。”《十二星象练习曲》里是肉体有关的体制,是时间有关的情欲,“饥饿燃烧于奋战的两线/四更了,居然还有些断续的车灯/如此寂静地扫射过/一方悬空的双股”“丑时”是NNE,是3/4E,是露意莎,是四更“虫鸣霸占初别的半岛”,象征和隐喻,数字和符码,以及那一片竹林,不是神秘,是隔离,而在组诗以“天干地支”制造的时间序列中,那些超越和挣扎却在互相照明、互相回响的状态中。那以奇莱山为坐标的《奇来前书》和《奇莱后书》却像是一次宗教意义的救赎,在台湾历史的流转中寻找一个引领者,寻找一种寓言的言说方式。
当下是真实的返回,当下却也是虚幻的逃避,对于杨牧来说,世界的喧嚣恰好让他能够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那种种的过往,最后却是甘享一种孤独,那一匹衰老的兽,抑制潜伏在诗人乱石磊磊的心里,而那善变的花纹,只是“族类的保护色”,“凝视/遇远的行云,向往/天上的舒卷和飘流”,在一种风雨随意鞭打的现实里,“他委弃的暴猛/他风化的爱”。华盛顿大学那一处绿树掩映的房子,是杨牧书写的地方,没有人惊扰,只有诗歌存在;那台湾的寓所里,他一个人静静活在书房里,即使那只叫黑皮的狗也从不吵醒午睡的他。“他选择宁静的世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他的内饰太狂烈了。”小心翼翼地退守在自己的领地里,是一只孤独的兽,是独享“风化的爱”。
他们说,杨牧扩展了世界,他们说,杨牧制造了让年轻人却步的“杨牧障碍”,他们说杨牧应归于博学诗人之列,他们说,杨牧的“影响焦虑”是他的生命呈现出一部最好的诗集。而这首诗是一个人的诗,只是一个动作的诗,《一首诗的完成》是过去式,所以在无限而无穷的宇宙中,必须要《朝向一首诗的完成》,写诗没有完成,它只“朝向”未来,朝向未知,朝向永恒。而在这宇宙之中,那颗星是惟一的向导,“淡忘了你,淡忘这一条街道/在智慧里,你是遇,掀我的悟以全宇宙的渺茫/你的笑在我的手腕上泛出玫瑰”。
“爱是一种神明,何况春天已经来到。”杨牧坐在那里,读着自己的那首诗,即使有人掀帘,即使有人出招,即使有人叫你叫他叫我,诗歌却响起“一块马蹄铁,两块,千万块马蹄铁”的激烈撞击声,妙玉坐禅,郑玄寤生,林冲夜奔,马洛饮酒,但是现在的一个人,现在的一个动作,叫做:“杨牧写诗”。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907]
思前: 《捉妖记》:跨界是一场冒险
顾后: 公交车上的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