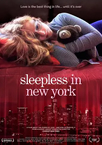2020-12-13《纽约不眠夜》:没有人能活着走出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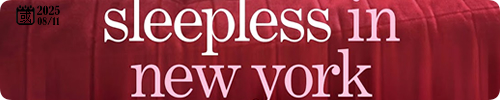
11:20的航班从杭州起飞,两个小时后降落于广州白云机场;辗转地铁3号线到组委会指定入住的宾馆,匆匆整理一番,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出宾馆,行走在天河北路上,一切都是陌生的存在……出发前的一晚炒面和飞机上的所谓米粉早已经被消耗了能量,饥饿难耐,广州之行完全是从肉体开始的一次寻找:先是过街看到了一家正开张的饼店,买了老婆饼,一口下去没有丝毫饱感,于是又沿着体育东路前行,经过了恒大作为主场的天河体育场,再辗转之后,看见了“非遗小食街”,下台阶进去,门口的广告设计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进去之后才发现只有几家店铺;退出时已经夜幕降临,广州正华灯初上,行走已累再加上饥肠辘辘的我终于看见了装潢典雅考究的“和府捞面”——门口的广告语是:“一家开在书房里的捞面”,不仅“原汤养身”,而且“书房养心”,果然店内餐桌旁布置了书架,书架上有可翻阅的图书,门帘上的“觉”字更有某种超凡脱俗的禅意。
不管是“书房养心”,还是“觉”字的禅意,其实在饥饿的肉体面前,这些精神意义的向往都变成了背景,文化层面上的食粮都只是摆设,肉体和精神似乎完全被隔离了,而这一种感受竟也提前演绎,成为一个多小时后上映的《纽约不眠夜》的相关主题:当一个人遭遇被甩式的失恋,看上去是付出了爱的灵魂在痛苦中无处可栖,实际上却只是一种生理上的疼痛,或者正如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研究表明的,他们所患上的是一种欲罢不能的“爱情上瘾症”——导演了《战地摄影师》的克里斯蒂安·弗雷此次关注的“旅程”,切入的是失意灵魂之旅,最后却变成了无法走出而陷入在理智与情感无休无止纠葛的正常“病态”中。
失恋,无疑是人类正常的情感状态,但是当一个人失恋而痛苦,他是真的不想走出来,还是找不到突围的出口?弗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开始招募失恋者,开始用镜头记录他们失恋后的生活,打印的招募广告张贴在纽约街头,他要求应征者能带上一份自己失恋时写的日记来面试,最后弗雷挑出了三个面试者,开始了对人类这一“旅程”的探寻。很明显,弗雷以招募的方式寻找失恋者,并且用他们自述的方式倾听他们失恋的故事,他的目的是发现失恋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但是这种发现是一种预设,因为当他从很多志愿者中选中了三个应征者,并且结合海伦·费希尔的研究成果,只是为了说明他早就拟定好的主题,在纳入自我体系的记录中,其实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发现,他只是要把科学研究成果展示出来而已。
这是一种静态的、非逐层深入的解析过程,所以纪录片本身也显得极为静态:从三个对象失恋后焦虑、不安、哭泣等不同反应的呈现,到人类学家对这一现象背后原因的揭示,始终是一种已知的状态,在这种已知中,不管他们曾经经历了什么,还是以后会遭遇什么,一直没有从业已得出结论的成果中有一种递进、逆反,也没有因为主人公无法忍受这样的“自虐”式生活,他们也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实,每个人有不同的故事,每个故事有不同的情节,每种情节的背后都是走出来的渴望,但是,他们在痛苦、反抗、陷入、再痛苦、再反抗、再痛苦中,一次次循环,而92分钟的时间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最后每个人都无法走出“Sleepless”的永劫之中,连弗雷也在这样的静态轮回中把这场灵魂失意之旅变成了某种堆砌。
静态的“Sleepless”无非是因为失恋者根本无法让灵魂安然走出这样的泥潭,因为肉体所代表的生理层面拒绝走出。他们都是被动接受了分手的命运,当主动权不再自己这里,一定是不解,一定有无奈,也一定会品尝痛苦。“第23天,又一次在凌晨三点醒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她不在,他会想我吗?”从失恋第四天开始,艾莉总是在问这样的问题,问题里他和她,虽然也有“我”,但是这个我是被抛在了现实之外,只有他和她进入到了未知却在一起的生活中。这无疑就是一种隔离,艾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曾经对她说“永远爱你”的他抛弃,又为什么会选择另一个女人,所以她一遍又一遍问:她比我好在哪里?在自己独处的房间里,在深夜无眠的房间,艾莉不是在寻找答案,而是在自我折磨。他们曾经是那么相爱,曾经一起开启了大峡谷之旅,一起在日落时朗诵诗歌,曾经以为会永远在一起,但是命运无情地把艾莉推向了无法走出的深渊中:她面对泪流满面的自己写下失恋日记;她在无眠的夜晚“住”在沙发上辗转反侧,她和有限的朋友视频恍惚睡去之后又被自己苦醒……
| 导演: 克里斯蒂安·弗雷 |
不明白分手的原因,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也不想走出来面向未来,这是艾莉的状态,而自由翻译者迈克尔何尝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和同居的女友已经分手两周了,他也陷在无法自拔的痛苦中,那些曾经的美好占据了回忆的时光,而面对现实,他的痛苦在于发过去的信息总是没有任何音讯——她像是从他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当这种消失越发彻底,迈克尔想要维系的渴望则更为强烈,他每次开车总是要经过同居过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故意要绕开,甚至还想知道她在那里干嘛,甚至希望有一天能碰见她。不断地强化自己这种意识,迈克尔仿佛编织了一种虚幻的场景,而对于另一个失恋者来说,从一开始她就陷入到想象之中。“红玫瑰”是一名舞蹈演员,她是在科尼岛的美人鱼游行演出时遇到心仪的他,当初的邂逅,当初的相识,当初的亲吻,似乎都在“红玫瑰”的世界里变成完美的存在,当她把他看成了此生挚爱,他却离她而去,仅仅是邂逅?“红玫瑰”却用爱来命名,当他消失之后,“红玫瑰”用配饰在床头做了一个小神龛,祈求着他能再次回到身边。
艾莉的泪水,迈克尔的失意,“红玫瑰”的痴情,都让他们无法走出,尽管艾莉通过买花装点房间来转移注意,尽管迈克尔想用健身、学大提琴和写作来缓解痛苦,尽管“红玫瑰”和女伴们通过设计个性舞蹈服装来充实生活,但是这一些改变总是脆弱,一转身,他们又回到了痛苦的状态中,只不过,艾莉的失恋日记又变厚了一些,迈克尔经过的次数又增加了一些,“红玫瑰”祈祷的方式有了新的变化。他们在改变,他们在抵抗,但是在弗雷的镜头中根本不起作用,而这种难以自拔难以走出的状态其实并非是他们真的不愿走出,而是被某种“大脑回路”控制着:艾莉同意人类学家弗希尔的建议,接受了一次实验,这个实验就是通过扫描的方式观察失恋者在看到自己无法忘记的人时的脑部活动——虽然是一张照片,但是当艾莉躺在那里,当她的眼前出现了前男友的照片,她的大脑异常活跃,和看到其他没有感觉的男人照片时的脑部活动不同,艾莉在“看见”前男友时兴奋的,而且,弗希尔发现,尽管艾莉已经失恋,但是看到照片兴奋时的脑部活跃区域和强度几乎和恋爱时一样。——甚至失恋者释放的兴奋物质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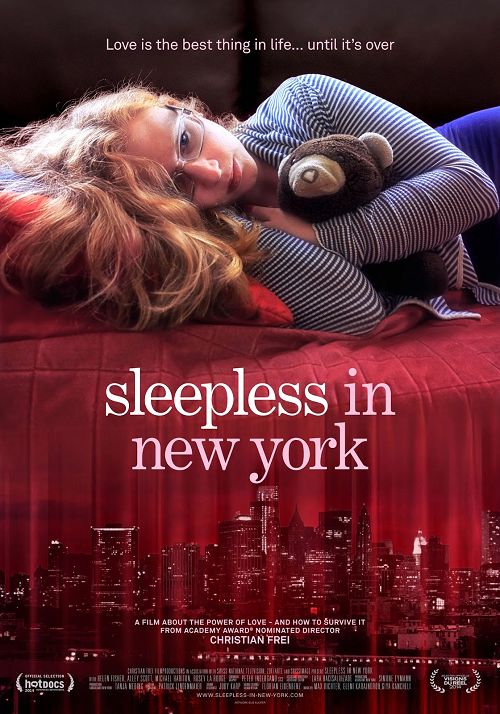
《纽约不眠夜》电影海报
这种有些违背常理的实验结果被弗希尔命名为“挫折吸引”,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越遭遇挫折大脑的活跃程度越强,释放的兴奋物质也越多,所以艾莉、迈克尔和“红玫瑰”在失恋的状态中,无法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让自己走出来,反而越陷越深,而且,这种“挫折吸引”看起来是灵魂层面的自我折磨,实际上是生理层面的一种疼痛,也就是说,在经受情感痛苦的时候,脑部与牙疼有关的岛叶皮层也异常活跃——这是一种“爱的疯狂”,也是一种“爱情上瘾症”。所以在实验作为支撑,在人类学专家得出结论的现实面前,毋宁说,失恋后走出深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弗希尔在观察人类日常性暗示和爱的举动之后,得出了人类大脑回路中形成三个层次的研究结果:第一层是纯粹的性欲,第二层则是一种浪漫的爱情,第三层便是基于占有的爱,也正是爱的分层存在,当一个人遭遇了失恋,无论是“挫折吸引”还是生理疼痛,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都会上演艾莉、迈克尔和“红玫瑰”式的痛苦,而弗希尔并没有提供让他们走出来的办法,相反,为了更形象生动理解这一实验结果,她用一句话概括了建立在生理意义上的灵魂拷问:“没有人能活着走出爱情。”
活着,是一种只和肉体有关的生理式存在,爱情只能建立在其上,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无论是热恋还是失恋,唯一指向就是活在爱情中,所以在弗希尔的这一结论中,在三个志愿者的现实展现中,弗雷以平面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生活,不逃避是一种追求客观的态度,但是在不深入的主题挖掘中,在灵魂生理化的解读中,在无休止的痛苦循环中,消极抵抗不仅无法转变成积极生活,甚至在“没有人能活着走出爱情”的定论中,一切都变成了无意义,纽约也永远在不眠中。
观影完毕,似乎肚子又开始有了饿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