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13 《梅兰芳》:难以逃离的纸枷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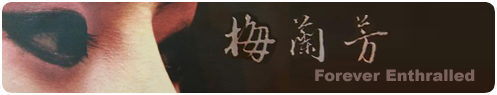
秋天过渡到初冬,北方冷空气正长驱直入,和这来势汹汹的萧杀相映衬,这不是一个抒情的夜晚,在《梅兰芳》两个半小时略显沉闷的演出中,这个夜晚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怀旧之夜。
邻座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后座是一对老夫妻,这样的环境显然为这部电影作了极好的铺垫,在他们的心目中,梅兰芳不仅仅是一场电影,更是他们所缅怀的那个时代,经典,隽永,还微微有些伤感。 梅兰芳属于时代,是偶像,是经典,更是一个文化的意象,任何人心目中的梅兰芳都变成了符号,一不小心的阐释就可能是一次亵渎的冒险,所以陈凯歌才会如此小心翼翼,不再张扬地把一个戏剧伶人的悲情藏匿起来,当然也可以理解深陷“艳照门”的阿娇的戏份会如此毫不吝惜地删除。
梅兰芳属于时代,是偶像,是经典,更是一个文化的意象,任何人心目中的梅兰芳都变成了符号,一不小心的阐释就可能是一次亵渎的冒险,所以陈凯歌才会如此小心翼翼,不再张扬地把一个戏剧伶人的悲情藏匿起来,当然也可以理解深陷“艳照门”的阿娇的戏份会如此毫不吝惜地删除。
中规中矩,和贺岁片其实挂不上多少关系,“解读凡人梅兰芳”这是陈凯歌想突围的角度,然而,明显流露出黄昏心态的陈凯歌在解读一个凡人梅兰芳的实践中却陷入了二律背反中,把一个平面的黎明当成是凡人梅兰芳的影像,不仅使梅兰芳的命运远离了作为艺术大师的惶惑不安,更使整个故事变得散乱平淡,没有章法,没有高潮。
那把轻易可以弄破却不能撕破的纸枷锁,不仅戴在“凡人梅兰芳”身上,更是戴在距离拍摄《霸王别姬》15年之后的陈凯歌身上。
“谁毁了梅兰芳的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这是邱如白对孟小冬的恳求,在梅孟恋情影响大师事业的时候,邱如白试图还原一个创造时代的梅兰芳,在经历辞职到改戏,到策划梅兰芳推入市场,以及之后的恳求孟小东、导演枪杀梅兰芳,邱如白是一个比梅兰芳更懂戏更执著于戏的疯子,他把梅兰芳推向了神殿,是梅兰芳造神运动的推手,没有邱如白就没有梅兰芳,但是,邱如白只是一个符号,是梅兰芳从伶人变为大师,又从大师变为凡人的符号,但是“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的”,这是梅兰芳的悲剧,他永远无法走出那一纸的枷锁。
与孟小冬的爱情是梅兰芳的一次摆脱纸枷锁的挣扎,然而,他的真爱被扼杀了,孤单是梅兰芳成其为大师的代价,蓄须拒唱,摒除了邱如白“只要梅兰芳在唱,京剧就还在”的最后的诱惑。最后在自我酿造药物的麻痹和痛苦中,才得以逃避而返朴到一个平凡的梅兰芳,但是对于梅兰芳来说,这一切的平凡却丧失了其作为符号的一切,尽管挣脱了纸枷锁,但是梅兰芳死了。
《梅兰芳》从总体结构上无悲无喜,《死别》、《生离》、《聚散》三个篇章是陈凯歌对梅兰芳传奇一生的选择性记忆误读,简单地把梅兰芳爱事业、爱感情和爱国家逐一如教科书般匆匆道来,感觉总导演不是陈凯歌,而是梅葆玖。而且,在主题深化中,陈凯歌显然对于凡人梅兰芳的塑造显得急功近利,与青年梅兰芳的锋芒相比,中年梅兰芳在在黎明的演出中,变成了一个木讷、软弱、害怕的梅兰芳,整天用稀粥诠释生活变奏的平面化人物,只有儒雅,没有灵气,没有大师的风范,而《梅兰芳》里最值得看的两个人,十三燕和邱如白,一个是伶界高人,一个是京剧推手,都富有生命的尊严,甘愿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付出毕生的心血,却都是悲剧收场。
影片三分之一的篇幅,那个自由洒脱、聪明主动的梅兰芳是可爱的,而后面三分之二,看到了陈凯歌某种对梅兰芳的同情,同情一个再也无法挣脱、无法归去的梅兰芳,枷锁已然上身。倒是从这个角度说,黎明演得拘谨,尴尬孤单,像是陈凯歌内心的一束黄昏的折光。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