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10《呐喊》: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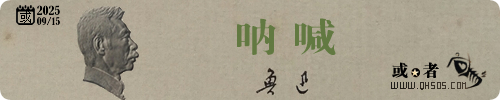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
是恐怖的疑问,也是寻找的希望,因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大抵还是有的;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但是孩子也可能已经被吃了,或者正在被吃,那么,没有被吃的孩子是不是也“或者还有”?于是,大声疾呼着:“救救孩子……”或者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可以有人救孩子,这双重的死亡都是那么微弱,仿佛一问便是无声的寂静,便是没有月光的黑暗——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和吃过人的孩子一样,或者是没有了;能救孩子的人,和不能救孩子的人一样,或者也是没有了。
疑问和希望,都变成了双重的死亡:孩子被人吃了,孩子也吃人——孩子被孩子吃了,这个世界似乎只存在着逃脱不了的命运:既吃人也被吃。一种普遍的存在,一种共同的命运,正如这两册的狂人日记一般,“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作者只是隐去了名字的“狂人”,日记中的人名、村人名字也都易去,也“不著月日”,在不被命名的世界里,在不具体指向的故事里,人人都是“语颇错杂无伦次”的狂人,人人也都是“多荒唐之言”的狂人,人人都是害怕被人吃了的狂人,人人也都是吃了四千年人的狂人。
患了“迫害症”,狂人先是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吃人的人,赵家的狗在“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中看了“我”两眼,是不是就是朗的亲眷的““海乙那”,甚至在月圆之夜成了饿狼;出门看见赵贵翁,眼色很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而且周围七八个人在交头接耳议论我,他们张着嘴,对我笑,“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一种吃人的感觉袭来,我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和我有仇?似乎只有二十年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那时候的古久先生很不高兴;仅仅是这个原因?于是看着村子里所有人似乎都开始对我笑,开始张开嘴:街上的女人打他儿子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仿佛是在看我,仿佛青面獠牙的一伙人哄笑起来;想起前几日的佃户来告荒,告诉大哥说,村里的一个大恶人被大家打死了,他们还挖出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还有陈老五,送的饭里面有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女人说“咬你几口”,一伙人青面獠牙地笑,佃户说大恶人被打死而且吃了,加上陈老五饭菜中的蒸鱼,狂人的世界里,“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而且不仅是外人,大哥说要请何先生诊一诊,想着那何先生是不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而且临走时对大哥说:“赶紧吃罢!”大哥让我去何先生那里,何先生让大哥“赶紧吃吧”,原来合伙吃的人里,还有自己的哥哥;大哥要吃人,而且想起四五岁时,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后来妹妹死了,哥哥是不是“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一开始是看到周遭的人都露出白厉厉的牙齿,说着“吃了”的话,所以对于狂人来说,自己也会成为被吃的人,翻开历史,历史没有年代,但都歪歪斜斜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但是现在当知道大哥也是一伙也会吃人,狂人便知道自己是吃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不是因为二十年前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一脚,因为那一叫根本没有踢翻整部“吃人”的历史,而是这四千年的历史中都是被人吃也吃人的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而在四千年的历史没有翻过那一页的时候,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真的还有吗?不被吃的孩子真的能被救吗?当“救救孩子”成为一个疯子的荒唐之言,到底是谁吃掉了最后的死亡?到底是谁制造了“迫害”?人人都是害怕被人吃了的狂人,人人也都是吃了四千年人的狂人:孔乙己是狂人吗?站在咸亨酒店前喝酒而穿着长衫唯一的人,说出“窃书不能算偷”的读书人,告诉说“回字有四样写法”的人,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人,连名字都是古旧书里的命名,完全是被旧礼教毒害的牺牲品,可是因为“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被打折了腿,来喝酒还说是“跌断”的,最后用手走着离开了,在众人的说笑声中留下残缺的背影,而最后,“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孔乙己尚且没有吃人,但独独被自己和他人吃了,“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一种不确切的确切,一种模糊的不模糊,活着和死了大约也没有区别,因为他们都是被“吃了”。小栓也死了,吃了那人血馒头依然没有见效,他死于肺痨,肉体之病,医治的是人血馒头,而人血馒头背后则是一个生命,革命党人夏瑜被砍头了,夏瑜被人吃了,小栓吃了人,吃了人血馒头的小栓和被用血做了人血馒头的夏瑜,最后都死了,最后也都葬在了一起,“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人血馒头是药,药却不能救身体,反而是以人死为代价的,而在这个吃人和被吃的过程里,华老栓的愚昧、康大叔的残忍、红眼睛阿义的冷血、以及夏四奶奶的痛苦,构成了这个吃人世界的冷寂,和小栓坐在桌前吃饭是一样,“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一样,都是病态。
和小栓一样,《明天》的宝儿也终究没有看见“明天”,单四嫂子梦见宝儿病好了也只是一场梦,“明天醒过来,自己好好的睡在床上,宝儿也好好的睡在自己身边。他也醒过来,叫一声‘妈’,生龙活虎似的跳去玩了。”中焦塞着的病,用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去找何小仙,烧了纸钱,也用板凳和衣服作抵,最后的梦还是一场梦,宝儿死了,于是,世界比任何时候都冷寂,“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白光》里的陈士成也死了,梦里是墙上的榜文,最后变成了乌黑的圆圈,第十六回考试依然没能翻身,“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但那白光却照了进来,也是古旧的梦,因为据说祖上是巨富,屋子底下埋着无数的银子,白光引导着他找寻祖宗的秘密,但是除了那“斑斑剥剥的像是烂骨头”的东西,还有什么?而且,“上面还带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齿”,也像是做了吃人的准备,跟着白光的陈士成终于“到山里去”了,而第二天日中,有人在万流湖里发现了一具浮尸,“仵作也证明是生前的落水,因为他确凿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
白光从古旧的世界里招来,是死亡的召唤,吃掉陈士成的是传说中巨富的祖宗,是一心为功名却责怪考官“有眼无珠”的欲望,或者就是那个不断吃人的封建体系。当然也有没有被吃掉也不曾吃人的人,他们站在吃人和不吃人的中间地带,既不敢进也不敢退,就像《头发的故事》的辫子,是像古人那样是身体的一个器官,从脑袋到生殖器再到髡,都刻印着吃人的惩罚?还是既不想做遗老又不是顽民,但都是难做的百姓,“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所以一部头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吃人的历史,“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后来的革命或者不革命,辫子也成了标志,但是剪了头发便是改革?“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风波》中九斤老太感慨:“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连体重从九斤到了下一代的七斤,又到了更下一代的六斤,但是这“一代不如一代”不只是出生体重问题,更在于辫子的地位问题,七斤没有了辫子当然非常危险,赵七爷轻易不穿的竹布长衫也穿了出来,他质问的是:“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而且他说现在有人保驾皇上,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张大帅,但是七斤却有些模糊,一方面颇为不平,“辫子呢辫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龙庭。破的碗须得上城去钉好。谁能抵挡他?书上一条一条写着。入娘的!……”另一方面却看到赵七爷又坐着念书了,而且辫子盘在了顶上,也没穿长衫,“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
皇帝要不要做龙庭,辫子要不要盘在顶上,在“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中,中国人的吃苦、受难和灭亡根本就没有改变,死而不死,不死而死,就如吃人和被吃,都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常态。而阿Q呢,当他画圈“画成瓜子模样”,当他游街示众也没“唱一句戏”,当他被枪毙是“坏的证据”,是不是真的变成了革命党?他看到的是四年前的那只饿狼,“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饿狼要将他吃了,而四年前手里还拿着一柄斫柴刀,可以壮着胆回到未庄,而现在倒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本来未免要杀头,要游街,要示众,为什么还要画很圆的圆圈?为什么还要手里拿着斫柴刀?为什么还要区别出好和坏?为什么要做革他们的命的革命党?
是因为阿Q起初是想要做一个人,一个住在未庄土谷祠里没有家的人,一个只给人家做短工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一个姓名籍贯“行状”都有些渺茫的人,该怎么成为一个人?连《阿Q正传》也“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立传,大约需要开首写道“某,字某,某地人也”,但不知阿Q姓什么,说姓赵,和赵太爷一样,赵太爷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于是阿Q第二日自己也模糊了;名字叫阿Guei,是阿桂?阿贵?没有人知道;籍贯呢?“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如此,只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而“正传”,也是因为文体卑下,也是因为“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从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套话里取出来,与字面相混,也顾不得了。
不配姓赵,名没人知道,籍贯有些觉不定,只有正确的“阿”字,阿Q无疑被抽离了具体的存在,而成为一个符号,于是这个符号用那些“怒目主义”、“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成为具体的人:头上的“癞疮疤”也学着忌讳,不准说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亮”和“烛”都避讳了;精神上的崇奉,是想“我的儿子会阔很多”,进了城又鄙视城里人,“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被人打了,便在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心满意足走了,当众人揪住他的辫子让他说:“人打畜生!”阿Q用手捏住自己的辫根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于是反败为胜,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了两个嘴巴,打完之后又心平气和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怒目主义和精神胜利法,是阿Q创造了另一个自我,一种分裂感是为了让自己有存在感,是为了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而对于小尼姑以及吴妈的态度,更是在男人意义上找到了位置,摸着小尼姑新剃的头皮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阿Q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这便是一种怒目主义,因为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但是在小尼姑的头皮上开始感觉“飘飘然”,礼教上不应该有,那也是女儿的可恶,“假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阿Q便不至于被蛊,又假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阿Q便也不至于被蛊了”,但终究对吴妈喊出了:“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一刹中的寂然,阿Q的确第一次作为一个大胆的男人出现,但是未庄是不允许这样阿Q成为一个人,更何况成为一个男人,赵太爷给他立下了五条严惩措施,赔罪、担费用、不准踏入赵府的门、不准索取工钱和布衫,不准和吴妈接近,就是在逐步取消人的意义,取消男人的位置,一刹而寂然,也就这一刹的人之光,最后归于寂灭。
似乎被被未庄所不容,阿Q进城了,进城回来了,阿Q似乎与向前不同了,腰间伸出的手上是银和铜,穿的是新夹袄,挂着大褡裢,还叫着“现钱!打酒来!”这是阿Q的中兴史,“这结果,是阿Q得了新敬畏。”但是他还是没有成为一个人,他说见过革命党被杀头,是完全作为麻木的看客,“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终于当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的那艘乌篷船开到了赵府的河埠头,举人老爷来乡下逃难,革命党便进了城,“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见过革命党被杀,听说革命党要进城,对于阿Q来说,是要成为革命党还是躲开革命党,但是他的推理逻辑是: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让举人老爷这样害怕,让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慌张,于是阿Q快意地要加入革命党,“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造反有理,革命有理,阿Q又成了一个人:先是想象着自己变成革命党,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接着把辫子盘起来,还插了筷子;又要去和革命党结识,去找“假洋鬼子”——但是他的这个计划又被取消了,因为他们不让他革命,“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但是取消了革命的可能,阿Q是自己命名了革命,“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终于被抓了,没有革命的革命党,被取消了革命的革命党,“他们没有叫我”的革命党,不是赵的姓,没有名字,不知籍贯,阿Q再一次成为一个符号,还是在“怒目主义”和精神胜利法中活着,还是在“怒目主义”和精神胜利法中死去,最终也成为一种示众,在看客的热闹中散场,“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枪毙了,是阿Q的死,是被人吃掉了,看客连杀头也麻木了,只想听唱一句戏,就像阿Q曾经看到革命党被杀头,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都在一起,是狂人看见的世界,也是狂人被当成“迫害狂”的世界——苦难、麻木、冷寂、死亡,中国人在四千年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履历上,不断地吃着人,也不断被人吃着。
“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在荒原之上,是不是真的没有“救救孩子”的希望?看到的是一间铁屋子,里面绝无窗户,许多熟睡的人们不就要被闷死,当从昏睡入死灭的时候,是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的,但是当有人大嚷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惊起几个清醒的人?“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荒原中是有铁屋子的,铁屋子里绝非从昏睡入死灭的人,只要叫喊,便有希望唤醒,便有可能毁坏,“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所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是有的,因为还有“鸭的喜剧”,“夏雨一降,院子里满积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的叫。”所以,“救救孩子”也会有人喊出,因为“一件小事”总是浮在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因为“故乡”里看见了希望,“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