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10《无岸之河》:我来,主要是向时间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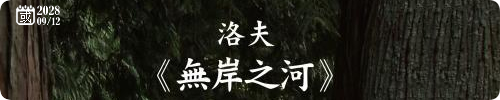
1995年的《诗魔之歌》,打开了通往洛夫,甚至通往台湾现代诗的入口;2014年的《洛夫诗全集》,以整体的方式窥见了死亡之凝视——在《他们在岛屿写作》三辑共18部纪录片介绍的作家中,洛夫对于我来说,是最全面被阅读的写作者,但阅读仅仅是从文本打开而进入的状态,王婉柔的《无岸之河》则以影像的方式接近一个诗人,一个更具体、更鲜活以及更多元的写作者,但是就像“无岸之河”的片名所揭示的,对洛夫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还原,真的可以抵达那条“无岸之河”?
黑屏,传来声音:“诗十行,每五行一节……关于死亡,生命和战争,这是一种庄严的表达方式……”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种特殊的出场方式,所有的黑屏都在衬托着声音的传递;之后洛夫走进了金门的武杨坑道,从光明里走向黑暗处,然后是跟拍他的身影,站立,指着坑道的另一个入口,“像进入了时光隧道……”从黑屏到光影,从光明到黑暗,王婉柔在开篇是用心的,它连接起了诗歌和影像、过去和现在、活着和死亡,在黑与白的对话中、行进中、转换中,指向洛夫诗歌的永恒意象:时间——这曾是洛夫在金门军中的生活,这曾是洛夫写作《石室之死亡》的原始意象,这曾是洛夫见证和想象死亡的地方,时间穿过黑暗,穿过光明,再次穿过黑暗,终于来到了站在前面的“当下”,但是,当洛夫在诗歌中说“我一无所惧地躺在时间里”,王婉柔真的能唤醒一个诗人关于时间的全部意象?
从文本到影像,洛夫无疑变成了一种鲜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一种串联起回忆的轴线,洛夫以具象的方式行走其间,王婉柔就是以完全具象的时间向洛夫致敬,就像洛夫在《漂木》里的一句诗:“我来,主要是向时间致敬。”时间是老照片上的湖南老家,坍塌的房子指向了1944年,就是在那一年,洛夫的记忆中是“跑警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以及被炸出的大坑,以及遍地的死人,以及对故乡的逃离;时间是1951年9月12日来台湾的那一则日记,“来台湾,发热,感觉太寂寞了……”人生地不熟,但是再无返回去的可能,于是和痖弦、张默开始创办《创世纪》,于是考取了外语学校,于是去了金门,于是开始创作《我的兽》,“睡在防空洞里,一切都地下化了……”时间1965年11月去越南战地,目睹了暗杀行动,写下了《西贡诗抄》,两年后回到台湾,在现代诗的论战中回归传统文学;时间当然也是1988年回到湖南老家,在鞭炮声、诗朗诵声中回到故乡,却再也听不见那蟋蟀的叫声,那小时候曾游泳的河流,现在行驶着挖沙船,“变了,一切都变了……”时间也在1996年3月30日去往了温哥华,住在痖弦家里,相识60多年的老友再次重逢,而从2000年开始,洛夫在温哥华开始了《漂木》的写作——漫长的低潮期过去,洛夫终于写下了“向废墟致敬”的诗句,“我低头向自己内部的深处窥探/果然是那预期的样子/片瓦无存/只见远处一只土拨鼠踮起后脚/向一片废墟/致敬……”
时间串联起了洛夫的回忆,时间成为王婉柔的叙事线索,时间当然也是对洛夫诗歌的一种解读,但似乎仅仅如此,时间是被看见的时间,时间是被标注了数字的时间,时间是透过文字被解读的时间,但是洛夫想要致敬的时间究竟在哪里?从文本的世界里走出来,仿佛是从黑屏中听到的那个声音,它是具体的,它是个体的,它甚至是丰富得超过任何言说的注解:洛夫说起《创世纪》初期的时候,没有经费,大家自掏腰包才被这个刊物办了起来;洛夫回忆自己在金门的经历,每天听到炮声传来,死亡压迫着自己,但却还是要写《石室之死亡》,“这是一种揽镜自照,甚至是对于现实的报复”;洛夫和痖弦再次相聚,夫妻俩包饺子迎接前来做客的痖弦;妻子琼芳,儿女莫非和莫凡说到洛夫去越南的情景,那时的莫凡刚出生不久,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而洛夫和家人也别离了整整两年;还有拿放大镜看洛夫现代诗的林亨泰,说他就是“阿波利奈尔”……影像里的洛夫和他们都是鲜活的,他们在说,他们在回忆,他们把时间变成了被翻阅的文本,渐渐的,洛夫的当下取代了文本,甚至取代了诗歌,那些诗变成了对象,变成了目标,音乐人钱南章、研究者刘纪蕙、李瑞腾、诗人尹玲评论洛夫和他的诗,于是,向时间致敬变成了向洛夫致敬,甚至变成了向“洛夫”这个符号化的标签、作者致敬,而诗歌本身的意义模糊了,缺失了。
| 导演: 王婉柔 |
所有的纪录片可能都会陷入这样一种尴尬,关于洛夫,关于洛夫的诗歌,关于洛夫诗歌中的时间和死亡,关于洛夫诗歌的现代主义,在具象化的解读中一定指向了确定性的存在:石室之死亡和武杨坑道有关?《自焚——记西贡老高僧》和西贡的战争有关?《漂木》真的指的是那一根漂浮于水上的浮木?这些都在王婉柔的镜头里,拍摄而成像,便成为了对洛夫诗歌的理解入口,但是像在纪录片里的洛夫一样,他甚至变成了一个不爱多说的人,是内向也是内敛,或者自我言说可能就是一种误读——洛夫对自己也不想过多的解读,那个“洛夫”式的洛夫绝不是出现在镜头里确定的意象。
但是王婉柔显然无法驾驭洛夫诗歌中真正内在的东西,当一切都变成影像的呈现,影像化意味着表象化,表象化也意味着浅显化:从《我的兽》到《石室之死亡》,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关联?从叛逆的石室到回归的《长恨歌》,洛夫在其中又为什么必然进行转化?《漂木》的世界是死亡还是新生?“而我确是那抹被锯断的苦梨,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引用洛夫的诗歌,成为不同章节的过渡,这是王婉柔的一种文艺范,但是这种文艺范只可惜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并没有深入到洛夫的诗歌世界,同样,“凡是敲门的,铜环仍应以昔日的炫耀,弟兄们俱将到来,俱将共饮我满额的急躁……”文字的背后到底有着洛夫怎样的内心争斗?这亦在引用中失去了可能深入的多元视角。
“我来,主要是向时间致敬。”洛夫一直在向时间致敬,也在向着时间中的自己致敬,时间里的生和死既无可逃脱,也无可超越,但是诗歌让时间返回内部,变成自我的一部分。从《石室之死亡》到《西贡诗抄》,时间中的死亡的确变成了洛夫对残酷命运的报复,在《石室之死亡》序中洛夫这样说,所谓报复,就是在命运的死亡中感受到残酷,而这样的死亡包含着母性之死、肉体之死、信仰之死、秩序之死等各种死亡。但是死亡绝不是一种毁灭,1998年回湖南故乡,不是就听到了那一声声的蟋蟀叫声,不是可以回忆和哥哥趴在窗台上看漫天飞雪?到了2000年的《漂木》,身在异国他乡对于洛夫来说也不是死亡,而是对自我生命的重新审视:“一根木头罢了”的过往里是“民离散而相失”,是“去故乡而就远”,是“出国门而轸怀”,这东迁、流亡和远行都刻在那根木头的身上,那根“把麻木说成严肃/把呕吐视为歌唱”的木头曾经写满了一种谎言,但是在漂泊之中,变成了散落在沙滩上的骸骨,是行将腐朽而夜夜揽镜自照的木头,当那一声断裂的“咔嚓”响起的时候,木头就嵌入了体内,天地合一,木人合一,木头变成了骨头,变成了坚挺的器官,变成了广场上的旗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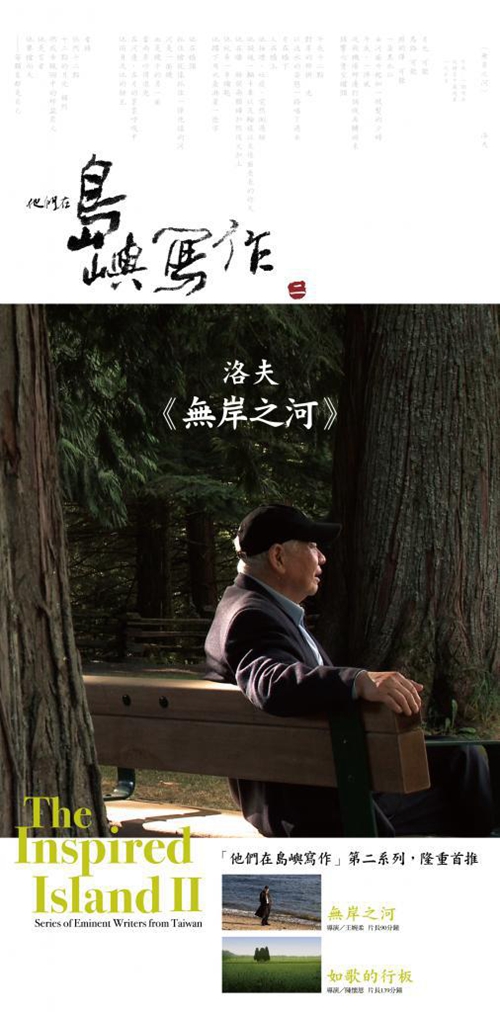
《无岸之河》电影海报
死亡是时间的断裂,重生是时间的叙事,在《漂木》中洛夫从那漂浮的世界里寻找到最终极的四个命题:致母亲、致诗人、致时间和致诸神,对应着母性、诗性、史性和神性,在母性、诗性、史性和神性的再寻找、再创造中,一根漂木在时间和生命的意义上完成了意义的追寻,但是这并非是一种终极意义,所谓的突围,所谓的自我,所谓的死亡,所谓的时间,它们的最后走向必将是一个废墟一样的存在,所以《向废墟致敬》便成为漂木般人生的最大领悟,最彻底的救赎,而这种和神性、物性、人性共存的状态也是时间的终极意义:“我来/主要是向时间致敬/它使我自觉地存在自觉地消亡”。自觉便是接近真实,接近生命的意义,那“一无所惧地躺在时间里”的也绝非是一个肉体,而是像一本书的永恒。
王婉柔用最后具象的废墟代替了洛夫的“废墟”,用具象的木雕代替了“漂木”的重生,或者也用具象的洛夫代替了那个诗人洛夫、作者洛夫,洛夫诗中的那一句:“他们都来自我,我来自灰尘。”也许也是对这个被具象化、影像化的自我的一次逃离。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