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4《而已集》: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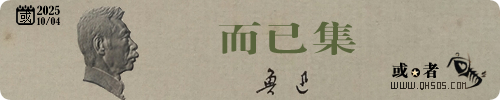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小杂感》
这是“妻性是逼成的”中国,这是“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的政府,这是“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的现实,当一九二七年的一切在变与不变中行进,当南中国的鲁迅在革与不革中思考,“小杂感”是不是还未能探出那可以向前的方向?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广州,鲁迅在南北中国的奔波似乎在寻找革命的方向,但是在冷嘲的专制之后还是沉默的共和,当武士刀指挥着武士还有文人,当犬儒的刺苟延了自己的生命,当凉爽的秋夜有人自杀却还怕大海的汪洋,那发生的一切是不是还是一个循环?
曾经看见了许多的血和许多的泪,于是有了杂感;后来“泪揩了,血消了”,但是“屠伯们逍遥复逍遥”,于是只有“杂感”;后来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而已”而已,是一声叹息,也是一种愤怒!八句话的题辞曾经出现在《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里,当再次出现在《而已集》变成“而已”而已,它们似乎都在同一种呼吸里变成鲁迅的喟叹:续编的续编,“而已”而已,回应着永不消逝的“逍遥复逍遥”,在反复和轮回中,无论是题辞中的杂感,还是“小杂感”,都指向了关于革命的循环疑惑中。
共和革了专制,却为何沉默?为何还有“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的遮蔽?“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革新最终是不是只是为了阔气?可是,“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在现实里,“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笑声中有死亡,疾病中有死亡,凉爽的秋夜中也有死亡,而自杀的甚至“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似乎还没死;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相通的是:“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在杂感的世界里,有讽刺,有无奈,有愤怒,有呼喊,而对于革命,那复杂的链条里似乎并没有唯一的出口,是革命,是反革命,是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与反革命,反革命与革命,杀与被杀,被杀与杀,革命是反“反革命”的反革命的革命——所以这是一个“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循环,永无止境,永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纠葛和错乱中,于此,鲁迅说了一句:“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否则”的拒绝是不是一种个人对于革命的清醒立场?
所以对于一九二七年在南中国的鲁迅来说,“而已”而已的杂感,关键词是“革命文学”,但是这个关键词可以拆分为两部分:革命和文学,又在两个层面上变成杂感:社会和自我。革命之前,总是需要被革命的东西,那是中国还没有彻底改变的国民性:西洋人的脸上有着多余的东西,那便是“兽性”,而中国人只有下巴,当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当听了有些醉心的说话,便将下巴挂下,将嘴张开,不雅观而且精神上少了一样什么机件,那便是兽性,“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但是现在的广州和上海一样,他们只是修养着他们的趣味,甚至电影一开始电灯一熄灭,连下巴也看不见了;报载女附中主人不许剪发女生报考,甚至有一处鼓吹减法的,后来被军队攻入,把剪发女子拔去头发,还割去双乳,“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忧“天乳”》)”连“英国人的乐园”香港也受到影响,检查员胡乱翻开皮箱戳破纸包,把里面的小刀看成是凶器,把生得太瘦的人看成是“贩鸦片”的,这无非是高等华人对低等人的呵斥,“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再谈香港》)”……
人寿有限,“世故”无穷,这边也是要对世故革命的缘由;而还占据着“公理”的那些人,反倒成了革命的主将,他们拿走了公理和正义,他们成了“正人君子”,“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但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鲁迅问的是:“公理”几块钱一斤?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是“交了好运了”,被升为“首领”,“……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闲话》里把“首领”的帽子戴在鲁迅头上,于是甲说:“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于是乙说:“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是“首领”而且有“大义”的旗,“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辞“大义”》)”生生地把自己推向了“战略”高度,于是鲁迅感慨道,从前在背景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一个海边,只有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
在成为首领手拿义旗而“有些阔气”的现实中,鲁迅是被革的“首领”,而他当然是要革他们一下的:在《“意表之外”》中,他说自己的骂对于被骂者是大抵有利的,“天下以我为可恶者多,所以有一个被我所骂的人要去运动一个以我为可恶的人,只要摊出我的杂感来,便可以做他们的‘兰谱’(朋友),‘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了。”这是“咱们一伙儿”的谬论;“假如有一个人在办一件事,自然是不会好的。但我一开口,他却可以归罪于我了。”这是把坏话都推给鲁迅自己倒干干净净的一派,“我又不学耶稣,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所以还是要论战,骂是骂被骂者获利的骂,譬如高长虹,曾真正得到过指导和帮助,但是获利之后反过来谩骂鲁迅是“世故老人”,说自己是太阳,还把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转而又咒骂:“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于是鲁迅“赞叹”太阳:“他还润泽,温暖,照临了你。因为他是喷泉,热,太阳呵!(《新时代的放债法》)”于是,在一种嘲讽中鲁迅说看见了“新时代的新青年”身边藏着许多账簿,而对于“身败名裂”又怀着天大的恐慌,于是鲁迅关上门塞好酒瓶捏紧皮夹,“这倒于我很保存了一些润泽,光和热——我是只看见物质的。”
被革的“首领”要革获利的无耻之徒,也要革打着人性旗帜反对平等的人性论者,梁实秋认为“人”字根本上应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子的意义太糊涂,聪明的,愚蠢的,女人,男人,三教九流都是人,“近代所谓的男女平等运动,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男女的差别。”所以真正的平等就是尊重人格,“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平等就是承认不平等,因为那是自然的不平等,由此,鲁迅抨击这是为了“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也,胃口有差别,正如“人”字也有差别。这“胃口论”是针对梁实秋的“人性论”的,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辩》中说,文学应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长久,鲁迅反问,这种“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无非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论,难道中国的历史论也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另外本质的问题是:“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人出的汗都不一样,有香汗、臭汗,怎么会有不变的人性?“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文学和出汗》)”
反讽的“胃口论”,抨击的“人性论”,鲁迅被革成为“首领”,也有了革的想法,但是对于身处南中国的鲁迅来说,个人的被革和革命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在这个国家层面的革命问题上,鲁迅的疑问是:什么是革命?如何革命?在《黄花节杂感》中,对于黄花岗烈士的纪念似乎是变淡了,继而是忘却了,“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这是不是革命的后遗症?而这后遗症在孙中山的遗言里便成了“革命尚未成功”——是革命成功而被淡忘,还是革命尚未成功需要继续革命?在鲁迅看来,革命成功是暂时的事,革命尚未成功则是无止境而“止于至善”的事,“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需要怎样的培养?需要不赏玩不攀折不摘食,让其逐渐生长最终开出幸福的花果来。
革命尚未成功,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一种判断标准,而“革命文学”,不仅和革命有关,也和文学有关。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四一二”事件发生之前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里做了演讲,谈到了“革命时代的文学”,他认为“大革命”和文学之间存在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都是针对社会种种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第二阶段是大革命时代,文学没有了,“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第三阶段是大革命成功之后,社会状态缓和了,生活余裕了,这时候产生的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这是革命讴歌派,“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但是另一种文学则是一种革命挽歌派,“吊旧社会的灭亡”——而在演讲中,鲁迅认为中国还没有这两种文学,既没有对新制度的讴歌,也没有对旧制度的挽歌,因为革命尚未成功。
四月八日的演讲,似乎预言了四天之后的那次从革命走向反革命的事件,但其实也是对于革命常态的一种态度,“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这便是“止于至善”,而要革命,并不需要革命文学,首要的是革命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而革命文学实际上就是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在直接标题为《革命文学》一文中,鲁迅强调了“革命人”的意义,“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因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怎样成为一个革命人,怎样创作平民文学,怎样看见血管里的血?在七月十六日广州知用中学演讲时,鲁迅认为读书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读书,另一种则是嗜好的读书,“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所以对于青年来说,真正的读书方法是和社会结合起来,走向社会也在社会中实践,革命文学需要的是革命人,革命人需要和实社会接触,这种实践论也是鲁迅自己的选择,“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而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完全可以看做是鲁迅为“革命文学”在发声。
魏晋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群雄纷争的乱世,但也创造了文学上的奇观:曹操是一个英雄,鲁迅认为曹操虽然专权,但是他尚刑名、尚通脱,影响到文章风格,便是清峻和通脱,所以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大师”,“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到了曹丕的时候,文学走向了自觉,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文章的风格是华丽、壮大;之后出现了一个人,叫何晏,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另外则是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他吃的要不是寻常的药,是名为“五石散”的药,这种药有毒性,需要寒食,只有一样东西例外,便是酒——无论是晋人“不鞋而屐”还是“居丧无礼”,都和这药有关,但他们有钱,“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而在名士之外,则有竹林七贤,他们喝酒成瘾,完全是反礼教的典型,名士吃药和七贤喝酒,构成了两道不同的风景,“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反礼教,也因此被杀,被杀,也越狂放,之后则出现了平和的田园诗人,陶潜便是晋末的代表,虽然是田园诗人,但是他对于世事是没有遗忘和冷淡的——魏晋文章,从自然状态的清峻和通脱,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华丽、壮大,再从名士对于药的痴迷而开创风格,到“竹林七贤”以酒为乐反对礼教,梳理下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鲁迅那里又归回到了实践派,人不可能超于人世间,所以文章也不会超然独立,“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酒杯里装着的是酒,无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而至于反革命,其实都难以脱离社会现实——不是不变的人性论,是总是在变革的阶级论,于是“而已”而已的杂感不是悲观主义,而是目光向前的战斗主义,于是鲁迅大胆、犀利地在一九二七年“豫言”了这个需要永远革命的中国的一九二九年:
·科学,文艺,军事,经济的连合战线告成。
·正月初一,上海有许多新的期刊出版,本子最长大者,为——文艺又复兴。
·正月初三,哲学与小说同时灭亡。
·有提倡“一我主义”者,几被查禁。后来查得议论并不新异,着无庸议,听其自然。
·谣传有男女青年四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人失踪。
·《小说月报》出“列入世界文学两周年纪念”号,定购全年者,各送优待券一张,购书照定价八五折。
·美国开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决非卢梭所及。
·绑票公司股票涨至三倍半。
·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险,仍旧束胸,家长多被罚洋五十元,国帑更裕。
·有革命文学家将马克思学说推翻,这只用一句,云:“什么马克斯牛克斯。”全世界敬服,犹太人大惭。新诗“雇人哭丧假哼哼体”流行。
·茶店,浴堂,麻花摊,皆寄售《现代评论》。
·赤贼完全消灭,安那其主义将于四百九十八年后实行。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