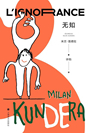2023-08-19《无知》:异乡人中间,找到一个姊妹

人们赞颂珀涅罗珀的痛苦,而不在乎卡吕普索的泪水。
——《2》
购入一本书,是在7月7日,合上一本书,是在8月19日,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一个文本被拥有、被激活,以及被阅读,似乎只属于和文本有关的读者的事。但是,中间却是一个巨大的死:2023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在巴黎去世,享年94岁——在去世一周前选择购买这本书,不是一种预言,在逝世一个月之后完成阅读,也不是一种怀念。
但是当一种沉寂之后的死被夹在拥有和阅读之间,米兰·昆德拉的符号意义似乎被凸显了。这是米兰·昆德拉“遗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从《缓慢》到《身份》再到《无知》,是对“身份”的遗忘?是一个在“缓慢”中展开的遗忘?遗忘的终点是“无知”?当《无知》走向了最后的遗忘,疑惑于这本书对于作者的“遗忘”:以前在米兰·昆德拉的前面会写上相应的国籍,1981年之后创作的著作被标注的是“法国”,2019年米兰·昆德拉重新获得了捷克国籍,但是这本创作于2003年的作品,在中文版本中却未标注任何国籍——不是流亡状态的法国作家,也不是回归之后的捷克作家。
国籍变成了一种无,这种无或者就是一种“无知”,而返回这个夹着死亡的文本,似乎也是关于流亡和回归“无知”的故事。伊莲娜就是流亡者,从一九八九年离开捷克之后来到了法国,来到了巴黎,二十年的时间她在这里结婚,她拥有了工作、住房,她适应了生活,甚至当丈夫马丁去世之后她重新结婚,和瑞典人古斯塔夫又组建了新的家庭,一切都让她成为了法国人,流亡便成为了归宿,可是,当她二十年后有了回到捷克的机会,是不是意味着流亡生涯的结束?是不是带着久违的希望以及一切美好的希望回到那个称为祖国的地方?但是,在好友茜尔薇面前,她却无法告别这里的一切,不仅仅是就业、住房有关的实际问题,“我在这儿已经生活了二十年。我的生活在这里!”
而是所谓的回归,甚至在国际政治大背景下所谓的“大回归”,是不是新的一种流亡?在说到祖国的时候,伊莱娜的确有着某种触动,那几个字给她带来了一种力量,她闪现出了旧时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大回归”激励之下呈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记忆,也是祖先的记忆:“那是与慈母重逢的游子;是被残酷的命运分离而又回到心爱的人身旁的男人;是每人心中都始终耸立的故宅;是印着儿时足迹而今重又展现的乡间小道;是多少年流离颠沛后重见故乡之岛的尤利西斯;回归,回归,回归的神奇魔力。”的确,对于流亡者来说,唯一的目标就是回归,回归也是对于流亡身份唯一可能消除的机会——米兰·昆德拉抛弃了纯粹小说叙事的手法,在故事展开之中插入了带有个人情感的评述,他说“回归”一词实际上有多重表达,有的包含着“痛苦”,有的需要增补“对过去,对逝去的童年,对初恋的怀念”的补语,但不管如何,回归都不是纯粹的从原路返回,古希腊悲剧中的尤利西斯是最伟大的冒险家,也是最伟大的思乡者,但是当他在卡吕普索那里生活了整整七年,当卡吕普索深深爱上了尤利西斯,这个伟大的思乡者的回归也是一种痛苦,他回到了故乡,杀死了向妻子求婚的人,最后回到了妻子珀涅罗珀身边,但是他真的重新拥有了一切?
因为尤利西斯流亡的生活已经变成了安逸的生活,快乐的生活,他和卡吕普索整整七年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和珀涅罗珀同床共枕的时间,所以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尤利西斯的回归,赞颂珀涅罗珀用自己的痛苦等待丈夫回家,却从来没有在乎过卡吕普索的泪水——实际上,不管是珀涅罗珀的痛苦还是卡吕普索的泪水,对于尤利西斯来说,都不是自己可以做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流亡之后的回归或许是新的流亡。从尤利西斯的悲剧回到伊莱娜的现实,米兰·昆德拉实际上将这个人类的悲剧归结为制造流亡的时代本身。对于捷克来说,20世纪就是流亡的历史,它由三个“二十年”组成:一九一八年在一战结束后获得国家独立,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丧失了独立;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引入的革命开启了捷克第二个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是解放的终结;一九六九年的占领政权建立起来,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又“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二十’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米兰·昆德拉显然不是赞叹数字背后的美学,而是以讽刺的方式书写历史,每一个“二十年”背后都是个体生命付出的代价,“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伊莱娜是在第三个“二十年”开始的时候流亡到法国的,而现在已经流亡了二十年的她,就像祖国捷克一样,迎来的是一种动荡:共产党政权已经被有礼有节地删除了,是不是意味着伊莱娜的“大回归”也仅仅是一个象征?被置于“祖国”流亡状态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流亡者,二十年仿佛是同一个梦,一个叫流亡者的梦,一个叫尤利西斯的梦,一个叫“无知”的梦,和白天的回忆、向往、希望不同,夜晚的流浪者之梦带来了可怕的体验,而白天和黑夜构成了相互撕裂的两面:“同一个潜意识导演在白天给她送来故土的景色,那是一个个幸福的片断,而在夜晚则给她安排了回归故土的恐怖经历。白天闪现的是被抛弃的故土的美丽,夜晚则是回归故土的恐惧。白天向她展现的是她失去的天堂,而夜晚则是她逃离的地狱。”
| 编号:C38·2230707·1975 |
流亡者其实再也回不去了,这便是米兰·昆德拉所命名的“无知”——永远呈现空白的国籍,出去和回来都意味着生活在异乡。伊莱娜的母亲来巴黎看她,这是母女离别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母亲是“祖国”的一个代表,但是在五天的时间里,母亲却没有过问伊莱娜一个问题,她对伊莱娜的生活、对法国的饮食和文化,对巴黎的葡萄酒、电影都没有问及,仿佛法国是陌生的,巴黎是陌生的,伊莱娜是陌生的,而她不停唠叨的是发生在布拉格的事,说起伊莱娜同母异父的弟弟,说起那里的朋友而和亲戚,而这些话题伊莱娜插不上一句话。母亲是母亲,母亲却不是母亲,她以一种祖国式的侵入方式想要快速结束伊莱娜的流亡身份,但是二十年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伊莱娜,第一次感觉到低人一等、软弱无能和从属他人的感觉。对于流亡的不幸,她发现那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一种所有人看待流亡者的方式制造的幻觉,实际上对于伊莱娜来说,所有人之外是一个鲜活的个体,流亡反而是她人生最好的出路,因为,“大写的历史的无情力量虽说一度剥夺了她的自由,但还是把自由还给了她。”
身份是伊莱娜夹在流亡和回归之间的一个符码,爱情也是,与马丁一起流亡到法国,马丁染病去世,在马丁去世之前就认识了古斯塔夫,“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她的身体、她的脸庞终于被发现,被欣赏,并且因为这两者的魅力有个男人主动邀她共度人生。”在爱情中她当然也是在流亡,而走进古斯塔夫的世界,是流亡的终结,但这是一种身体的回归?在伊莱娜看来,也许古斯塔夫需要的并非是和自己的一场艳遇,并非是青春的重新勃发,并非是一种感官的解放,“他要的只是休息”,只是逃避妻子之后的休息,所以再次审视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并非毫无触动,只是她心里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身体没有应有的触动。”
终于,她还是回到了布拉格,但只是逗留,只是经过,眼前的是祖国?相聚的是朋友?他们喝着酒,他们讲述着自己的流亡故事,他们感慨回家的不易,但是对于伊莱娜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她们拒绝了她的葡萄酒,也就是拒绝了她本人。拒绝了的是她,是离开多少年后重新归来的她。”为什么没有浓浓的思乡情?为什么没有结束了流亡想要的归宿感?和尤利西斯一样,伊莱娜患上了失忆症,“他们的思乡之情越浓烈,他们的记忆就越空洞。”尤利西斯一心想着故乡,但是当他会到家他才突然明白,他的生命,他的财富,包括他的爱情其实并不在伊塔克,而是在他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或者说,尤利西斯的意义不是回家,而是只属于他的奥德赛之旅。对于伊莱娜也同样,聚会上大家的嬉笑,耳边传来的捷克语,以及那个装了一副假牙的老同学让她回来的呼唤,都让伊莱娜有了回到布拉格的真切感,但是这种真切感依旧是一种幻象,周围的人像是“祖国的坟墓“的密使,“受命提醒她:警告她时间紧迫,生命刚开始就要结束。”
离开和回来,仿佛只是两个端点,生命的意义被这两个端点简单地连接起来,但是那二十年的奥德赛之旅呢?伊莱娜像是滑动在时间轨道上的物,像是在两个端点间机械运动的行李,取消了归来的意义而变成了“无知”。而就在巴黎机场候机的时候,伊莱娜认出了男人,曾经在布拉格的时候,她在酒吧里认识了他,但是他们的故事还没有开始就中断了,“她为此遗憾不已,这是一道从未愈合的创伤。”遇见似乎是将创伤置于治愈的可能性中,而从机场的偶遇,米兰·昆德拉将叙述的视角从伊莱娜转到了这个男人,他叫约瑟夫,和伊莱娜一样曾经从布拉格离开,不过他选择的是丹麦,同样是流亡者,同样面临“大回归”,从伊莱娜的遇见岔开去的这一条叙事线索,为伊莱娜的孤独制造了回响。
约瑟夫是回到故乡看望亲人的,但是对于他来说,故乡也掺杂了太对幻觉,记忆也变成了一种无知:三十年前,母亲去世他看着装着母亲遗体的棺材放入了地下,而现在这里变成了城市新区,身边一式的高楼让他迷路;家人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流亡,但是没有收到讣告,因为警察一直在监控写给流亡家属的信,在没有信件的交流中,他成为了不存在的人;哥哥和嫂子还在,但是约瑟夫很久才认出来,作为唯一的亲人,哥哥给了他一个包裹,里面是童年时代的相册,是儿童画册,是笔记本,一切都以回忆的方式涌现出来,自己的童年,自己的父母,但是对于约瑟夫来说,记忆回来不是温馨,不会回味,而是和不再居住的国家之间建立了联系,而这种联系带着更多“受虐记忆”,对于这种受虐记忆,唯一的做法就是远离,“随着自己生命的构架坍塌在遗忘中,人就会摆脱他不喜欢的东西,从而觉得更为轻松,更为自由。”所以约瑟夫最后扔掉了儿童画,扔掉了“献给妈妈的生日”的祝福。
约瑟夫似乎比伊莱娜更为彻底,他解构了记忆,是把自己完全放置在他者的位置上,也许只有逃避才能让受虐记忆消失。这时候伊莱娜打来了电话,一个不想回到生活过的地方的人,一个想要忘记和阴谋有关的爱情和婚姻,偶遇带来的电话,同是流亡者的身份认同让他终于和伊莱娜走到了一起。二十年前曾有过相遇,二十年后再次相遇,他们仿佛将中间的时间全部抽离了,仿佛流亡对他们来说都是无关的存在,“他讨人喜欢,富有魅力,只照顾着她一人。”他们一起喝了酒,他们一起聊了天,他们一起做了爱,“一起”是对于各自“无知”的一种抵御和对抗。那被抽去的二十年可以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空白,但毕竟存在,说起和他们命运一样的尤利西斯,约瑟夫说:“二十年的贞洁。他们相爱之夜一定是困难的。我想象在这二十年里,珀涅罗珀的性器官都缩了,萎缩了。”伊莱娜的回应是:“她跟我一样。”
粗话连接起了他们,二十年未讲的捷克粗话,既让他们都感到不受约束的自由,“正是通过这门语言,从其根源深处,向他涌来一代又一代捷克人的激情。”也像是对那个驱逐他们二十年的时代的嘲讽,“多少次约会之后,或者说多少年交往之后,情人们终于敢于放肆,迫不及待地要放肆一场,彼此刺激,仿佛他们想要把过去错过和将会错过的一切浓缩在一个下午的时光之中。”但是伊莱娜忽然发现约瑟夫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想不起来他们遇见在酒吧的情形,终于她感觉到自己受骗了,被幻觉受骗,被逃避的欲望受骗,“你像耍娼妓一样耍了我!我对你而言只是个娼妓,一个陌生的娼妓!”约瑟夫不知道伊莱娜的名字,也许这也是一种情感流亡的状态,也许这也是“无知”的一种现实,可是,相遇,讲粗话,喝酒,做爱,只要是找到了在一起的感觉,何必要知道他或她的过去,何必想要两个人相关的未来。这是另一个尤利西斯的故事,当他们得到了激情的释放,当他们找到了快了的感觉,何必要去“赞颂珀涅罗珀的痛苦”?更何必去在乎“卡吕普索的泪水”,对于尤利西斯来说,奥德赛之旅的意义就是漂泊本身。
米兰·昆德拉最终提供了关于消解“无知”状态的一种办法,约瑟夫看着还在睡熟的伊莱娜,他想到自己对她一无所知,但是知道她爱着他,时刻准备和他一起走,离开一切,重新开始一切,于是,他把她称作了“姊妹”,充满友爱的姊妹,进入同一命运的姊妹,无数异乡人中间的姊妹——他离开时留下的纸条上,最后一个词是“我的姊妹”,他对大堂的接待小姐说:“有个太太还在我房间里,她晚些时候再走。”姊妹在睡觉,姊妹会醒来,姊妹最后一个人离开,但是当约瑟夫命名为姊妹,他似乎也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宿,他似乎也拒绝了流亡路上的他者,而或者这才是他记住的、留在故乡的亲人,“他透过舷窗,看见在天空深处有一圈低矮的木栅栏,在一座砖房前,一棵细高的冷杉,像一只举着的手臂。”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