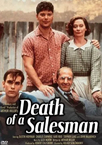2020-08-19《推销员之死》:生活没有真相

威利没有上楼,“让我一个人吧。”当妻子琳达走上了楼梯,他穿好了外套,系好了鞋带,戴上了帽子,然后从客厅的通道里走了出去,关上门消失,背后却传来琳达的呼喊,然后是一声绝望的“不!”——在通道被一扇门关上而隔绝了这个黑夜之后,威利消失在一片泛白的世界里,在过度曝光的淡入之后,是一场如雾中举行的葬礼,面对着威利的坟墓,站在中间的琳达在肃穆中说让自己再呆一分钟,在这告别的一分钟里,琳达对着不再说话的威利说:“帮助我吧,我要开始另一次旅行,我期待你的到来——我们自由了!”
威利在死亡之前说:“让我一个人吧。”琳达在葬礼上说让自己再呆一分钟,一个人,一分钟,都是为了沉思自己存在的意义,而这种沉思最后变成了仪式:对于威利来说,他穿好外套、系好鞋带、戴上帽子,便是一种告别——他是跟着已经死去的班而离开的,17岁进入非洲丛林21岁走出丛林,“之后我就变得富有了”,班有着一种传奇的经历,但是富有却意味着死亡的降临,当班拎着皮箱从那扇门走出去,并且告诉威利“我们要迟到了”,其实就是带着威利离开这里。当仪式展开,对于威利来说,死亡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前进的方向,这种对死亡的执着最后在琳达和他告别的世界里变成了另一种仪式,她知道为什么威利会选择死亡,“对于推销员来说,生活没有真相,但必须有梦想。”死亡如梦想一样发生,它甚至像自由一般成为一个人最好的归宿。
死亡是容易的,威利以仪式的方式奔赴了死亡,而这个落幕告别世界的镜头其实早就在影像的叙事中发生,第一幕的场景在夜晚,在路上,开着车的威利不断听到从身边疾驰而过汽车的喇叭声,也看到更多的汽车超越了自己,在嘈杂的声音里,夜雾中的汽车大灯照亮了威利前进的方向,但是这种方向是容易迷失的,在慢镜头里,威利似乎遭遇了颠簸,似乎在刹车声里意外正在发生——一场车祸?在第一个场景结束时,提着箱子的威利打开了那扇门,他回到了屋子里,看见琳达,他说:“我不能控制死亡。”最后五分钟他已经记不得什么了,但是每小时十里的速度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造成事故的,威利从佛罗里达回来,到底遭遇了什么?他说他一直看着窗外的风景,但是后来似乎离开了路,好像撞死了人,“你这是很奇怪的想法。”琳达安慰他。
夜雾中的行驶,汽车大灯造成的迷失,嘈杂的声音构筑的混乱,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威利从佛罗里达回来的路上,那次他的确没有遭遇意外,但是感觉离开了自己行使的路,感觉撞死了人,其实是威利在不断暗示自己的死亡,因为“我不能控制死亡”,正是在死亡中不断迷失,不断产生幻觉,终于最后一次和班离开时,他关上门便是走向了真正的死亡——看起来是追随着曾经富有的班而去,实际上是在隔绝了活着的家人之后选择了死亡——在一个没有真相只有梦想的世界里,也许死亡不是无法控制,而是成为了自己摆脱这一切向往的所在,因为死亡带来的是永恒,带来的是自由,带来的是沉默。
一种倒叙的手法,将最后的命运在第一幕中展现出来,死亡真的是一种最容易完成的事,而这个结构倒置的运用,在施隆多夫看来,或者正是要把威利作为推销员的一生展现在没有真相的世界里。改编自阿瑟·米勒的小说,当它成为施隆多夫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小说的文本,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所以在这个可以自由叙事的影像里,施隆多夫对于这一个死亡事件的描述完全在自由状态中,他甚至用意识流的手法把“推销员之死”变成了一种现实版的梦境,在不同场景的交错和融合中,在人物随着剧情而自由出入中,影像镜头变成了流动的舞台,在间离效果的不断运用中,一种死变成了生的一部分,它在必然意义中成为了一个失败者无法逃避的选择。
| 导演: 沃尔克·施隆多夫 |
场景的自由调度隐含着施隆多夫技术主义的主张:威利回来之后,在庭院里推动着车轮,这一幕被在楼上的儿子毕夫和海波看见,之后威利回到了厨房,拿出一瓶牛奶坐在那里,然后开始自言自语,而他的自我叙述又像是对小时候的毕夫说的,他回忆起父子一起剪树枝,一起搭吊床,一起在院子里玩游戏,而正当威利在回忆中自言自语时,毕夫已经走到了他面前,然后两个人开始了对话,并打开了门走向庭院,门打开的瞬间,黑夜变成了白昼,而此时的毕夫和海波正在庭院里玩橄榄球,威利说起自己的未来一定会有大事业,说起孩子们会去不同的城市,“这是好棒的感觉。”他甚至对琳达说起自己的销售情况,言语中满是自豪——游戏、事业和满怀希望的未来,在这个白昼的庭院里成为一种幸福,但是这只是一个回忆的场景,当威利从庭院里走回来,照着镜子,场景又变成了夜晚的厨房间,那杯牛奶还摆在桌子上——没有曾经游戏的庭院,没有未来的希望,甚至没有了毕夫,在照镜子的过程中,威利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现实。
当威利和查理聊天说到销售的工作时,他们说到了曾经去过非洲现在已经死去的班,而此时在镜头的虚焦里,穿着白衣服的班就在他们身后,当话题结束,虚焦变得清晰,而班也走到了威利的面前,接着他们打开了门,又进入到那个毕夫和海波正在玩橄榄球的庭院,拎着皮箱的班告诉他们自己17岁进入丛林21岁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就变得富有了。”班讲述的是关于自己的一种传奇,而这种传奇故事不管是对于威利来说,还是对于毕夫来说,都变成了一种激励,班最后用拐杖抵住正在地上躺着的毕夫说:“不要和生人公平决斗,否则,你将来不会从丛林中出来。”一种警告,暗示了丛林的危险性,暗示了未来的残酷性,而这正是社会这个丛林里有着太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缘故,而威利在最后将班从那扇通道的门送走时说:“我会向他们灌输。”——威利所说的“他们”当然是指还没有进入社会丛林的毕夫和海波,尤其是寄予希望的毕夫,而正是这种“灌输”的想法,使得威利和毕夫父子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和升级,最终导致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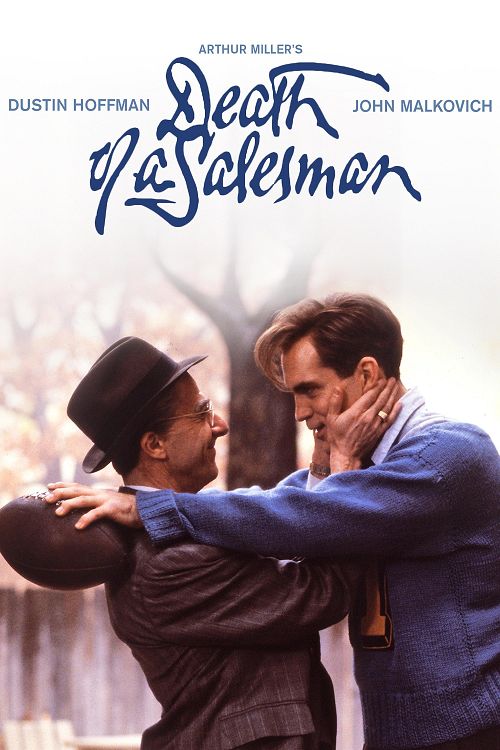
《推销员之死》电影海报
施隆多夫技术主义下的场景装换,其实是两代人命运的不停转换,从四个人的家到充满游戏乐趣的庭院,从楼下的厨房到楼上的房间,从赫尔德的办公室到史坦利的小餐馆,甚至威利和女人佛亮丝在一起偷情的旅馆,这些场景构成了威利多维度的生活,但是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是封闭的,即使在施隆多夫的镜头转换间变成无缝对接的存在,但威利就是在这些封闭空间里演绎生命最后阶段的无奈、失望、崩溃和死亡,演绎一个推销员在找不到生活真相的现实中渐渐迷失,演绎了丛林对自己一步步的扼杀——只有最后一扇门打开,最有后一个仪式完成,他才以自由的方式选择了一种死,一种梦境般的离开,一种在家人的呼喊中的沉默。
威利为什么会选择死?因为“我不能控制死亡”,而真正不能控制的是这个现实,对于一个63岁而一事无成的老人来说,对于一个跑了700公里而赚不到一分钱的推销员来说,对于只想每个星期拿到65美元的父亲来说,威利处在社会的底端,在赫尔德的办公室里,他只想凭借自己36年来为公司勤勤恳恳工作的态度,只想和赫尔德父亲的交情找到一份差事,但是赫尔德告诉他的是:“生意就是生意。”当自己的青春、热情、人格都消耗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威利感觉到的除了心酸,还是失落和愤怒,最后是大声的宣泄——他失去了自己最后的工作,而在查理的办公室,似乎是可怜他而已,查理给了他一些钱,威利又大声对查理说:“我只是被开除了。”而最刺激他的是,查理的儿子伯诺本拥有了一份律师的工作,伯诺本告诉威利的一个消息是:毕夫的数学课挂了,而且无法毕业。起先是他和查理两个父亲之间的对比,然后是伯诺本和毕夫两个儿子之间的对比,在双重的对比中,威利似乎失去了过去和现在,也失去了他寄予希望的未来。
自身命运的遭遇,是威利无法摆脱的可怕现实,毕夫的不争气是他一样不可逃避的真相,而在这种真相里,威利的可怜之处就在于为毕夫规划了人生之路,在于用经验“灌输”给他们成功的道理——当威利自己成为失败的推销员,何来成功的经验?他一直鼓励毕夫,说他会成为最伟大的人,但是似乎又不敢放开手脚,而毕夫讨厌这个城市,讨厌父亲的设想,他甚至想要去西部养牛,一种对未来生活的自由向往最后被无情扼杀在威利的经验主义中,“他应该在这房子里建立一个家庭。”在处处设计好的未来中,其实一切都变成了幻想,而数学被挂无法毕业的现实,对于威利来说又变成了沉重的打击,甚至他还听说毕夫偷走了老师的金笔——在威利开始训导毕夫的时候,他其实在和佛亮丝在一起,而毕夫推门进来发现了父亲的丑闻,威利还解释说她是自己的买主,是住在隔壁的客人,但是毕夫已经无法容忍他所作的一切,在“伪君子”的骂声中甚至开始怨恨父亲,将曾经的愤怒宣泄在威利身上。
自我希望的破灭,儿子未来的渺茫,以及父子之间的相互攻击,生活中其实有着太多可怕的真相,但是无法面对真相的威利只能在“他像我,他将变得优秀”的自我欺骗中,只能将眼泪咽下去还保持着微笑——当威利在仪式中自己选择死亡,其实是在否定不能控制死亡的宿命,但走过通道,跟着班走进丛林,何尝不是另一种宿命?甚至直到威利死亡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推销员:向客户推销产品,向儿子推销未来,最后这个失败的推销员终于在偏离了道路的情况下,撞死了自己,结束了永远卑微的一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