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31《工厂日记》:通过苦役获得人的尊严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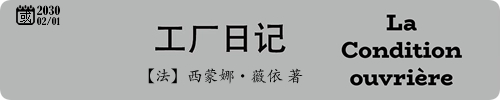
物如人,人如物;这就是恶之源。
——《工厂生活经历》
工人们听从命令,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员;他们每天不停地工作,只是在重复五六个简单的动作,大约一秒钟就是一个动作;除了焦急地找箱子,找校准员或其他零件,他们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当主管过来把他们安排到其他地方,他们便开始新的工作,还是听从命令,还是重复动作,还是没有喘息的机会——他们就这样“像物品一样”被放在机器前面。
而且,机器就是一件正在运转的物,甚至相比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发生了变化的零件,人连零件那样的“历史”都无法拥有,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没有在其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甚至“什么都不了解”。物如人,是被支配的存在,人如物,没有选择的能力,当西蒙娜·薇依将人和物并置在“工厂生活”这一环境之中,她所指出的“恶之源”就在于对工人现状的揭露,物被生产让它们成为劳动产品,而人如物却不被考虑产品的劳动,并置成为了倒置,恶之源指向工厂,指向现代工厂,也指向商店、市场和交易所,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现代工人被奴役的写照。
这是薇依于1941年至1942年通过在马赛的工厂实践写下的“工厂生活经历”,和她最初进入工厂不同,那时的工人境况更为糟糕,1936年之前因为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工人们的生活异常艰难于残酷,更具有“无产阶级”的标本意义,但是后来随着情况的改变,工人的境况也得到了改善,但是工人们依然在这种“恶之源”的控制下,在成为物的生存中不断重复动作,不断抹除自我的痕迹,不断被奴役——她在写下这段经历之后也提出了建议,那就是让工厂里的专家、工程师记住,工人不仅要制造东西,也要避免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且这不是为了让工人听话,不是为了让他们感到快乐,“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堕落下去”。
薇依的建议并非是大声呼吁型的,也并非是号召工人进行反抗的,她仅仅希望“在工厂内部得到纠正”,希望这种恶在不出现在工厂里。也正是这种内部化的解决方案,使得薇依从934年开始的成为工人的“体验”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工厂里,大大小小的苦痛被加诸人身上,让人产生了被奴役的感觉。”这是薇依的感受,她之所以进工厂成为一名工人,之所以在工厂一线成为被奴役的工人,不是为了生活所迫,不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一种“体验”,体验工厂的做工环境,体验工人的辛苦、劳累和痛苦,体验现代化工厂对工人身心的戕害,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恶之源”,从而在恶的基础上产生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意义——薇依命名为“尊严感”,只有拥有了尊严,人才会脱离物的束缚,才能摆脱物化的现实,最终得到人的权利,最终走向善的高度。
薇依的这种被奴役的生活体现在1934年至1935年的《工厂日记》中。她于1934年12月4日进入第一家工厂,第一周的工作中,每天的工作都不一样:周二从早上开始进行1小时的钻孔,上午结束后进行操作冲压机1个小时,下午结束后则操作手柄45分钟进行纸板制作;周三上午操作飞轮冲压机,工作不累但是以失败而告终,下午还是冲压机工作依然失败,之后则是钉扣机工作;周四上午还是钉扣机,成功率还是不高,下午遇到电力故障3点离开;周五进行冲床压制直角零件,做坏了100件,从11点开始进行手工劳作,用敲击槌、空气管、锯片和灯箱制作纸板,对眼睛影响很大,去工具房感官被责骂;周六还是做纸板……从周二到周六,从第一周到第十五周,薇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为了一名体验的工人,而对她来说,,这些体验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做工人的“物化”的存在。
在第七周的时候,发生了两起事故,第一起事故是因为传送带偏向了一遍,后来有人将它修好了,但是对工作产生了影响,第二起事故是工具卡主了零件,主管认为这是薇依的错。1935年4月开始薇依在塞夫尔老桥街的另一家工厂做工,她被安排到高度专业化的戈蒂埃车间,那里有油罐和防毒面具,有传送带和冲压机,她则在冲压机上工作,有一个工头告诉她:如果做不到800件,就会被解雇,而这也意味着在剩下的2个小时里要完成800件,薇依努力着,虽然心中充满愤怒,最后还是达到了每小时600件;后来她又进入了雷诺工厂,那一周她记下的工作时间是67小时,除了一天是8小时另一天是9小时之外,其余五天都是10小时,而最后挣得的工资是173.25法郎,按照工作要求,就必须在最多三小时里完成4000件,之后还要做5500件,“几乎不可能”。
巨大的劳动压力让薇依感到身心疲惫,在1934年工作的第七周,薇依被诊断患上了耳炎,后来被送到了医院,在休息了几周之后薇依重新上班;但是第十五周又开始头痛,她无法上班只能“瘫倒在家”,稍微好点出去到书店买了工业制图手册,她希望通过学习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头痛依然困扰着她,“耳朵剧烈疼痛,凌晨3点半就醒了,身体有些发抖,感觉像是发烧了……”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中,只要能坚持薇依总是在机器前完成工作;但是薇依还是被解雇了,在被头痛折磨而陷入沮丧和消沉之中的时候,还是去找工作,而第二次找到工作后她决定每周包括交通费在内只花费3.5法郎,她这样做,是为了让“饥饿成了持续的一种感受”,在她看来,是不是有比起吃饭和工作,还有更难受的事。
实际上,不仅进入工厂是她体验的一种方式,甚至身体被折磨、饥饿也都成为了她寻找答案的特殊手段。从个体意义上来说,薇依进入工厂成为工人,是要“感知自己所做事情的用途”,“于每个人而言,他自己的工作都是一个沉思的对象。”工厂生活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活,而是作为“沉思的对象”,也就是说,薇依把沉思分为两种,一种是知识型的沉思,它在阅读和书写中完成,是文本化的存在,但是另一种沉思则是实践型的沉思,是通过劳动、感知甚至以极端的实践方式获得的感受,并以这种感受为基础进行沉思,“有什么比一台机器更不具教益的了……”那么,她不惜一切代价成为工人,成为被奴役的工人,成为被身心折磨的工人,她真正想要沉思的到底是什么?
| 编号:B83·2230921·2007 |
首先就是从个体出发对自我的沉思,她在写给阿尔贝蒂娜·泰弗农女士的三封信中说出了自己沉思的目的,“这种体验在很多方面都与我的预期相符,但却有一点不同:这是现实,而非想象。”体验是真实的,是真切的,它不是书斋里的想象,从企业的管理模式,到零碎的工作,到官僚式地制度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工厂的体验中才能变成现实,才能感同身受;在1934年给一位学生的信中,她也认为,自己感觉逃离了抽象的世界,“走进真正的人类中间”,而且不是简单的好坏,而是真正的善恶,“我更喜欢你说的想要与现实生活接触。”薇依认为很多人只是靠感觉、为感觉而活,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被生活欺骗了,甚至是在自欺欺人,“因为真实的生活不是感觉,而是活动——我指的是思想和行动的活动。工人和创造者才是真正的人,与他们相比,那些靠感觉生活的人在物质和道德上都只是寄生虫。”
这样的现实,这样的活动,薇依在沉思中获得了什么?她认为,工厂生活“无限改变了我对事物的整体看法,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感知”,而且她认为自己“感到快乐”——为什么在如此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劳动强度中,在身体受到戕害的实践中,薇依还会感到快乐?那就是她获得了真正的表达,“人因为想表达而贬低了不可表达之物。”这是过去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就像自欺欺人的生活一样,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但实际上只是“不可表达之物”,而现在表达就是表达本身。在薇依的表达中,身体的痛苦和折磨是真实的,工作的劳累和奴役是真实的,这些都是生活带来的真正的表达,“慢慢地,在苦难中,我通过苦役重新获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感。”不管是沉思还是表达,在薇依看来,只有通过苦役才能拥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感,反之,没有经历过苦役,所谓的尊严都是自欺欺人。
薇依的苦役便是无尽的疲惫,不止的痛苦,甚至是从这家到下家不停满足被奴役的欲望,“疲惫使我忘记留在工厂的真正原因,也使我几乎无法抗拒这种生活最强烈的诱惑:停止思考的诱惑,这是唯一能避免痛苦的办法。”所以她要自己忘掉痛苦,只有疲惫才会忘记,只有时间被占满了才会忘记,而忘记也不是麻木,而是让精神变得更加坚定,甚至对于薇依来说,反抗也不是最后的办法,她要消灭反抗,因为反抗就是要回到舒适圈,是要改变自己的苦役,所以在工厂做工的生活中,薇依不仅不让自己有一丁点的反抗,而且期望自己变得顺从,只有顺从了才能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间在工厂里,只有顺从才能更深刻领悟苦役的魅力——苦行僧般的工厂实践,对薇依是身体的戕害,是精神的折磨,但她极端地追求这一切,并在这个沉思的对象中完成对人的尊严的书写。
当然薇依的沉思绝不仅仅是在个体意义上得到尊严,她更是为了工人的现状和未来,更是为了人的存在。在《工厂日记》中,薇依记录了工人的现状:一位女钻工因为戴着发网,在工作时被机器扯掉了一整束的头发,头上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但是这位女工下午还是来上班了;一位女工在28岁的时候患上输卵管炎症,之后她的胃被切除了,她现在无法自己从冲压机上起身,但是她完全不想换公司;一位怀孕的女工发生了不幸,很多人为她募捐,薇依捐了2法郎,在更衣室聊天的时候听到的是:“每年都有!——真是个巨大的不幸,仅此而已。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知道的时候,不应该……”在工厂里,薇依的工友中有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寡妇,有和丈夫分开的女人,有失去了一个儿子,为自己没有一个孩子而高兴的女人,有“幸运”地在8年前失去了患肺结核的第一任丈夫,有生病、独自生活的女人,有带着两个孩子和一个患病丈夫的螺丝切割机女工……他们工作在“资本家的陷阱”里,他们被困在官僚主义制度中,“你不愿意这么做,却在残酷的逼迫下。”
他们当然也成为了薇依“沉思的对象”,这是对人的沉思,但是在这样的沉思中,薇依又不像对自己一样无情地推向苦役,而是从他们的苦役中寻找出路,“处于苦役中的缺点是,人们很容易把那些山洞里苍白的影子看作确实存在的人。”所以她要做那个破坏“洞穴”和影子的人,在她看来,由社会塑造的个人尊严已经遭到了破坏,所以必须要为自己另外打造一个,“一个人最终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如何意识?如何打造?在1934年至1935年写下工厂日记的时候,薇依的沉思在于对环境的改变,比如对工厂官僚组织的改变,让管理者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展示出更多的善良;比如建议创造一些“灵活的自动化机器”,这样才能让工人体会更多的人情;甚至建议让工人更加熟练,提升自己的注意力,从而在一分钟与下一分钟相连接中更有主动性,而这也是灵魂不被奴役的办法。而在1936年写给一位工程师的信中,薇依则希望老板培养更多的工人,不是培养一种机器而是培养一个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另外则向雷诺的工人发出号召,用他们的笔写下自己的工作,谈谈工作中的苦,“真诚地表达。无论好坏,不要故意避而不谈,也不要夸大什么。我想毫无保留地说出真相会让你们感觉好一点。”
无疑,薇依对工厂经理的建议,对工人的号召,都是自我沉思的一种扩大,像自己的目的一样,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人,使自己拥有人的尊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她反对的是工人们的反抗,“反抗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极其短暂的抗争(我想说的甚至是一种感觉)。”她分析认为,一个工人在独自工作,如果他反抗,只能反抗自己,“或者带着情绪工作,这将导致工作失误,自己也会因此挨饿。”也就是说,在薇依看来,反抗是对思想的一种唤醒,而唤醒之后的思想更令人痛苦,所以就像她自己一样,顺从是选择,这样才能更彻底地感受奴役之苦,也才能更全面得到尊严感。她更不希望革命,在她看来革命前后其实并没有让工人改变被动服从的生产模式,连雷诺的经理也无法改变服从的现实,相反革命之后工人甚至会陷入更差的环境,“但我丝毫不想强化反抗精神,这与其说是为了秩序,不如说是为被压迫者的心理着想。”在这个意义上,薇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工人罢工,对于“量变引起质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颇有微词,在她看来,这些都无法真正改变工人的现状,都不是对个体尊严的给予。
所以,顺从的薇依选择了“合作精神”,“我全心全意地希望现行体制能朝着更加平等的力量对比发展,尽可能彻底地发生转变。1936年薇依在向法国总工会所做的报告中,分析了北方冲突并提出了建议,她认为需要从实践性意义上寻找突破,那就是制定工会制裁条例,薇依建议:在工会、联合会、联合管理处中研究工业企业的新秩序、新纪律;邀请所有工会部门和雇主就所有有关秩序、纪律、产率和工作质量问题的困难向联合管理处提交报告;邀请法国生产总联盟与法国总工会一起就该领域的整体性问题,以及所有具有一定重要性的特殊案例展开研究。1936年她又提出了《建立工业企业内部新制度的计划准则》,她认为,“新制度旨在在各企业内部,实现工人作为人的合法权利和物质生产利益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要工厂的生产模式和工人的尊严、道德相适应。1937年2月23日面向工人阶级听众所做的一个讲座中,薇依又提出了“合理化改革”的目标,“合理化改革似乎是对生产的一种优化。如果我们仅从生产角度考虑,那合理化改革是促进工业进步的连续创新措施之一;如果我们从工人的角度出发,有关合理化改革的研究极其重要,它事关工业企业中可接受的制度问题。”
一方面,薇依在制度、管理层面上进行改革,希望工厂改变不合理的设置,让工人拥有尊严感,另一方面,则是让工人们自己行动起来,摆脱物的状态,拥有自己的权利,“你现在应当努力使自己有能力承担它们;否则新获得的优势有一天会像梦一样消散。只有当你能够正确行使你的权利时,你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去除阶级性和革命观点,薇依的“顺从”式沉思其实还是回到了人这一层面,“于人类而言,生存不是目的,它只是一切善——无论真假——的基础。善加诸生存之上。当善消失时,当生存之上不再有任何善的时候,当生存变得赤裸裸,它就不再与善有任何关联。”反抗无法走向善,革命也只是一个谎言,唯一的解药就是找到善,由此薇依的神性观念开始得到阐释:人们必须通过符号才能读懂文字,必须通过中介才能认识上帝,那些苦难,那些奴役,就是符号,就是中介,“宇宙充满了无尽的象征性符号。我们应该去阅读它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找到上帝皈依上帝,而上帝才能让人成为人,“在上帝那里,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行为,它仅关乎自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对象。”
进入工厂,是一种体验,是对于自我意识的体验;感受痛苦,感受奴役,是一种体验,是对于人之为物的体验;改善制度,实现变革,是一种体验,是从恶之源到善之生存的体验……薇依用身体和精神完成了体验,也完成了沉思,她也找到了拥有尊严的唯一办法,但是“关乎自我”的唯一一条道路通过苦行来完成,通过奴役而书写,自身是不是也会成为符号和中介?薇依将对身体的戕害看做是一种道,当她终于以拒绝食物而付出生命的时候,也许真的看见了上帝,但是成为自己,拥有尊严真的需要如此极端而决然?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