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03《西西诗集》:美丽正在我家梁上做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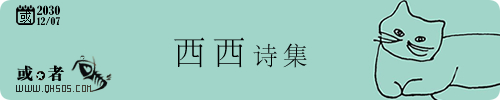
所以,不要对我说
这里的梧桐
是法国梧桐
——《法国梧桐》
梧桐还是梧桐,甚至法国梧桐还是法国梧桐,但是没有蝉鸣,没有长街上叶落的许喧哗,也没有河,没有雪,没有冰花白糕糖,更没有母亲,所以这里有梧桐,却不是“法国梧桐”。从梧桐到“法国梧桐”的否定,也是呼应着那个“问题”,而“法国梧桐”的问题似乎也成了西西对于自身归属的某种疑惑,“《法国梧桐》与法国无关。我在上海出生,市内到处是法国梧桐。来港后,不免怀旧。”
西西祖籍广东中山,出生于上海,13岁的时候随父母定居在香港,而当看到香港街上的那些梧桐,却不是带着记忆的法国梧桐,或者说,那些蝉鸣、叶落、河、雪、冰花白糕糖和母亲共同组成了和“法国梧桐”一样的怀旧意象,怀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缺失,而缺失的背后是对自我属性的某种辨认,这种缺失和辨认似乎成了西西诗歌中最常见的情感抒发,而在另一个意义上,用诗歌来抒怀,用诗歌来唤醒,诗歌也成为了她的一种寄托。《西西诗集》获得2019年纽曼华语文学奖诗歌奖,在写于2000年的“序”中,西西回顾了自己和诗歌结缘的过程,她说自己开始读诗是在初中,后来发表在杂志社,认识了诗人力匡和齐桓,之后参加了“星岛”举办的旅行活动,又认识了王无邪和岑昆南诸文友,还拜了无邪而师,通过无邪和昆南,又认识了诗人叶维廉。在写诗的道路上,西西似乎一直用仰望的目光看待香港的那些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西是谦卑的,或者说写诗并非是自己的强项:看了叶维廉的一首《愁渡》,“我一读,顿然呆住,自己的诗太窝囊,再也不敢写。”但是后来觉得自己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写,也不管别人,也不要什么主义,所以“又敢写了。”
从“再也不敢写”到“又敢写了”,变化过程也正契合了西西对待诗歌的态度,不管是觉得自己写的诗太窝囊,还是要将“什么什么的主义扔掉”,毕竟诗歌对西西来说,也是自己寄托情感、抒发情感的一个通道,也是自己生命中和“法国梧桐”一样的存在——当西西确认梧桐只是梧桐,法国梧桐就是法国梧桐,她想要寻找的是蕴含着情感的专有之物,这种专有之物甚至具有某种唯一性。从初中开始写诗,诗集中收录了三首旧作,《夏天又来了》《在马里昂巴德》和《面包》,三首诗歌的确就是西西所确认的“法国梧桐”,它们散发着怀旧的气息,它们带来美好的回忆,它们激发着诗人的情感:“行囊仍是去夏的/泳衣泛起的是肥皂味/谁知道哲学现在躲在哪里/我的浮床就是我的上帝”,在《夏天又来了》中,“又来”的夏天是不同的,但又是相同的,相同的“阳光折射的样子”,相同的“女子持伞的姿势”,相同的光点子,相同的暗色汽车;看了法国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之后,西西写下了《在马里昂巴德》,那里有午报,有牛群,有绿灯,有滚铜环的女孩子,有敲响的钟,有廊下,有竖琴,有警察,是电影影像留下的意象,却也变成了自己的诗意,“给我一个锚。给我一座山。”写于1962年6月的《面包》,记录的一次仪式,“这里是手/这里是碗/甜甜的面包/你们究竟打不打算从独木桥上走下来”,彼时24岁的西西发出的疑问也是让面包从仪式返回到日常。
所以西西早期的诗歌,更多是表现为对生活的热爱,凭借着自己细致的观察和细腻的情感,西西笔下的生活是无忧而快乐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在科斯摩斯的秋天,她感觉有“一只妖怪跟在我身后”,于是大清早可以去数数“蒲公英的胡子”,这是生活的趣味;对于自己长大后想要成为什么,西西说“我想做/热水炉”,因为热水炉可以让所有小孩都有热水洗澡,所有妈妈也都有热水洗衣服,这是对生活的爱;《花墟》是关于一只盛花布袋的故事,“有一束花/名叫我的灿烂/这边的一朵/名字是/见雪/还有这一朵/名叫鱼歌”,这是对生活中美的发现;即使在上学时会遇到“猎眼的训导主任”,他会“瞪着罗伞树下满地的碎屑”,然后处罚学生,但是“苹果脸的小孩”看着头上的罗伞树,也会手舞足蹈,也会又跳又笑,“是花瓣呀/是花瓣呀”……在西西的诗歌中,海素是很乖的婴孩,门神长着胡子替自己把门,玻璃呈现出草莓红河风信子的蓝,河水将扇子挥动时的“达达马蹄声”从上游“达达”到下游,阿尔卑斯山上的天使会把云吸得很白很干净,而赌气的云“搬到城里/定居去了”……
| 编号:S29·2240119·2053 |
这一种带有美好回忆的情感在西西笔下就像是《美丽大厦》一样,西西住的地方是香港的“美利大厦”,但友人的信常常写成了“美丽大厦”,错字带来的是错误的地址,但是西西却将它变成了“美丽”的错误,她发现了一种浪漫,“在西晒的窗下/挤迫的空间/从容地生活/常常微笑/并且幻想/美丽/正在我家梁上做巢”,美丽变成了具有生命活力的动物,可以在家里的梁上做巢,于是错误变成了浪漫。同样,西西对故人的思念也在诗中具有了一种情感的力量,从《父亲的背囊》里,阅读着那些“白发的朋友”的故事,更感受着父亲身上散发的亲情,“然后我父亲背起背囊继续上路/脸上展开一个微笑/挥手和我划独木舟的弟弟道别”。同样是写父亲的,《重阳》更看做是对逝去父亲的怀念,在坟前的对话中,西西和父亲说着心里话,“你真的不用为我/担忧/我活得很好/而且/快乐”。而对于记忆的激活,即使带着遗憾,即使梧桐不再是法国梧桐,西西的布袋里也装着“小小朴素的古城”,装着那里的山,装着散步的声音,装着长江。
对快乐生活的抒情,对美好童年的记忆,对故人的思念,对故土的怀旧,西西都将它们视作自己心中永存的“法国梧桐”,之所以在现实中梧桐不再是法国梧桐而在诗歌中依然被命名为法国梧桐,就在于西西在这些事物中发现了美好,在这些元素中找到了诗意,“法国梧桐”的命名就在于让普通的物激活,从而赋予它们一种生命,在这种具有生命之物中寻找寄托,仿佛它们不曾远去,仿佛它们越发鲜活,从而完成一种对话。这是从物到生命的转变,西西的诗歌成为了一种赋能物,这是西西创作诗歌的一条路径,而随着对外部事物的不断接触,随着对人生的不断感悟,西西诗歌又走向了另一条路径,按照黄灿然的说法,那就是西西对异化世界的态度,“西西的诗,语言明净,语调天真,构思奇特,保有一颗童稚之心。这正好用于揭示她的重要主题:现代人的异化。”
异化首先是一种形式上的,西西对诗歌技巧的探索在很多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突围,这里不妨看做是一种“修辞”,在《快餐店》里,她连用19个“既然”,“既然我不会劏鱼/既然我一见到毛虫就会把整颗椰菜花扔出窗外/既然我炒的牛肉像柴皮/既然我烧的饭焦/既然我煎蛋时老是忘记下盐……”铺垫了“我认为可以简单解决的事情实在没有加以复杂的必要”的生活,最后也得出了“我常常走进快餐店”的结果;《可不可以说》也是排比句式,但是西西改变了数量词的固定搭配方式,从一枚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一个胡椒粉、一架飞鸟、一管椰子树,到一头训导主任、一只七省巡按、一匹将军、一尾皇帝,赋予了诗歌特殊的意蕴;《一郎》则引日语入诗,“莎苦拉莎苦拉”是樱花,“以苦拉 以苦拉”是多少钱,再配以木屐“的的塔”的声音,在节奏上制造了韵律;还有仿超现实主义画家玛格丽特创作的《这不是诗》,“这不是诗/不是诗/是诗/诗”,也完全是一种诗歌形式的尝试。
但是在形式的探索中,《绿草丛中一斑斓老虎》既是形式创新的一种外在展示,同时符号的密集引用也隐喻了电脑书写带来的迷失,而这正是西西表现的现代性的异化:
杉杉松 蝗柏 梧蝶 蝉 榆桐
艸艸花艸鸽艸木艸艸艸虺艸艸草艸鸢艸树艸
艸木艸杨艸山岫林艸草艸蚤艸山艸狐艸鸟艸
艸艸艸虫艸山岫岫山岫艸花岫艸木岫
艸山蚁艸蟀艸木艸蜢岫岫鸟岫虫艸木艸
艸山蚁艸木艸树艸王艸艸木艸蚓艸花艸
艸林艸艸木艸艸艸花艸艸鸟艸山艸蟀岫岫艸
杉杉松、蝗柏、梧蝶、蝉、榆桐,都是生命体,在西西对日常意象的建构中,它们都应该从物变成充满活力的生命,但是却夹在在“艸”之中,“艸”是有意义的文字,但是在这里却完全变成了吞噬生命的符号,变成了湮没诗意的物。相同的还有一首《床前明月光》的诗,很明显这首诗和李白的经典名作有关,但是在西西的仓颉输入法中,李白诗中的每一个海子都对应一个字符,“日是A,月是B,明是AB/床是ID,前是TBLN/光是FMU/”,于是李白脍炙人口的“窗前明月光”就被替换成了“ID/TBLN AB/B FMU”,于是“李白酒醒,惊见蛮书”。“艸”成为生命体无法逃离的迷宫,仓颉输入法成为了没有意义的字符,这就是电脑书写带来的“异化”,符码是符号,它也在转换中会变成汉字,会输入成文字,会连成一首诗歌,但是当西西又将它们复原为符码的时候,它们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符号,也在物化着生命、诗歌和情感。
|
| 西西:可以进来/听一曲箜篌吗 |
而这就是西西笔下的现代症候,它们是《电话》中的那些按键,是电话答题中的选择,“大天使加百列按A字,大天使/迈可按B字。六翼天使按C字/撒旦按D字,教徒热线按E字/上帝请按G字”,最后的结局是:“上帝不在家,请留言”;它们是《爱说话的猫》在现代都市中的迷失,“你会不认得回来/每幅墙一模一样/每个角落阴暗/每扇门紧紧封闭/冰凉的铁闸背后/你也不会找到朋友”;它们是《迷宫老鼠》中被讯息绑架的生活,“指令的讯息我是否收到/指引我曾否误读?/如同迷宫老鼠,我对外界一无所知/管它呢,且到楼下/耍一阵四方形的肥皂泡”;它们是《法兰肯斯坦》中复制带来的现代恐怖,“能够制造人,你就是/上帝了。你会复制自己吗?/抑或,你本来就是复制/我?”它们是《浏览商场的橱窗》里的中央空调、电动楼梯、健美中心,是“温柔的照明,女巫的催眠/魔王的点金棒,变幻色彩、形状/潮流的触角,水晶天鹅的双翼”,这是城市中独立却封闭的世界,这是如童话中南瓜的寓言,这更是巴尔扎克笔下“拱廊街”的现代隐喻,“我们可以找到/织织复织织,木兰当户织?”
西西对我们是否可以找到的疑问表达了两种看法,一是在现代被异化和物化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物,变成了符号,变成了指令,变成了讯息,现代人无处可逃,甚至现代人也成为了一种物,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异化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还可以找到“织织复织织,木兰当户织”?它们构成的诗意或者残存着,但并没有消逝,而这也正是西西在坚持和努力的,正如她那些用天真童稚的眼睛发现的生活美好一样,诗并没有彻底被异化,在这个意义上,西西对现代人的异化重在讽刺重在揭露,而背后她所期望的是发现和发掘——诗还存在,诗意还存在,就像《超级市场》这首诗中,西西描绘了香港遍布的超级市场,如果那些广告中“模拟的橙子、鳄梨和苹果从高楼掷下”,会砸中读财经杂志的行政人员、手袋里藏着丽人故事的女白领、肋下夹着电脑资料的年轻人、走路读着日本漫画的青少年、刚在报摊买了份马经的送货员,但是一定不会击中“读诗的人”,因为在西西看来,读诗的人和诗歌一样,在这个异化的时代,是唯一不被异化的存在。
诗歌在哪里?诗人在哪里?它在西西的旅行、寻找、对话、思考、阅读和凭吊中;《城遇》中的诗人进入了中国诗歌史之中,“我”找不到白头鸦和五花马,错过了床前明月光和捣衣声,在骊山、灞桥,不见年年柳色和水边的丽人,经过咸阳没有阿房宫和王,连骠骑大将军也两千年不见,但是种种之不见、不遇、不闻,却是西西的另一种发现,“敲敲门/对不起/可以进来/听一曲箜篌吗”;《将军》中的城破已听闻不到,戍卒叫、函谷举、楚人的火炬也都不见,“王的步卒与骑骁/都鸦雀无声”,但是历史还在,“你终于发现,王/真正的敌人/其实隐蔽在/什么/地/方”;《石磐》“不过是几块石头罢了”,但是这些石头分明是历史的石头,是再次发声的石头,“只有磬/你听/你甚至可以看到/它即兴时候/朴素的文舞/这天地的风铃/长歌它自己/朗朗郁穆的南音/湮远而又古老/透过战国的隧道/仍然那么/年轻”;即使在博物馆中的《咳嗽的同志》,也能看到一丝历史留下的印记,“他实在瘦/瘦得露出了不少骨头”……
对历史的反思其实构筑了西西诗歌重要的维度,因为那里有文化的积淀,有朝代的兴衰,那何尝不是一种在诗歌中被赋活的存在?《奏折》通过古代皇帝的奏折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之乱,镇江丹阳境内“忽有飞蝗 米价腾/贵 民以艰食为虑”,台州燕海坞处“海盗炮攻起事/掳掠居民 抗拒/官兵”,淮安近海各场“连日风雨/海潮漫涨 防堤/冲决”,还有济南等地的流棍、强贼、饥民,而这一切都在皇帝“硃批”简单一盖中仅仅变成了“奏闻”的存在,而自己则无虑无忧,“朕今大安/七月尽间/即哨鹿起身”;《雨与紫禁城》一诗中的雨不停地下制造了大河的暴涨,“江水倒流/入巴蜀/龙羊峡上/起波涛”,只有皇上所在的紫禁城安然无恙,“护城河内的紫禁城/在我国的地图上/是一处/是唯一处/从来没有水患的/地方”;还有“整座雄关/像一片薄脆饼干/将碎裂倾塌如粉了”的《嘉峪关》,还有“坐在火车里 看/这 残破古旧的”《塞外》……这一切就像在《忽必烈的皇宫》中所写,“二千年来的中国宫殿,一如/封建的帝制,即使转朝换代/从不变改”……
历史在西西的诗歌中回想,这是西西视作中雄浑的一面,而这雄浑更是她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或者回到“异化”主题,西西也正是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寻找人类的解救之道,在《以弗所的三支柱》中她从中国古代转向了世界文明,“站在以弗所三支石柱前,我不知道/这是希腊罗马昔日的辉煌/还是文物古迹沦落的悲哀”;在《飞行的矛》中,西西通过巴西电影《理想国》表达了构建人类理想国的想法,“让我们/惊醒,/沉着等待/那飞行的矛,刺破/层层黑云/让我们腾身飞跃/振臂接取”;这种惊醒和等待就是《建造巴别塔》中的人类梦想,“人类何其渺小而自大,但我们/不能因为梦想无法成真/而放弃梦想,不管上帝怎么想”……
从生活中发现美好到被困于现代的物化,从和古代诗人对话到对历史的反思,从中国现实到世界图景,西西的诗歌在多维中构建一种诗意理想,错误的“美丽大厦”反而被赋予了一种存在的意义,“美丽正在我家梁上做巢”,这是诗歌的使命,这是诗人的担当,就像西西笔下的“庞德”,以汉字解读诗人的名字,并赋予一个永远行走者的写作意义,“彳亍在十字街头的诗人/你用十只眼睛横眉看世界,以一颗/中庸慕道的心建设地上的乐园”……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