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04《一个女人的故事》:我重新让母亲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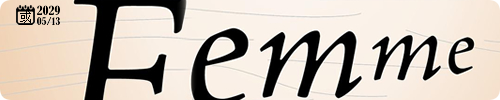
人们不知道我写的是她。我的确不是在书写她,我觉得更像是与她一起生活在她曾活着的时间和地点。
最后的“落款”写着:“1986年4月20日星期日-1987年2月26日”,这是安妮·埃尔诺写作这本书的时间:1986年4月20日,动笔写下关于13天前母亲的去世,它构成了小说的第一句话:“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在蓬图瓦兹医院的老年病房。”1987年,2月26日,在距离写下第一句话10个月后,安妮·埃尔诺终结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就像十月怀胎一般,从初始到终结,书写的故事是一种重生:1940年9月,当我从母亲的世界里降生,我的回忆和讲述构成了生命的重回,“现在,我书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
为什么要书写母亲?为什么要让母亲重新降生?又为什么书写的并不只是个体的母亲?安妮·埃尔诺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既是在讲述自己母亲的故事,又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在讲述“女人”的故事,“女人”构成了小说的三重身份,“我希望我写出的正好是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事情。”所以写作具有的并非是一种私记忆,家庭连接的是社会,女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在“曾活着的时间和地点”中具有一种共性的存在,那么,这个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女人”的故事,又该如何书写?
从母亲之死开始,第一句话就直接指向了死亡本身,在蓬图瓦兹医院的老年病房里已经痴呆两年的母亲病逝了,安妮·埃尔诺从这个死亡的起点开始,以最接近时间的方式记下了了母亲逝世后的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里总是出现一些花:在殡仪馆里,架子上摆放着扶手椅和矮桌子,桌子上放着几本杂志,那些花是人造花;在办事员那里签了支票把棺材买下来之后,发现这里什么服务都有,就是没有预备鲜花;开车去医院附近的新街区寻找花店,想买一束白色的百合花,但是花店老板却劝我不要买,因为白色的百合花严格来讲“是送给小孩子或是年轻姑娘的”。殡仪馆里的人造花,服务项目中没有预备鲜花,百合花不适合送给逝者,我所经历的这些关于花的故事,其实凸显的也是死亡本身带来的结束:当灵车将母亲的遗体运往诺曼底的伊沃托,当母亲被葬在了父亲的身边,当我回到了巴黎大区,“一切都真正地结束了。”
葬礼结束了,母亲的后事结束了,在没有鲜花陪伴的仪式之后,一切真正结束了,于是,我的伤感涌上心头,“她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是对死亡本身的叙述,故事在时间里发生,但是这个死亡又成为了我回忆的起点,“母亲的去世使我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周围的世界”,一种死笼罩在现实里,一种死也将打开另一种时间,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是“我生命中唯一重要的女人”,是那个我不曾了解的女人,却是真正的女人。从这里的书写开始,母亲以“女人”的身份出现,而我则在回忆中书写女人的故事:外祖父是农场的马车夫,外祖母在家纺线,结婚后他们在伊沃托安家;1906年母亲出生,她在家里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她的四个兄弟姐妹一生中从未离开过伊沃托,母亲则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四分之三;外祖父五十岁死于心绞痛,那时的母亲十三岁,母亲的童年有一个“从未被填饱过的胃”,那次吃了一小块面包,她便说:“直到二十五岁时,我还能吞下大海和大海里所有的鱼!”家里的兄弟姐妹都睡在同一间屋子里,母亲和她的一个妹妹睡在一张床上,那时候家里女孩的裙子和鞋子总是姐姐穿完了给妹妹穿……
这是母亲的家庭生活,而在个体的成长中,不断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母亲身上“女人的故事”慢慢从家庭走向了社会:母亲从小就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校里教理问答她可以熟练地背诵所有的答案;十二岁半的时候“既不高兴也不难过地离开了学校”,她在一家人造奶油工厂开始做工,饱受寒冷和潮湿之苦的母亲却从未“看到”人造奶油,从学校来到工厂,这是当时的“普遍规则”,而从未看见的人造奶油又让她的“少女梦幻”时代结束了,对于母亲来说,最重要的事便是在周六的晚上给外祖母带回工资;后来认识了父亲,父亲也是出生在多子女的家庭,也是十二岁辍学当了帮工,他们于1928年结婚;结婚后他们节省着过日子,后来母亲决定开一家食品店,于是一家人来到了距伊沃托25公里外的里尔伯恩,用贷款开了卖食品饮料的小店,在拥有七千居民的工人住宅区开始了生意;1931年出现了经济危机,罢工的人们谈论着一个“为工人阶级而斗争”的布鲁姆,人们关心社会,店里也总是聚集着不肯离去的人……
| 编号:C38·2230408·1936 |
在社会的“普遍规则”中辍学而成为工人,这是母亲“少女梦幻”时代的结束,结婚开始自己开店,这是母亲为理想而奔波的写照,经济危机、持续不断的罢工,又将母亲纳入到一个更复杂的社会中。这是母亲身为“女人”的另一种生活,它连接起了家庭和社会,母亲既是一个要照顾家庭生活的人,又成为了为生存奔波的社会人。而当1940年我出生之后,母亲又因为我的介入而开始了另一重身份,她是我记忆中的母亲,也是我认识的母亲,更是我“书写”的母亲:当这种书写在母亲逝世两个月后再次看见“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这句话的时候,我接受了母亲逝世这一事实,而且“可以像在读描写别人的话一样那么无动于衷”,甚至在我的回忆中“已经忘记了事情的细节”,这样的母亲又是怎样一个母亲?
我和母亲的关系构成了书写的脉络:母亲生下了我;因为山谷的雾气大气候潮湿一家人离开了山谷;一个冬天的早晨,母亲居然闯进了正在上课的教师,要求女教师找回我遗忘在洗手间里的那条羊毛围巾;一次圣餐会上母亲竟然喝得烂醉,从此我开始监视母亲,不让她醉酒;母亲开店认为首先她属于顾客,因为顾客“养活了我们”;她成了远近闻名的人,寄宿学校里老师让我在黑板前做题,题目是:“假设你的母亲卖十包咖啡,价格是……”母亲让我们“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她细心对待书,每次都是先洗手再去拿书……这是母亲的生活,它是在我的回忆中成为了母亲的故事,我的视角构成了对母亲的回忆,无疑,这是被我“书写”的母亲。
但是我和母亲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安妮·埃尔诺在题辞中引用的是黑格尔的一句话:“声称矛盾是不可构想的,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实际上,在一个生命体的痛苦中,矛盾甚至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矛盾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从黑格尔的哲学到个体的成长,再到“女人”的生活,矛盾一直存在也将永远存在,我和母亲的矛盾也不可避免——这种矛盾所体现的恰恰是“女人”的自我意识。母亲是家中最粗暴和自负的女人,这种粗暴和自负其实就是作为社会下层的反抗意识,她拒绝别人以家庭出身对她进行评价;那时候的女孩子被夹在“享受青春”的欲望和“被人指责”的困扰之间,母亲尽量按照社会的要求做一个“靠谱的女工”,她去做弥撒、领圣体圣餐,不单独和男人到树林里约会,但是,她也穿超短裙,她也留男孩子式的短发,她也会有“放肆”的目光,她渐渐远离了人们所要求的“得体女孩”;正因为婚后工资太少,以“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己命运的母亲不想一辈子当工人,开食品店成为了她的一次冒险;在战争爆发的1945年她竟然独自骑着自行车穿越德国人修建的路障,挺着大肚子回家分娩,“她没有丝毫的胆怯,当时的她浑身是那样的脏,以至于我父亲都没认出她来。”
这是母亲的另一面,这是一个女人不为人知的故事,正是这个故事也成为了我的故事,“她身体的一切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那时我想,长大后我将成为她。”成为她是因为我也不是“得体女孩”,是因为我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因为我也学会了冒险:我鄙视社会习俗,鄙视宗教活动,鄙视金钱;我开始抄写兰波和普雷维尔的诗;在作业本上贴上詹姆斯·迪恩的照片,听布拉桑的歌曲;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离开家,开始关注《时尚》杂志里介绍的女性形象,和丈夫认识之后一起讨论萨特和自由,看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奇遇》,支持左派的观点……我成为了她,但是她和我之间却出现了矛盾,“她并不喜欢让我长大。我脱衣服时,她看到我日趋成熟的身体很反感。可能她认为我的乳房和臀部的发育都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意味着我会去追求男孩子,进而荒废学业。她希望我永远做小孩子。”曾经母亲冲破社会习俗的束缚,远离了“得体女孩”的标准,而当现在的我也在成长中追求属于自己的一切,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因为女人的相似,而变成了矛盾。
后来我们一家去了安纳西,我每天要到离家四十公里的山区中学教书,在生活所累中我甚至“一点也不想念母亲”,她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后来父亲去世母亲还是一个人住,我有了某种负罪感,我们住在“资产阶级的大房子”里,有了第二个孩子,但是母亲什么都没有享受到;母亲最后搬了过来,她开始适应安纳西的生活,于是她照看外孙打扫房子,后来还随我们搬到了巴黎地区的新城;但母亲还是在六个月之后搬回了伊沃托,在一个老年人住的单间公寓里生活,“她很高兴再一次获得了独立”;但是197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她在穿越人行横道时被一辆车撞倒……在搬来搬去的辗转中,我和母亲的故事也在矛盾中发展,而这一次又成为母亲生命中一个特殊的起点:被撞之后她的腿骨折、脑震荡,在昏迷了一周之后母亲挺了过来,她会突然对已经死了二十年的妹妹喊道,让她注意有车朝她撞来,“我看着她裸露的臂膀、第一次被万般疼痛折磨的身体,仿佛自己正站在那个在战争期间的一个晚上为生下我而遭受痛苦的年轻女人面前。”母亲康复了,但是精神上却出现了问题:她会在火车站台等待已经开走的火车,出门买东西发现所有的店门都关闭了,要是经常找不到,后来忘记厄兰各种名字,甚至会称我为“太太”。
母亲得了阿尔茨海默,她失去了理智,宗教信仰在她身上渐渐消失,她总是喊着要喝酒,后来她的髋骨断裂了,“她无法再离开她的轮椅,她被一个齐腰的棉布条绑在轮椅上。她被安置在餐厅里,和其他老太太一起,面对电视。”后来我去看了她,吻别之后离开了,第二天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又回到了“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的叙事中,这是一个从死到死的循环,但是“我的母亲死了”在个体死亡之后,又在我的书写中重新降生,这是我赋予“一个女人的故事”更多的意义。当母亲患病的时候,其实关于她的故事已经结束,“这个世界上没有她的位置了”,但是即使在母亲去世之后,我回到托老院看见母亲待过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母亲的复活,“她的位置上还有人”,位置上的人是另一个女人,也可能是以后的我,“也许有那么一天,2000年左右,我也会成为在饭桌前摆弄着手里的餐巾等待晚饭的人其中之一,在这里或是在其他地方。”
这是母亲留下的位置,这是女人留下的故事,对于我来说,看见房间里的灯就是看见了母亲,看见了身为女人的母亲,看见了连接家庭和社会的母亲,看见也是书写的一种,“我知道,我必须通过写作将她现在所成为的痴呆女人与曾经那个坚强的、闪亮耀眼的女人结合起来,否则我无法活下去。”一个女人的故事,当然无法安放母亲一生的起伏,但是一个女人也是其他女人,母亲的故事也是其他母亲的故事,所以在这个安妮·埃尔诺所称既不是传记、也不是小说的故事中,母亲这个女人的故事带来的是书写的意义问题,“她更喜欢为每个人付出,而不是获得。写作不也是一种付出的方式吗?”我的书写就是像母亲一样改变着自己,掌握语言和思想中书写母亲的故事,“为的是让我在这个世界里不觉得太孤单和虚假。”一个女人,是母亲,是女儿,是女孩,是妇女,她们的声音,她们的语言,她们的双手,她们的微笑,她们的疾病,和她们的死亡一起组成了她们的故事,而死亡本身,仅仅是“我失去了与我所来自的世界的最后一根纽带”,但那个房间里有灯光,那个位置上有人坐着,那些故事里还会有生命的降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7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