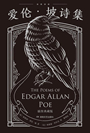2024-05-28《爱伦·坡诗集》:诗的唯一合法领域就是美

直到我几乎在喃喃自语“其他朋友早已离散,
明晨它也将离我而去,如同我的希望已消散”。
这时乌鸦说“永不复焉”。
——《乌鸦》
这是风凄雨冷的十二月,这是暗影笼罩的小屋,这是丧失所爱的男子,在伤悲还未完全逝去的时候,一只乌鸦用翅膀猛扑着窗户,然后栖息在帕拉斯半身雕像上面:乌鸦是谁?它为什么来访?它将带来什么?1945年的诗歌《乌鸦》是爱伦·坡后期的一首代表作,与其说是一首诗歌,不如说爱伦·坡是以小说的方式在书写: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故事发展的情节,最重要的是描写、对话和议论形成的细节,都是小说创作的手法。
“我认为小说构思的习惯模式中有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作者要么是借历史故事来阐明主题,要么是用当今的某个事件来暗示主题,或充其量是动手把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拼凑起来塞进小说以构成叙述的基础”,这样的小说其实就是故事,而这个关于《乌鸦》的故事如何实践着爱伦·坡对这样的错误构思的批判?它如何又成为爱伦·坡的一首诗?《创作哲学》就是爱伦·坡针对《乌鸦》进行的创作谈,他认为小说不是为了讲一个故事,而是为了达到一种效果,每个作者都应该在动笔前问自己:“于此时此刻,在无数易打动读者心扉、心智或心灵的效果中,我该选择哪一种呢?”只有选定了强烈的效果才会考虑是否用情节创造情调,在他看来,大小转轮、启幕滑轮、活动楼梯、活动板门、华丽服装、胭脂口红以及黑色的饰颜片,都隐藏在幕后,却是艺术家必不可少的用具;当然,在创作中最重要的是要施予一种“强烈的刺激”,它的作用就是启迪心灵,而这和情节所创造的情调,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作者所追求的效果达到了完整性和统一性;爱伦·坡强调一首诗的长度必须有一个限度,只有在限度里,作品才可以“精确地”与价值相称,与刺激或启迪相称,与效果的程度相称,这个说法在爱伦·坡另一篇讲稿《诗歌原理》中有更直接的表述:“诗之所以是诗,仅仅是因为它可在启迪心灵的同时对其施予刺激。诗的价值与这种有启迪作用的刺激成正比。”
要先确定作品期望的效果,要创造情节所传达的情调,要把作品限定在一定的长度内,这些都是爱伦·坡在作品创作中的具体甚至有些标准化的方法,但是真正的创作对于爱伦·坡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如何表现美?“我历来坚持一种观点,即诗的唯一合法领域就是美……”什么是美?爱伦·坡认为,“那种最强烈、最高尚、同时又最纯洁的快乐存在于对美的凝神观照之中。”在他看来,美不是一种质,而是一种效果,是强烈而纯洁的心灵升华,只有在对美的凝神关照中才能有所体验。对于美的阐述其实表达了两层含义:效果的传递需要达到一种美,它可以在灵魂的交流中得到升华——作者和读者之间;另一方面,作品本身就是在书写美,美就是诗歌的合法领域,也是诗歌主题的领域。而这两者在《乌鸦》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哦,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风凄雨冷的十二月,/每一团奄奄一息的余烬都形成阴影伏在地板。”从一种阴郁的氛围开始,外面的风凄雨冷和里面的余烬阴影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在这样的世界里,屋子里的“我”就像是一个行将死去的人,死亡带来的强烈效果是因为死亡正在发生,它是从死亡开始正在进行的死亡,“因那位被天使叫作丽诺尔的少女,她美丽娇艳,/在此已抹去芳名,直至永远。”但是很明显,少女丽诺尔的死亡首先是现实中的死,这种死亡所毁灭的是她的肉身和她的名字,它们在具象意义上是一种“美”,但是这种美在死亡发生后却在我的心灵起到了强烈的效果:美之逝去。当窗外的乌鸦猛扑着,当我抬头看见这个“不速之客”,我把它叫做“神圣”的乌鸦,它像是给我问候,它像是带来安慰,而且就栖息在房门上方一尊帕拉斯半身雕像上面。于是我乌鸦当做了一种寄托,和它进行了对话。
“冠毛虽被剪除,但你显然不是懦夫,/你这幽灵般可怕的古鸦,漂泊来自夜的彼岸,/请告诉我你尊姓大名,在黑沉沉的夜之彼岸!”乌鸦被当作自彼岸的幽灵,乌鸦被看成是黑夜的鬼魂,而且对于我的问题,乌鸦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永不复焉。”而且每次对于我的提问和对话,乌鸦只是在重复着这句话。“永不复焉”的重复传递,在诗歌的节奏和情调营造上达到了爱伦·坡的创作目的,而在主题上,乌鸦之回答,乌鸦之重复回答,其实完全可以看做是我的自我回答,“永不复焉”的否定性答案指向的是死亡之后的另一重死亡:它是朋友的离散,它是孤独的体验,它是美的消逝,更为重要的是,当我愤怒于乌鸦是恶魔,“是不是撒旦派你,或是暴风雨抛你,来到此岸,/来到这片妖惑鬼祟但却不惧怕魔鬼的荒原——”我甚至命名了乌鸦的死亡性,而乌鸦还是以“永不复焉”来回答:乌鸦依然栖息在哪里,依然在雕像上面,它的目光依然和魔鬼的一样,而我在经历了死亡之后是不是在“永不复焉”中再次走近死亡?“而我的灵魂,会从那团在地板上漂浮的阴影中/解脱么——永不复焉!”
从死亡到死亡,是重复,却又是“永不复焉”,不是乌鸦带来了死亡,也不是乌鸦重复着死亡,更不是乌鸦取消了死亡,而是在死亡的不同演绎中,美从消逝变成了降临:丽诺尔的死亡是美的一种消逝,当乌鸦来到,它带来了或者说启迪了我对于另一种美的刺激,那就是悲郁之美,爱伦·坡问自己的是:“依照人类的共识,在所有悲郁的主题中,什么最为悲郁?”他找到的答案是:死亡。死亡最初是美的消逝,而现在死亡变成了美的表达,这是乌鸦“永不复焉”带来的感悟,或者说,乌鸦这一意象就是一个象征,“乌鸦所象征的是绵绵而无绝期的伤逝”——它不是被魔鬼附体,不是幽灵的存在,而是我通过乌鸦的“永不复焉”找到了美的双重表达:它随肉身而消逝,它以悲郁而现身,消逝和悲郁都是美,却是“永不复焉”带来的升华,“任何美一旦到达极致,都会使敏感的灵魂怆然涕下。所以在诗的所有情调中,悲郁是最合适的情调。”
| 编号:S54·2240221·2063 |
一首《乌鸦》,一篇《创作哲学》,爱伦·坡注解了美“永不复焉”的本质,而这种“永不复焉”的美在1945年被阐述之前,就已经贯穿在爱伦·坡的诗歌创作中。在这个世界只逗留了四十年的爱伦·坡,也只留下了四本诗集的60余首诗歌,在他只有18岁的时候就出版了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这本收录了10余首诗的诗集出版后少有人问津,爱伦·坡在序中也说这是对世界还一无所知时发出的声音,“作者竭力要揭示那种为了实现雄心壮志而不惜用心中最美好的感情去冒险的愚蠢。”诗集也成为“谬误”的象征,一方面是对于社会性谬误的观察,在《哦,时代!哦,风尚!》中他就认为这个时代“世风日下”,流行已是流水落花,只剩下“美好的往昔”,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人生的茫然,“我是一种思想,不管怎样做最好,/是严肃对待人生,还是把人生当玩笑”,在茫然中却又有着巨大的战斗热情,“虽然不是与信仰——与虔敬——其宝座/早已把它击败——以雷霆万钧之力;/戴上它自己的深情作为一顶荣冠。(《诗节》)”,这样的激情,这样的战斗,同样是一种盲目,所以爱伦·坡说:“他太偏爱自己的少作,以致不愿在‘老年’时来修改它们。”
有过漂泊的经历,化名应征入伍,当过报刊编辑,娶了十四岁的表妹弗吉尼亚为妻,为了支撑一家三口而苦苦挣扎,《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小诗》、《诗集》和《乌鸦及其他诗》这三本诗集反应了爱伦·坡在生命中的这些际遇,但是对于诗歌本身或者文学本身而言,他就一直走在“永不复焉”的那条路上,在消逝和悲郁中体验着死亡的双重性,死亡的双重性带来的是美的双重性,而死亡和美构筑的激情就是爱伦·坡一直在追求的快感——含混的快感:“依我之见,诗与科学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诗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快感,而不是求得真理;诗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诗的目的是获得含混的快感,而不是明确的快感。”在《乌鸦及其他诗》的序言中,他更是将这种“激情”放置在了属于自己的最隐秘处,“对我而言,诗并非一个目的,而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应该受到尊重,它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为了人们微不足道的报偿或更微不足道的赞赏而被随意唤起。”
美是易逝的,它在爱伦·坡所致的每一个名字后面体现出来,它是《致玛格丽特》中的澄澈纯净,是《致奥克塔维娅》中的“搏动的悲哀的希望”,是《致海伦》中的“芳菲的大海”和“尼西亚的小船”,是《尤拉丽》中的“美丽温柔”,是《献给安妮》中“亮过天上所有星星”的目光,也是写给初恋情人莎拉·爱弥拉·罗伊斯特的《歌》中的“那团红霞”,是写给迷人的艾德琳的《小夜曲》中“爱人的歌声”,是写给弗朗西斯·萨金特·奥斯古德关于爱的“朴素的天职”……女人的名字是美的象征,她们都在诗歌里唤醒了爱伦·坡的激情,“这爱与美都属于我们自己所有!/美过青春希望所知,在它最快乐的时候。(《梦》)”名为《梦》,它就是易逝的,在所有被命名的美和“爱人”中,“我仅仅是一名过客”所感受的就是一种无法把握的逝去。
因为美的易逝性,所以美也就走向了死亡,但是在爱伦·坡的诗歌中,美所代表的爱神和死亡背后的死神契合在一起,或者说,爱神的另一面就是死神,这是对爱和死亡在一种灵魂上的升华。《帖木儿》中的帖木儿在征战,帖木儿登上王位,“战斗的呐喊,胜利!凯旋!”但是这种荣誉却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却是最后走向了死亡,“于是我把自己裹得富丽堂皇,/并戴上一顶想象的王冠——”这是一种死亡,对于帖木儿来说,他对灵魂发出的疑问是:“那我为何要丢下爱去漂泊沉浮,/去迷恋那团火,去期待那道光?”得到了荣誉和王位,取得了胜利和地位,只不过是诱惑,只不过是罪戾,但是却失去了最美好的东西,所以死亡更指向了逝去的爱,“弥留之际听仁慈的安慰!”帖木儿在爱伦·坡的笔下成为了忏悔者,“我该如何解释给他一名‘圣徒’来听他临终忏悔呢——我也说不清楚。他需要有人来听他的故事——干吗不能是一名圣徒呢?这种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这对我的目的就足够了——至少我对这种新说法有充分的根据。”在死神逐步靠近的时候,帖木儿问神父最后,“我如何离开那尊偶像——爱神”——离开爱神便是死神的降临。
爱神和死神的关系同样在《阿尔阿拉夫》中。“啊!没有俗物,只有那道眼光,/那道(从花间反射的)美人的眼光,/就像在那些花园,白昼在那里/从塞尔卡斯的宝石堆里升起——”这里就是天堂,是爱神的领地,妮莎就是爱的象征,“这漂泊王国的女王/离开了她的宝座——丢下了权杖,/闻着袅袅焚香,听着隐隐圣歌,/在四重光里把她可爱的手足洗濯。”而在地上,凡尘之处有着“理想之美”——“天籁”和“理想之美”构筑了爱神的世界。但是,“可寂静终于笼罩这世间万事万物——/美丽的花、天使的翅、晶亮的瀑布——/只剩下从那个灵魂发出的声音/陪衬着那位少女唱出的咒文”,死神来了,是快活变成罪过的死亡,“坠落的他——他是个英俊的灵魂”,永不再返尘世?“他们坠落:因为上帝对他们失去信心,/他们因自己的心跳听不见上帝的声音。”这就是阿尔阿拉夫这个介于天堂和地域之间地方的意义,它是爱神之美和死神之悲剧的中间状态,“阿尔阿拉夫的特征之一就是,即便在死后,那些选定该星作为归宿之地的人也不能获得永生——而是在令人激动的第二次生命之后坠入忘川和死谷。”来自于《约伯记》的思想便是:“我不会永生,请别管我!”
因为爱之逝去所以死亡,但是就像《乌鸦》的“永不复焉”一样,死亡也应该是一种美:悲郁之美,所以在爱伦·坡的后期诗歌中,“永不复焉”变成了另一种结合,“死亡就在那有毒的涟漪里,/在它的深渊,有一块坟地/适合于他,他能从那墓堆/为他孤独的想象带来安慰——/他寂寞的灵魂能够去改变,/把凄凉的湖变成伊甸乐园。(《湖——致——》)”在死亡中,墓地变成了伊甸园;“我不能爱,除非死神自己/把他的气息与美的气息混在一起——/或婚姻之神、时间和命运女神/在她与我之间正悄悄地走近。(《序曲》)”魔鬼也长着一张爱人的脸,死神也在靠近爱神;“美都在沉睡——瞧!那边/躺着伊蕾娜,伴着她的命运!”而另一边是“那是死者在墓中发出的呻吟。(《睡美人》)”美就是死亡发出的声音……“永不复焉”所传递的灵魂统一性便是爱伦·坡诗歌创作的终极目标,他在《诗歌原理》最后一段中强调了“真正的诗”:
关于何为真正的诗,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更直接地犾得一种清晰的概念,而这只需要借助一些可在诗人心中唤起真正的诗歌效果的普通要素。发光的天体、绽开的鲜花、低矮的灌木丛、起伏的麦浪、倾斜的东方大树、遥远的青山、聚集的乌云、时隐时现的小溪、泛着银波的大河、远离尘嚣的碧湖之静谧、映着星光的孤井之深邃——诗人从这一切中发现滋养他灵魂的神粮。百鸟的啼鸣、埃俄罗斯的琴声、晚风的悲泣、森林的呼啸、浪花对海岸的抱怨、树林清新的呼吸、紫罗兰的芬菲、风信子的馥郁芳泽、傍晚时分越过神秘莫测的茫茫大海从远方荒岛上飘来的幽香——诗人从这一切中感知滋养他灵魂的神粮。在所有高贵的思想中,在所有超凡脱俗的动机中,在所有神圣的冲动中,在所有慷慨无私、自我牺牲的行为中——诗人获得滋养他灵魂的神粮。在女性之美中——在她们优雅的步态中,在她们明亮的眼睛中,在她们悦耳的嗓音中,在她们柔和的笑声中,在她们悲哀的叹息中,在她们衣裙和谐的窸窣声中——诗人感觉到滋养他灵魂的神粮。在女性迷人的爱抚中,在女性燃烧的热情中,在女性慷慨的施予中,在女性温顺而富于献身精神的忍耐中——诗人强烈地感觉到滋养他灵魂的神粮。但更重要的是一啊,最重要的是——因了女人爱之忠诚、爱之纯洁、爱之强烈、爱之崇高和爱之神圣——诗人五体投地地信奉这种滋养他灵魂的神粮。
所以死亡是灵魂的安息,灵魂又是死亡的起点,这是爱伦·坡作为诗歌创作者的探索实践,他也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阐述了人生这一首诗歌的终极归宿:1849年10月3日,有人在巴尔的摩街头发现了处于昏迷状态的爱伦·坡,这时距离他的妻子弗吉尼亚夭亡只有两年多,而四天后他死于一家医院,据目击者称,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保佑我可怜的灵魂。”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