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28《桥》:所谓“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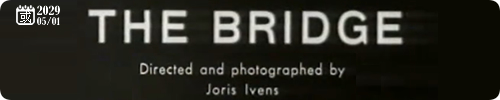
桥,是鹿特丹玛斯河上的桥,是沟通两岸的铁路桥,是可以升降实现火车和轮渡交叉通行的桥……桥的地理位置,桥的功用,桥的外观,桥的特殊意义,都成为“桥”的一种定义,但是这些关于桥的定义都是静态的,都是一种对于“事物”本身的命名,而一旦进入到尤里斯·伊文思的摄影机里,“桥”变成了运动的桥,变成了变化的桥,变成了承载交通意义的桥。
摄影机,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伊文思用全景拍摄远处的这座高大的桥之后,镜头却给了摄影机以及“持摄影机的人”,这一个镜头是富含深意的,摄影机不在背后,不是工具,它在画面中被拍摄,是推到前台的象征性存在,具有了叙事的主体性,也正是这个主体的凸显,持摄影机的人变成了观察者和记录者,而这种观察和记录就超越了对个体事物的静态拍摄,而成为“伊文思之眼”中的存在。首先从镜头的变化来说,伊文思之眼制造了“运动”:用全景拍摄远处大桥的全貌;在桥上,拍摄了正疾驰而来的火车,车轮、铁轨构成了运动的状态;从桥上俯视,是河道上行驶的船只;从两边望出去,是远处的水面;从行驶的火车上拍摄,是静止的桥,是两边的物,是流动的河水,是在马路上行走的人和行驶的车——伊文思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几乎选择了所有可以站立的地方,当他使用不同的镜头语言,富有层次的画面就成为了一种“运动”,它以不同角度构成了对大桥不同角度“环境”的描写。
这些镜头对大桥的描写也还是在一中静态中完成,但是大桥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座可以升降的铁路桥,当桥面降下的时候,它提供给火车通行的路,但是当它升起的时候,又可以使得下面的船只尤其是大型轮船可以畅通无阻。所以“伊文思之眼”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让这座升降桥在升降的物理变化中产生运动美学。伊文思记录了工作人员走上阶梯,来到高处观察桥体的过程;接着是拍摄桥特殊的装置,齿轮、绳索和控制杆;之后操作开始,在操纵杆的操纵中,桥面开始“断开”,两边开始缓缓上升,本来水平面的桥面慢慢变成了垂直;达到完全垂直之后,下面的大型轮船慢慢通过;当轮船通过,桥面又从垂直状态慢慢倾斜,最后变成起初的平面状态;合拢之后,等待在那里的火车再次启动,桥又变成了火车的通行之路。
| 导演: 尤里斯·伊文思 |
在记录桥面从平面到垂直,再从垂直到平面的过程中,“伊文思之眼”随着摄影机的运动而展开:操纵控制杆、齿轮运转,标尺上升,当桥面斜拉而竖起,伊文思的镜头也保持着垂直状态,它沿着水泥桥墩向上,之后给了桥面连接处特写,然后在高处俯视水面,俯视船只,俯视大型轮船通过大桥——摄影机捕捉到了一群飞鸟,它们的飞行装点了这座桥的宏伟;当随着桥面缓缓下降,伊文思的镜头再次跟拍这一过程,而且在桥面呈现90度垂直和180度平行的时候,摄影机一直没有中断,在保持连接中展现了桥体的变化,也带来了运动的效果。
在这里,伊文思之眼的意义就是一种连接,连接桥体的变化过程,连接桥面的运动过程,连接桥不同功用的过渡。桥本身承载的是“交通”的意义,桥面连接时让火车通行,桥面垂直时让轮船通行,在垂直和平行的交换时,两种交通变成可能。而伊文思镜头下的“桥”在影像上也实现“交通”:交汇而沟通,在上和下、起和落、行和听之间,镜头始终在记录,在叙事,在连接,它所去除的是对桥各个零件和部位孤立而简单的描述,它们融合在一起,成为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最后凸显的是桥“交通”的最本质属性。对于伊文思之眼的这一叙事,吉尔·德勒兹在《运动-影像》中有过专门的阐述,他认为在伊文思的镜头中,“桥”所呈现的并不是桥的概念,也不是“透过形式、金属建材、用途和功能”定义的个体化事物状态,金属建筑物被消解为“非物质性”的影像,也不再是工程师依据确切目的而生成的创造物,而是一连串“视觉效果的奇特系列”,是火车无法通过其上的“视觉变幻”,是用摄影机表现了“潜存性”:“七百个镜头的快速剪接使得不同的视野接合成物质的无限性,可是也不是将这些视野导向连接,而是成为任意空间中由相互调合之独特性所组成的整体集合,在该整体集合中,桥就只是一种纯粹质性,金属就如同纯粹力量,而鹿特丹自己就成为了动情力。”
运动的美感,钢铁的力量感,物质的无限性,组合的自由性,这一切构筑了“桥”的整体性,或者说,“桥”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力量,一种无限,一种自由,摄影机容纳了一切,创造了一切,而那个特写的摄影机和“持摄影机的人”构成了电影真正的主体。

《桥》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