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28《生命的烙印》:政治裹挟下的个体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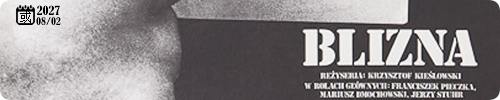
他走到年幼的外孙女身边,给她玩具,逗她嬉戏,只是尚未开始学步的婴孩想要站起,却又坐下,在几次尝试失败之后便开始哭泣,而面对孩子的哭声,他一时手足无措。这是最后一个镜头,已经从厂长岗位上下来的史提芬进入了家庭生活,扮演起外公的角色,但是这种角色的转换是不彻底的,在大人和小孩无法交流的尴尬处境中,就像婴儿本身,无法站立,只能哭泣。而这种无助的状态也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给这个时代中的理想主义做出的注解:在固定镜头里,前景是门框,是杂乱的呈现,远距离的家庭生活只在右侧四分之一的画面中被展示出来。
回归家庭生活变成了无奈和尴尬,家庭身份的转换变成了狭小的天地,开起来开放,却依然是一种封闭的空间。刻进他身体的“生活的烙印”到底是什么?当史提芬从华沙来到小城奥勒哥,当被政府选中成为新建化工厂的厂长,他是怀着某种理想的,那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改变小城贫穷和闭塞的面貌,通过投资加快该地区的发展——这种理想主义无疑还有一种家乡情结,奥勒哥就是自己和妻子出生的地方。当史提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他其实忘记了自己只不过是政府“选中”的人,自己的一切计划都无法脱离那个在背后指挥的体系,当体系主宰了一切,他便成为一个悬空的人,在狭小而封闭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史提芬的理想主义体现在多重维度中,一方面在个人意义上,他喜欢摄影,电视台的记者加拉奇是他的朋友,他就曾告诉加拉奇,自己想要拍摄一部“不是黑白分明的纪录片”,无疑,这种对黑白分明的否定就是去除政治干涉,让摄影和艺术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他在波兰战争期间拍摄的照片就是在寻找这种理想主义,甚至在他成为厂长之后,在政府主席为他安排的住房里,他把旁边的两间屋子改装成了暗房,用来洗照片。另一方面,他和妻子、女儿伊娃的关系也表现出他一意孤行的性格,当他告诉妻子自己要去奥勒哥当厂长,妻子拒绝同行,“这是发展的大好时机,因为以前我被遗忘了。”这是史提芬的观点,但是妻子坚决不去,她没有说出自己的理由,只是说伊娃可能要堕胎。后来史提芬见到了分开很久的伊娃,当伊娃给他新的电话号码时,史提芬说:“这是你第四次新换的号码。”不想伊娃针锋相对:“你也经常换号码。”而伊娃直接指出,“你根本不了解妈妈。”面对女儿的责难,史提芬却说:“你妈妈一个人可能更快乐。”无疑,夫妻之间,父女之间都存在着隔阂,妻子拒绝奥勒哥,按照史提芬的说法,是因为前几年发生了党派的矛盾,所以妻子不想再参与其中,但是对于史提芬来说,这种拒绝变成了逃避,让妻子一个人生活反而是对她的讽刺。
| 导演: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
妻子由于目睹甚至参与了党派之争,从而对政治意义上的工程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而史提芬似乎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委,他把建设工厂看成是小城发展的机会,让自己成为厂长当成理想的一次实践,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进入了完全不受控制的政治漩涡中。一方面对于工厂投资存在着某种误读:史提芬认为这是发展的好时机,他赴任之后立即启动了工厂的建设,在化工厂投产之后还着手进行厂房的扩建,这的确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良好机遇,但是投资本身也是一种破坏,在没有建厂之前,加拉奇就告诉了他自己叔叔的意见,身为大学教授的叔叔认为,建厂而砍伐树木,是一种破坏,是文明的倒退,但是史提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后来有报纸刊文认为,化工厂选址不当,因为必须砍伐掉一万公顷以上的树木,这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干旱将是小城今后几年遇到的自然灾害,在舆论面前,史提芬也没有重视;当地居民反对建厂,认为这是对家园的摧毁,有人甚至在挖土机进场后拒绝搬迁,“压死我好了……”这种以死抗争的行为让史提芬制止了工厂建设进度,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
史提芬的“漠视”并非是看不到建厂带来的危害,而是在他心里有另一种理想主义,在他看来,建厂是投资,投资是发展,发展能改善当地的生活水平——因为建立工厂意味着解决了就业问题。的确,在工程进行建设的时候,很多当地人聚集在外面,希望解决自己的失业问题,甚至人潮涌动将玻璃都挤碎了,史提芬更是将有专业毕业证和没有毕业证的人都登记在册,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工厂会带动就业,会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是投资带来的好处,但是同样造成了环境的破坏,甚至带来了家园的摧毁,而且化工厂还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在这个矛盾中,史提芬显然只看到积极的方面而没有发现消极的一面,在无可持续发展的短期行为中,史提芬的坚持只能将他带向群众的反面,他无疑变成了个人主义者。
但是,这似乎并不是主要的,史提芬的个人理想主义忽视的最大问题是:这是被政治控制的项目,他是被党派利用的棋子。“我们为他们卖命。”这是政府主席的观点,所谓的投资,所谓的建厂,只不过是政治之争的砝码,也正是在政治裹挟下,个体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一方面是那些当地的群众,他们生活的环境被破坏,他们的家园被毁坏,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了牺牲品,最后谈判不成沟通无效,便引发了最终的罢工,“关闭工厂”成为他们的口号,也演化成后来的“格里基斯事件”;另一方面对史提芬来说,他越来越发现自己失去了主动性,本来是为了解决当地人的就业问题,不想很多人是政府安排的,运输处的主任甚至没有经过人事的讨论就掌握了大权,而真正想要找工作的当地人被警察赶了出去,而且工厂选址、规划、扩建也都是由政府决定,更让史提芬难以接受的是,自己曾经的仇敌莱克也被政府安排进了工厂,而当史提芬最后提出辞职,接手他的竟然就是莱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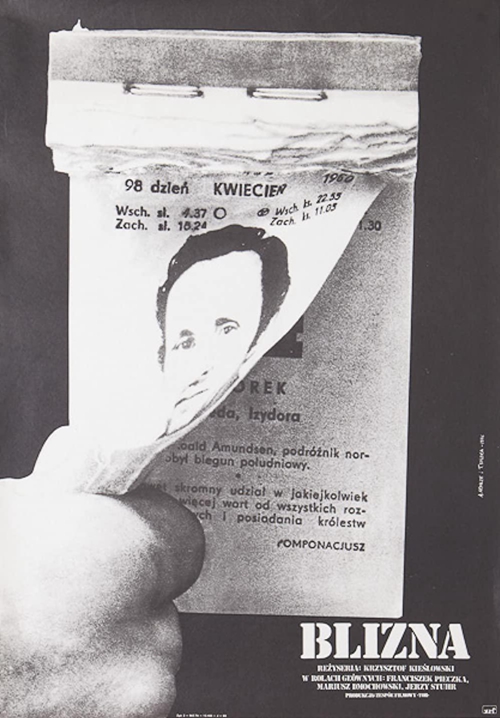
《生命的烙印》电影海报
政府操控了工厂建设的全部,但是当与当地群众出现矛盾,当“关闭工厂”成为行动的口号,政府又归罪于厂长,在那次会议中,政府开展了对史提芬的调查,认为他在解决工人问题上办事不力,没有和党组织进行沟通,而是想凭一己之力解决,结果反而激化了矛盾,“一个人不能成大事”,主席的这句话便是对他的警告,便是对个体行为的抹杀,便是重回政治体制和集体主义的暗示。坚持自我的史提芬在最后时刻还是强调办事风格不会改变,最后在批评声中,在事件调查中,史提芬结束了自己身为厂长的“政治生活”——不是主动选择了辞职,而是被迫下台,那部不是黑白分明的纪录片终于没有拍成,而自己成了黑白分明世界的牺牲品。
史提芬的个体理想主义遭遇了政治的解构,而基耶斯洛夫斯基似乎也在拍摄一部“不是黑白分明的纪录片”中看见了社会的弊病。这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从纪录片转型为剧情片拍摄的一个标志,但是很明显,纪录片的痕迹还很重,那场对史提芬调查的戏完全是短片《工人》的翻版,重在记录的风格也破坏了叙事的整体性,无论是史提芬还是他的妻子、伊娃、加拉奇,人物的形象都欠丰满,故事的叙事也语焉不详,比如妻子当年被卷入的政治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莱克和他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也体现在和妻子的情感上?伊娃当初想要堕胎有又怎样的难言之隐……这些情节在剧情中都呈现出缺省的状态,而史提芬的情感发展也处在一种表面的叙事上——基耶斯洛夫斯基似乎无法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无法在介入政治生活中挖掘出人性上的深度,都说明他的拍摄存在着一个审查上的禁区,无法突破禁区便也只能保持游离状态,在不真正激化社会矛盾的妥协中完成记录,只有最后一个镜头充满了寓意:像婴儿一样无法独立,是史提芬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现实;被控制在狭小的世界,是叙事被禁锢的无奈;固定的长镜头,走向自我表达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