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22《裴洞篇》:考察“是者”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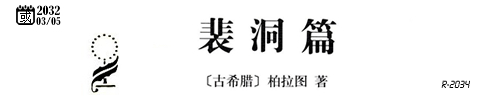
艾克格拉底啊,这就是我的朋友的末日。我可以说,在我们所认识的当时人中间,他是最善良、最明智、最公正的人。
太阳已经下山,行刑的时间到了,苏格拉底没有发抖,表情没有改变,他问行刑的人是否可以从杯子里倒一点毒药来奠神,那人说,只准备了够用的,苏格拉底依然向神做了祈祷,然后“爽快地、安静地一饮而尽”,之后就躺在那里,等到毒药发作冷到了大腿根,苏格拉底对格黎东说了最后一句话:“我们还欠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了。”格黎东答应了他,之后苏格拉底最后动了一下,行刑者揭开了苏格拉底的遮面物,“他的两眼定了。”格黎东就将苏格拉底的嘴和眼合拢了。
这是苏格拉底走向死亡的过程,在场的裴洞目睹了这一切,他把这一刻叫作“朋友的末日”,当苏格拉底逝去,裴洞当然和在场送行的人一样感到悲伤,“在这以前,我们中间多数人还能控制自己,忍住自己的泪水;等到目击他举杯的举止,看到他服尽毒药,我们就沉不住气了;为了不让自己泪如泉涌,我用大氅遮着脸暗自饮泣;这并不是为他而泣,而是因为我不幸失掉了这样一位朋友。”但是当他在艾克格拉底面前回忆时却说那时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感到既乐又苦”,苦是因为朋友即将逝世,作为人之常情肯定是悲伤的,这就是他的“苦”,但是苦中又有乐,而且裴洞说在场的人都有“时而欢乐,时而悲泣”的共同感受,之所以拥有这种感受,因为苏格拉底很从容面对死亡,因为苏格拉斯传递了讨论哲学时的快乐,更因为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不是赴死,而是出于神意走向了另一个世界,“我身上遇到的看来正是这样:我的腿由于戴脚镣弄得很痛,现在我感到随之而来的快乐了。”
面对死亡没有悲痛只有快乐,死亡不是消亡而是出于神意去往另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死亡不是死亡,而是一种不死,不死的当然是灵魂——《裴洞篇》在公元前1世界由柏拉图学派编订时就加了《论灵魂,或伦理的》副题。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爱利亚派创立者,裴洞在艾克格拉底面前回忆了苏格拉底的“末日”,在场者除了他之外,还有雅典本地人阿波罗多若、格黎多步洛和他父亲、赫尔谟根尼、艾比根尼、爱斯钦和安底斯滕,以及格底西波的巴央人,还有梅内格森和一些别的本地人,外地人则有特倍的辛弥亚,以及格贝和裴洞尼德,以及梅伽拉的欧格雷德和德尔普雄,但是柏拉图没有在场,裴洞说:“我想柏拉图是病了。”虽然柏拉图并没有在场,但是他却处处在场,因为苏格拉底在死前对灵魂的阐述就是柏拉图的观点。
“我要从头到尾给你全部说清。”裴洞的回忆构成了一个嵌套的结构,关于灵魂的讨论就是从死亡开始的,“我认为对于一个行将辞世的人来说,最合适的事情无过于谈谈来世的情况,考虑一下我们对来世的想法……”苏格拉底首先提出了一项“申诉”,那就是关于死亡的神意说,“我有力地坚持自己走向那些最为善良的主人——神灵。”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忧伤的原因,甚至他还坚定地希望给亡者准备赠品,为什么会有这样面对死亡的勇气,甚至苏格拉底会把死亡看成是去往另一个世界的福祉?那就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献身哲学的人就是要学会赴死和死亡。死亡不是别的,就是灵魂对肉体的脱离,就是灵魂获得独立存在的状态,在苏格拉底看来,当灵魂脱离肉体而获得独立,就能获取真知,达到真理,也只有死能去除肉体的障碍完成这一哲学家所追求的状态,“灵魂最能思考的时候,是在它摆脱一切干扰,不听,不看,不受痛苦或快乐影响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它不顾肉体,尽可能保持独立,尽量避免一切肉体的接触和往来,专心钻研实在的时候。”
苏格拉底将灵魂和肉体进行了二分,在他看来,视觉、听觉以及身体其他的感觉,获得的东西都不能认识实在,甚至它就是一种累赘:
肉体使我们充满各种感情、欲望、恐惧以及各种幻想和愚妄,真正说来教我们不可能进行思考。战争、革命和争斗的唯一原因是肉体及其各种欲望。因为一切战争的产生都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肉体而被迫赚钱的。我们是为发财而奔走的奴隶。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失掉了钻研哲学的余暇。最坏的是我们忙里偷闲关心哲学的时候,肉体经常闯进来用喧嚣和混乱打断我们的研究,使我们不能瞥见真理。
而灵魂的思考需要摆脱一切干扰,避免一切肉体的接触,只有死亡发生,才能让灵魂和肉体分开,才能让灵魂真正得到净化,死亡就是哲学家思考的状态,“真正的道德实际上是斩净这一切相对的情感,这种净化就是明智、公正、勇敢和智慧本身。”这就是苏格拉底首先提出的“神意说”,死亡不再是恐惧的深渊,而是哲学家向往之处。但是在场的格贝提出了疑问,在一般人看来,当人死亡后,肉体消灭了,灵魂也必定离开肉体而飞走,如何证明人死后灵魂还会继续存在并且“保持某种能动的力量和智慧”?从这里开始,苏格拉底真正开始阐述灵魂的性质,他提出了“转世说”,“我们还记得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认为这些灵魂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再回到这里,从死者托生。”用一个古老的传说来论证灵魂转世,这或者是柏拉图借由苏格拉底论述,显得缺少严密性,因为苏格拉底就是从这里论证灵魂从死者那里转生的:既然活人由死人托生,那么灵魂就必定存放于彼处,否则它就不可能托生,就不可能再度在活人中。
| 编号:B31·2241021·2195 |
苏格拉斯首先提出问题,“那我们就充分肯定这个事实,肯定一切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对立面生自对立面?”所谓对立面的关系就是在一端到另一端之间有一个不是直线的运动,它就是产生,活产生的是死,,那么从死产生的当然就是它的对立面,即死——如果没有这个对立面转化的过程,那么一切事物都是一样了,都达到了同一状态,就不会有产生了,活人就不会死,同样死人也不会活,所以当死亡发生,灵魂从肉体中独立,也就意味着灵魂还将返回到活人中。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格贝就说起了苏格拉底提出的学习即回忆的说法,作为补充的论证,苏格拉底说:“一个人如果要回忆什么事,一定得在以前某个时候知道这件事。”但是苏格拉底并不仅仅是一种补充论证,他由此将对灵魂的论述从转世说深化为“不变论”——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
“如果我们在出世以前就获得了那种知识,带着它生下来,那我们在出世以前和出世的时候就不仅知道相等、大于、小于,而且知道这类的一切事情吗?我们现在的论证不仅涉及相等,而且涉及美本身、好本身以及公正和虔诚,总之,涉及我们在问答过程中称之为‘某本身’的一切。所以我们必定在出世以前就已经获得了这一切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是在出世前就获得了,只不过出世的时候我们遗忘了,后来我们在学习中回忆起了原有的知识,这也就证明了灵魂也是先就存在的,是人形之前就获得的,而这也构成了苏格拉底关于灵魂就是从死亡状态中再生的过程:“一切生物都是从死物里生出来的。如果灵魂存在于出世以前,而它在进入生命、产生出来的时候,是不能从他处、只能从死亡和死亡状态中出世的,那它既然必须再生,就必定也在死后存在了,是不是?”所以他驳斥了在场的辛弥亚和格贝的想法,“你们有一种幼稚的恐惧,以为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会随风飘散,特别是死时大风怒号、天气不好的情况下。”
灵魂在人死后却去往另一个地方,又在人身上再生,之所以灵魂超越肉体和生死,就在于它不是易于解体的复合之物,而是始终如一的存在,“那些永远如一的实体却只能用理性去把握,是看不见的。”灵魂就是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这个理念,““灵魂单独由自身察知的时候,就进入那纯粹、永恒、不朽、不变的领域,以自身的不易灵性为本,于独立不受阻碍之时,就永远与那些不变性质同在,永远如一,常住不变,因为它与永恒是相通的。灵魂的这种状态就叫明智。”正是有这种神圣的、不朽的、灵明的、齐一的、不可分解的、永恒不变的灵魂存在,就需要理性来把握,而研究哲学的人就是要抛弃身体欲望,通过哲学的解放和净化作用,把握这个永恒的灵魂,“因此心向哲学,一切听从哲学,拳拳服膺。”
从死亡去往另一个快乐世界的“神意说”,到灵魂再生的“转世说”,再到学习的回忆说,再到灵魂的不变论,苏格拉底就阐述了哲学家“爱智慧”的真正意义。但是之后辛弥亚和格贝又提出了他们的不解,而就是从这里开始,苏格拉底进入到了对更具形式逻辑意义的“型相”的阐述。辛弥亚提出的问题是,和声是不可见的、无形体的、神圣的东西,就像灵魂,而有形体的、组合的竖琴和琴弦则像死亡,当有人破坏了竖琴或者割断了琴弦,那么和声不就毁灭了?同样,作为和谐的灵魂是不是也会随着形体的死亡而消失?“如果有人主张灵魂是身体要素的调和,所以会在所谓死亡的时刻首先消失,我们用什么话来答复这种说法呢?”格贝则从老纺工的比喻出发,在他看来衣服就像是灵魂,当一个人死去衣服还在那里,后来的人还会穿着,但是在衣服经常被穿之后,它也会有一天而朽坏,“灵魂经不住多次投生的折磨,终于不免在某次死亡时完全消灭。”
对于辛弥亚的观点,苏格拉底首先否定了灵魂和谐说,因为和谐必须要有成份来保证,必须听从成份的指挥,而且和谐意味着有其不和谐的部分,所以没有理由来说灵魂是和谐的,由此也否定了当竖琴被破坏之后和声不存在是对灵魂的否定。对于格贝的说法,苏格拉底认为,所有事物都必须研究原因,灵魂也同样,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被认为可以消灭又为什么会存在,进入到这个关于原因的讨论,苏格拉底说到了曾经看到了阿那克萨戈拉一本关于“心灵”的书,书中认为万物都是心灵安排好的,心灵就是万物的原因,“我就很高兴地认为,我在阿那克萨戈拉身上找到了一位老师,他使我在事物的原因方面大大开窍;我想他会告诉我大地是扁的还是圆的,然后进而说明它的原因和必然性,告诉我最好者的本性,以及大地为什么这样最好;如果他说大地在中央,就会接着指出它在中央最好;如果把这些事情给我说清楚了,我就决心不再求问什么别的原因了。”这个安排最好的心灵作为原因,就是对本体的研究,就是对存在的探寻,在苏格拉底那里就是“是者”,“是者”是不能通过直观获得的,就像我们研究日蚀,如果直接用眼睛就会毁掉眼睛,所以对于存在必须用思想,用理性,“因此我认为必须求助于思想,在思想中考察‘是者’的真相。”
什么是存在?“我想如果某某事物是美的,它之所以美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分沾了美本身;别的事情也都是这样。”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表达了型相说,也就是型相二分说:如果我们说事物是美的,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它“分沾”了美本身,“—切美物之所以成为美的,是由于‘美’。”美就是美本身,就是美的理念,而美的事物就是分有和摹仿了美的理念,“有各式各样的‘型’存在着,分沾这些‘型’的其他事物从各自分沾的‘型’得到自己的名称。”在对灵魂进行阐述的时候,苏格拉底说到了灵魂的转世,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灵魂在这里就是能从相反事物中产生的事物,也就是型,但是在这里的灵魂则是灵魂本身,是理念,是相,所以苏格拉底说:“一个相反者绝不能是它自己的反面。”就举例说到了数的型和相,“五不会容纳偶数的‘相’,五的两倍十也不会容纳奇数的‘相’。两倍有它自己的反面,同时也不会容纳奇数的‘相’;一又二分之一和其他带分数,以及三分之一和其他简单分数,也不会容纳整数的‘相’。”神是“型”本身,生命是“型本身”,灵魂也一样,既然灵魂不容纳它的反面,那么它就是不死的,“确确实实灵魂是不死的、不可消失的,我们的灵魂会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某处。”
通过在形式逻辑、概念和相中阐述了灵魂不死,苏格拉底再次回到对灵魂的态度上,因为灵魂不死,因为灵魂是明智,因为哲学家就是净化灵魂,所以“我们就必须关怀它”,关怀它的今生,也关怀它的全部世界,“—个人应当为自己的灵魂打气,在生活中拒绝肉体的快乐和奢华,以为这是身外物,对自己有害无利,而一心追求知识的快乐,不用外在的饰物打扮自己的灵魂,只用它自己固有的东西来装点它,如明智、公正、勇敢、自由、真实之类,等待着离开今生前往另一世界,准备在命运召见时就去。”所以面对死亡要快乐,这就是“赴死”,“我们还欠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快乐的表现,于是裴洞说:“在我们所认识的当时人中间,他是最善良、最明智、最公正的人。”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