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21《最后的故事》:完成感叹号并离开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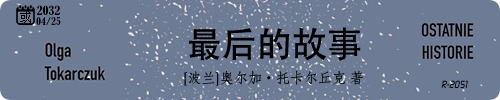
“你知道魔法是什么吗?”他问她,然后继续往下说,根本不在乎她已经要走了,“给你所看到的事物命名。强迫一个人说出他眼前事物的名字。事实就是这样产生的。每个人都喜欢坚持现实的某一单一版本,即使那个版本是错误的。”
——《第三部 魔术师》
箱子上盖着幕布,男孩和魔术师基什的助手各自拉着吗,幕布的一端,然后基什消失在幕布后面,接着幕布掉落下来,纸箱的一端伸出了脑袋,另一端则露出基什的脚,男孩接过助手递给他那把闪闪发亮的锯子,然后把纸箱切成两半,伴随着做了鬼脸的基什的尖叫,他僵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刀刃已经掉到了地上,一滴滴红色的鲜血汇流成一条溪流,流到了沙地上。”
尖叫、僵住,以及流出来的鲜血,这一幕的发生就像死亡一样——对,是像死亡,是对于死亡的表演,当众人惊愕以及恐惧的时候,掌声响起,三个人鞠躬谢幕。这是一场演出,这是一个舞台,或者这就是一个魔术。当魔术制造的场景将人们推向死亡现场的时候,掌声和鞠躬的致谢又将这一切拉回到现实,“她松了口气,终于结束了。”推入死亡,又拉回现实,经历恐惧,又返回安全,这就是魔术制造的效果,而这样的效果在基什那里就是对于“错误”的命名:它强迫对事物进行命名,以为这一切就是这样发生的,所谓偏执,所谓自我欺骗,就是达到了魔术的境界。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是谁强迫对事物进行命名?又是谁把错误的人拉回到现实?
魔术的名称是“人体切割术”,基什的脑袋和双脚在纸箱的两边,它们就是被“切割”了,那把刀从指向中间切割下去,基什尖叫,基什僵住,基什死了,这更是“切割”的结果——它指向的就是死亡,所以对事物进行错误的命名在人体切割的魔术中就是对死亡的命名,按照男孩的说法,这是“世界上最狡猾的艺术”。但是当基什说出魔魔法的本质时,错误的命名其实并不是“死亡”,而是“身体”,是身体被切割,是身体流出了血,是身体在尖叫,当然是身体保持着僵住的姿势。身体被切割,被切割的身体以错误的方式被命名,它就是死亡。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魔术本质问题:基什和男孩在舞台上表演,他们的魔术是奉献给地下的观众看的,不管是基什和他的助手,还是男孩,都知道魔术的秘密,都知道“人体切割术”的操作技巧,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强迫对事物进行命名的,他们也不会坚持错误,只有那些观众会进入到这个错误的命名系统中,底下的女人即这个叫玛雅的母亲和其他观众一样在人体切割术的表演过程中强迫命名了事物,并完全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观众是一个观察者,如果对魔术的观察只是寻求一种效果的过程,但是在现实中,观察产生的错误就变成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观察自己?谁在看,又在看谁?”这个问题关涉的是主体和客体,客体成为了主体观察的对象,纳入到主体的世界里,那么作为观察所有起点的主体是谁?一个“我”?观察者是我还是被观察的人是我?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双重的、复数的人,就是不合逻辑、自相矛盾的存在?当我观察我,观察我的身体,身体是不是在这种观察中完成了“切割”?在这里,对于观察的主体的疑问便开始了:“我”和“我”,这样的关系是不确定的、神秘的,甚至是随时可以被解构的;当“我”转向外部的“你”时,内心的独白就变成了一种对话,对话需要用语言来传递,语言你来我往,但是语言往往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它从人体切割术变成了理解切割术,“我们是不同的,但我们不知道彼此之间有多少不同。”不仅仅是不同,甚至当“我”通过语言的对话依赖于“你”的时候,切割术造成了痛苦;也许避免这一切的最好办法是把“你”换成“他”,“我”而和“他”不会靠得太近,关系会变得稳妥,但是当我面对的是“他”,那么这个他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物,甚至就是“它”,“把它像球一样从一只手扔到另一只手,对它施法,创造它,让它消失。”
我对“我”,变成对“你”,又变成对“他”,这是逐渐从自我到对话者再到物体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无疑就是一种魔法,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强迫命名的事物,因为随时对它施法、创造并让它消失就是一种命名,而且是一种错误——在底下的观众看见了魔术中的他,看见了被切割的人体,因为对他这一人体进行了物化的命名,所以会认为他死了,所以产生了恐惧。这就是“魔术师”带来的启示,而在这第三部的《魔术师》里,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将这个启示变成了和身体切割、他者物化、最后的死亡有关的隐喻:玛雅带着儿子来到了南中国旅行,在海边游玩,潜入海中,看别人做爱,遇见欧洲女人,或者观看人体切割术,这一趟旅行玛雅都是观察者,那个“我”,但是在她面前的是“我”?是“你”还是“他”?“她的身体总是冰冷。所以她从不讨厌炎热的天气。”这是对身体的观察,身体冰冷所以来到中国南海,但是在这里,她又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那就是食欲全无,“炎热的天气把人体机能都改变了。”身体的不适之外,是对于做爱的观察,露台上的男女在做爱,“他们缓慢地动着,懒洋洋地,像两株海葵,又像海草泛起的涟漪。”玛雅看见他们,然后就看见了另一个男人,“一个如此珍贵以至于让她无法呼吸的男人,一个没有名字的男人”,但也是关涉灾难性事件的名字,从身体出发,从观察出发,既是让她无法呼吸,也让她回忆了灾难性事件;还有魔术师基什,病了的他留在这座岛上,玛雅总是会观察他,她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捕食者”;岛上的每个人,新来的人,旅行者、流浪者都被她观察,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她看来,这些人都保持着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所以他们没有臣服于这里。”但是在遭遇了恼人的麻烦之后,“眼前出现了一个空洞,一个没有名字、没有边界的模糊的国家。”
| 编号:C39·2241205·2213 |
她在观察自己,观察他人,观察世界,是不是他们都成了“他”?是不是她进行了错误的命名?是不是她完成了“人体切割术”?而每一种观察其实都指向了死亡,家园被遗忘是死亡,语言成为深不见底的井 是死亡,人体切割术中流出的血是死亡,还有多年前她的母亲将她的外祖母带回家后外祖母的死亡,“她把自己置于死亡之中,仿佛坐在横贯大陆的火车包厢里,舒适安宁。”即使最后她带着男孩离开这里,她在公共汽车前灯照到的地方看到了寂静的剧场,“仿佛所有人都在期待一个演员会从这黑暗中出现。”舞台还在,演员还在,魔术还在,切割术还在,错误的命名还在,当然,死亡也还在。第三部,也是小说的最后一部,托卡尔丘克是不是在这“最后的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关于死亡的魔术?而实际上,《最后的故事》就是关于人生最后上演的死亡,但是当玛雅“把自己置于死亡之中”的时候,这样的死亡是不是也成为了关于自我他者化以及他者物化的错误命名?
玛雅想起了死亡之前母亲带着外祖母回家的情形,这似乎勾连起了《最后的故事》中的这三个故事,玛雅、母亲和外祖母组成了三代女性,《魔术师》中的玛雅是最后的一代,而往上则是《净土》中的伊达,她就是玛雅的母亲,“这时,恐惧攫住了她,因为她突然想起来,她把玛雅,她的小女儿留在了屋前。”而从玛雅到伊达,也是一个关于“人体切割术”的故事,“玛雅在三十三年前来到这世上。她的出生伴随着母亲的阵痛。”这样的人体切割术是分娩,是降生,当完成女儿玛雅的出生,这种身体的阵痛是不是变成着伊达的死亡?伊达在父母去世之后卖掉了乡下的房子,而当她在若干年后准备回老家的时候,就遭遇了车祸,在大雪天,车子滑出了道路,她的头撞到了方向盘,然后便听到了脑袋里令人难受的声音,当她醒来发现自己掉进沟里受伤了,于是迷路的她找到了乡间小屋,像一个被遗忘的度假别墅。
发生车祸而昏迷,醒来而迷路,伊达的身体遭受了创伤,实际上在这里人体切割术所表现的就是失忆,暂时失忆,那么这种失忆是不是变成了对于死亡的错误命名?在开车的时候伊达就想到了“冰冷的死人的呼吸”,这是一个矛盾的修辞法,“一个词推翻另一个词,凑在一起却又构成了某种意义。”就像人体切割术。来到乡间别墅,她遇到了善良的老妇人奥尔加和她的丈夫斯特凡,而老人似乎也记不起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比如战争时期的事,或者我们如何来到了这里,我甚至记得刚解放的时候面包的价钱。”当伊达感觉他们就像自己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时,记忆以另一种仿佛出现,它带着重复的痕迹,而重复也是伊达工作的核心,身为“欧洲之心”的旅行社导游的她,就是不断重复线路,不断重复景点;重复在她看来,也是宗教的核心,“不是重生,不是解放,而是时间的倒退,是让人们不断反思,重复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哪怕是些难以理解的胡言乱语。”
但是重复并不是无意义的,工作是重复,宗教是重复,死亡在重复,重复是完成新的命名,重复更是寻找自己的记忆:她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名字,知道了自己住的地方,知道了此行的目的,而确认自己活着并且进入记忆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回身体,八岁时就迷上了魔术戏法的她完成了关于自己的“人体切割术”:她触摸自己的胸部,感觉自己的心跳,她想起“在血淋淋的肉的褶皱中”的子宫,她观察自己由神秘的凹凸、层层叠叠的组织、血淋淋的褶皱组成的身体……这是伊达对身体的第一次确认,在这个意义上她才发现自己曾经对身体一无所知,“身体对自己一无所知,只有通过给自己做检查,才能知道自己的机体是如何工作的。”从身体回想起出生的女儿玛雅,想到共同生活了十八年的丈夫尼科林,想到了母亲的死亡,但更想到了只有冬天的弗罗茨瓦夫,想到了德国人留下的学校,想到了学校外墙留下的弹坑,所以,身体被切割成现在和过去,切割成记忆和现实,切割成活着和死去——身体不断被切割,就是不断刻下记忆的过程:
身体是有记忆的。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记住了我们的奔跑、漫步和追踪,记住了喜悦、玩笑和跳跃。身体记住了一些岁月、风雨、雷电、逃离、追逐、来访、道别。这样的记忆就像浓缩食品——当我们给它加一点液体类的物质,生命就会重新绽放,焕发色彩,再次开始。有记忆的是身体,而非头脑。身体随着记忆一同死亡。
当伊达确认了身体,恢复了记忆,是活着还是死去了?她终于找到了她的车,她终于驶出了弯道,她终于出发去老房子,但是以及又让她回到了车祸现场,“她把头靠在方向盘上,把脸颊放在上面,然后如释重负地闭上眼睛。”记忆在重复,身体在重复,或者说车祸在重复?她迷路、醒来、在别墅里遇见老人,以及离开,难道都没有发生?难道只是一场梦?那场车祸发生的时候她是不是就这样“如释重负地闭上眼睛”?也许身体没有回来,也许记忆只是虚构,托卡尔丘克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另一个“人体切割术”的魔术,在死去而活着的状态中,在失去记忆而回来的经历中,对于过去,对于历史,有了一次真正的观察。而实际上,这或者就是托卡尔丘克讲述“最后的故事”真正的用意,在第二部《帕尔卡》中这句话就成为了托卡尔丘克的观察目的论,“即使我们不去评论历史,我们承认历史早已模糊不清,无法将其放置于一个共同的叙述体系之中,那我们又该如何对待现实呢?它同样被放置于滤镜之后。我们看着同样的事物,看到的却是不同的东西。”
从第三部的玛雅,到第一部的伊达,再到第二部的“我”,孙女、女儿和“我”构成了女性的三代,而这似乎也是第二部标题所揭示的主题,“帕尔卡”指的就是命运三女神,其中的克洛托是“命运的纺线者”,她负责将生命线从她的卷线杆缠到纺锤上;拉刻西斯是“命运的决策者”,她负责用她的杆子丈量丝线;而阿特罗波斯则是“命运的终结者”,她是剪断生命线的人,用她那“令人痛恨的剪子”决定了人的死亡。当然三位女神并不是在三部曲中可以对位,托尔卡丘克在这里所讲述的是女性的命运,被死亡主宰的女性命运,讲述“最后的故事”的女性命运——而这里的“我”却恰恰是“最早的故事”的讲述者,无论是最早的故事还是最后的故事,关于女性的命运所组成的就是历史,就是历史延伸的现实,就是要将历史和现实除去滤镜之后真实命运。第一句:“我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床挪到了阳光房。”最早的故事是第一人称的“我”,那么这个“我”能否逃离自我的他者化和他者的物化这个人生魔术?
在“我”的身边上演的就是死亡:比自己大十五岁的丈夫佩德罗建造了阳光房,却在山坡的阴面,“佩特罗在礼拜日的晚上去世了。”儿子在遥远的旅行中死了,“我的第一个孩子死在了火车上。那是一次冬日里长达两周的远途旅行。那个孩子就是娃娃。”佩德罗原先是和斯塔德尼茨卡本是一对儿,他和她都是老师,但是后来俄国人把她带走了,“她像很多其他人一样,死了。”其他人是去了美国没有回来的人,是从战场上回来被射杀的人,是不知道身份而死去的人,以及被流放、被驱逐的人,“还有一些人,经历种种苦难,现在噤声坐在那里,紧紧地贴着地面,充满警惕。”还有没出生的孩子死了,那次尤里·利伯曼中尉压在“我的身上”,“他的身体快速有力,充满自信。”后来我怀孕了,于是忍着耻辱去做了流产,这个孩子永远不会出生了,他死在我的屈辱里;利伯曼也死了,我看到了他那只指甲变形的大脚趾,“脚趾承载着这个有着两副面孔的男人的所有力量,那力量变得怪诞而虚浮。这脚趾让我感到羞耻。”
死亡在发生,死亡没有停止地发生,死亡通过身体发生,而没有死的“我”呢?是不是也在身体切割术中看见了死亡?死亡是历史,死亡是政治,“政治是满足这种欲望的工具,这种欲望是整个世代基因中固有的。这很有可能。曾经主宰我们的是命运,现在是基因。”而现在当命运像基因一样无法更改,当然无法再忘掉苦难的记忆,再无法剪去错误和愚蠢,再无法像树枝一样会进入新一年的清白,“毕竟我们知道一接下来的某一个冬天会将我们杀死。”所以佩德罗建造了避世的阳光房,他在那里体会着自己的死亡;于是,在佩德罗死后我躺在他的身边,“我得好好看顾他,别让他还满脸胡茬。”所以我在雪地上踩出脚印,“我走在雪地里,因年老而疯狂,我看到了身后那串清晰、简单的脚印。”最重要的是,我在教堂的弥散中听到了自己唱出的歌声,“那是我,我拥有圣帕拉斯凯维亚·皮亚特尼卡的声音。”于是我成了圣帕拉斯凯维亚·皮亚特尼卡,一个殉道者——不是“我”将自己他者化了,而是以命名的方式完成殉道,这不是错误,这是对苦难、历史告别的重生,“就这样,我们一部分一部分地迷失了自己。然而,我想,走到尽头意味着把所有的东西集中在一起,把生活中的一个个时刻合成一个小小的集合。这不是失去,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失而复得。”
从玛雅的人体切割术,到伊达的身体记忆学,再到皮亚特尼卡的殉道者的自我命名,三代人讲述“最后的故事”回到了历史的起点,回到了“最早的故事”,它以一个感叹号而终结,“现在,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感叹号并离开地面,接着再向前滑行一小段,在雪地里留下一个点。”托卡尔丘克将小标题的字母合成了波兰语“PETRO UMARL!”,这就是“佩特罗死了!”最后的感叹号才是“最后的故事”,去除自我的他者化,去除身体的切割术,去除基因对命运的主宰,“我会在外面等着他们,就在我在雪地里踩出的最后一个黑点的地方。我会成为这句话的一部分。我会成为一个点。”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