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08 听不见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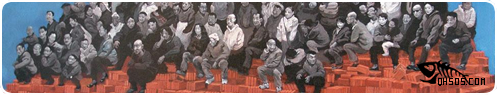
属于正装的西装领带上身,又脱下,这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这3个小时是一场纪念记者节的大会时间,是隆重表彰和嘉奖的时间,是领导提出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要求的时间,这3个小时的开始和结束,用一套服装的轮换作为标志,温度尚未遍及全身,却已经成为过去的风景,这像是对我这些年来作为记者归属的尴尬,似乎在一个纪念日,才想到我可能是被认可的记者或者新闻工作者,才会想到它应该多么的光荣和有力,才会想到我的14年的工作都可能是在发出另外一个声音。
每年都会隆重,每年都是喜庆,每年也有荣誉,但细细想来,“记者”这个职业其实一直距离我很遥远,从14年前偶然选择开始,都可能是一次次的尴尬,激情无非是年轻时的原始冲动,但是新闻不在场的无奈和记者身份的缺失使之完全沦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所以“不做记者好多年”的现实让我觉得节日更多是曾经的缅怀,而剩下的,便是一个最基本的困境:中国记者,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声音?
今天发言的主题是《记者的责任与使命》,我说记者是工作,是事业,但其实应该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是对目前现实的无奈,是对新闻体制的无奈,“责任与使命”是加在记者身上的道德属性,但是在“党管媒体”的时代,记者遭遇的不是道德上的自律还是他律,实在是法律意义上的基本权力问题。现实中让人不安的问题是:不是笔头对准了拳头,而是拳头对准了笔头,据中国记协统计,1998年他们设立新闻工作者维权委员会以来,受理的关于记者受害的投诉就有400多起,其中包括很多非法拘禁和殴打记者等恶性案件。虽然说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一些法律意识淡薄而特权思想严重的人专横跋扈是直接原因,但从根本上讲,却是法律的缺席。新闻采访权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司法权力,它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公众知情权是建立在新闻采访权基础上的,新闻采访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权需要从法律上加以特别的明确保护。但现有法律对新闻执业的保护非常弱,因为适用宪法原则保护新闻采访权,在法律实践中还有一定障碍。记者行使新闻采访权时,由于没有明确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采访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方的好恶。尤其行使舆论监督的记者,必然激起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痛恨,轻则设置重重关卡阻碍采访,重则拳脚相加。
所以,在中国的悲哀现实是,记者不是英雄,他只是一名职业操守,甚至法律缺失面前,他宁可隐藏自己的声音,在“喉舌论”、“耳目论”、“火炬论”这些冠冕堂皇的属性下面,是记者的集体失声,记者不在现场,在文件和指示中,记者不是无限接近真相,而是尽可能远离真相,是“正确的舆论导向”、“重大主题策划和报道”、“主旋律”这些词汇组合而成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个全民记者时代,这样的境况更显得尴尬。从“周久耕事件”到“烟草局长日记”,从“富二代飙车撞人案”到“李刚门”,从“躲猫猫”到“楼脆脆”,从“毒奶粉”到“地沟油”,从“唐福珍事件”到各类拆迁案件,媒体的监督一直像是孤胆英雄,而且自上而下,对贪官和丑闻的揭露,似乎网络的作用更强,似乎体制外的声音更大,而媒体记者应有的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和监督权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2008年记者节,《南方都市报》发表过一篇纪念中国记者节的社论,其中说到:
在这所有的声音中,有一种声音至关重要,它无所不在,无微不至,无可替代,无处遁形,那就是媒体的声音……它是声音的通道,也是声音的源头,它是声音中的声音,哭泣中的哭泣,欢笑中的欢笑,愤怒中的愤怒,赞美中的赞美。
在缺少对声音包容,尊重,倾听,理解和思考的时代,媒体的失声大于声音的传递,媒体的喧嚣大于孤独,我们其实连自己的声音也听不到,我们只是用一身的正装掩盖我们的贫穷,用三小时的节庆来弥补我们的羸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7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