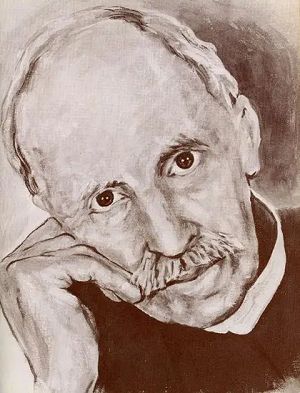2022-11-08《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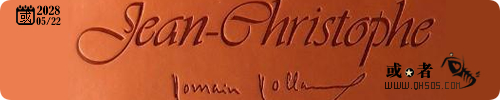
这些话给了克利斯朵夫很大的刺激,哦,原来有过一个孩子,跟他一样也是母亲的儿子,取着同样的名字,差不多和他没有分别,可是已经死了!
——《卷一·黎明》
母亲说到那件衣服,说到那个故事,说到那个早已存在却死去的哥哥,竟然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有着同样的名字,甚至自己和未曾见面的哥哥同名,就是一种生命的替代。这是一个秘密,一个生命存在的秘密,也是生命逝去的秘密,它降临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带来的触动甚至构成了他一生最大的符码:这是一个被命名的故事,同样的名字,差不多和他没有分别,对于母亲来说,“儿子”就是他们共同的属性,也正因此,用生者的他代替了死去的哥哥,不仅是名字,还有衣服;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母亲说哥哥在天上,在为大家祈祷,而实际上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来说,那就是一种死亡,无可逃避的死亡,带来痛苦的死亡,“从这时起,死亡的念头把他童年的生活给毒害了。”这当然还是一个关于上帝的故事,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而言,和祖父去了教堂并不代表他真正信仰上帝,他只是怀着好奇心知道了上帝,知道了宗教,但是离信仰还很远,甚至在知道死去才去天上,死后的灵魂才升到上帝面前,他对上帝反而有了某种不解,“他对于这个旅行非但不受吸引,倒反害怕。”
关于命名,关于死亡,关于上帝,对于幼小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来说,另一个已经存在的“克利斯朵夫”成为了他一生的出发点,而这些从母亲口中说出的词汇,在约翰·克利斯朵夫有限地思考中,进入心灵世界的则从命名变成了自我,从死亡变成了生命,从上帝变成了信仰,一切都变成了在灵魂意义上思索人生的价值。这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真正起点,正是从这个起点出发,他在黎明时醒来,在清晨发现万物之美,在少年开始品尝痛苦,在苦难中反抗,在音乐中思考民族精神和人类文明,并最终在“复旦”中迎来曙光:“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一种死亡的降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肉体生命的终结,却在人类的心灵史上留下了最精彩的华章:“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且休息吧!所有的心只是一颗心。日与夜交融为一,堆着微笑。和谐是爱与恨结合起来的庄严的配偶,我将讴歌那个掌管爱与恨的神明。颂赞生命!颂赞死亡!”
也是幼小的克利斯朵夫听到了“自己”的存在和死亡,他从“一刻浓似一刻的令人窒息的夜里”,闪现出照耀一生的光明,那就是音乐,神妙的音乐。第一卷《黎明》,罗曼·罗兰引用了《神曲·炼狱》中的话打开了酣睡之后的灵魂:“在平旦之前的黎明时分,当你的灵魂在身内酣睡的时间……”而灵魂的醒来首先是肉体的降生,一个孩子,一个醒来的孩子,睁着惊慌的眼睛,看到了灯光下的无边黑暗,看到了深不可测的阴影,他握着拳头,扭动身子,拧着眉头,似乎在感受着痛苦,之后则是断断续续的悲啼,“仿佛这一堆无意识的尚未成形的肉,对他命中注定的痛苦的生涯已经有了预感。”痛苦构成了一个肉体最初的感受,悲啼则是他做出反应的行为,也正是在痛苦和悲啼中,他的生命中出现了音乐:这是父子相传的音乐世家,从科隆到曼海姆,所有的音乐家都知道他们;当孩子被巨大的痛苦笼罩的时候,母亲用温软的手摸着他,在半梦半醒中听到了母亲哼出的曲子,它是伟大的母性之声,;而黑夜中又传来圣·马丁寺的钟声,“严肃迟缓的音调,在雨天潮润的空气中进行,有如踏在苔藓上的脚步。”婴儿的嚎哭停下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他开心的笑声;而等到长大了一些,祖父带着他去了教堂,听到了大风琴响起的声音,那像是瀑布的声音,在他的世界里变成了一种发光的存在,之后他溜出屋子在田野中奔跑,向灌木林行李,看到绿树向他点头,便是寻找到了这种音乐般的光泽。
肉体降生,灵魂中却涌入了不同的声响,它们变成了音乐,启蒙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活着多有意思”便是对于生命最初级的礼赞。之后祖父和父亲对他的音乐教育,是走向音乐的第二步,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音乐教育中得到的启发和启蒙依然是对于生命的唤醒,但是教育也带来了怒吼,带来了戒尺,带来了抗拒,“爸爸,我不愿意再弹了”也成为他喊出的第一声反抗。灵魂中音乐如光一样降临,音乐教育中的惩罚,似乎将克利斯朵夫带上了音乐的不同道路,而实际上在克里斯多夫生命意识里,不同的道路又走在了一起:在看了法朗梭阿·玛丽·哈斯莱指挥的乐队演出之后,只有六岁的他开始决心要写音乐了,而舅舅高脱弗烈特则告诉他,要成为音乐家就是要成为“为家、为国、为艺术争光”的人,而这就是对克利斯朵夫一生重要的启迪,它从单纯的音乐喜好变成了音乐事业,更是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但是六岁对于克利斯朵夫来说,音乐的启蒙对于人生的意义阐述还为时过早,只有经历了人生的各种苦痛和困境,只有体验了生命的艰辛和不屈,只有品尝了失败的苦涩和成功的喜悦,那一部音乐作品才会丰满起来,才会厚实起来,才会深刻起来。在知道同名的哥哥的死亡之后,十一岁的克利斯朵夫再次目睹了死亡,祖父约翰·米希尔离开了人世,舅舅说:“孩子,他和上帝在一起。”这一种死亡对于克利斯朵夫的感受和未曾江面哥哥的死亡不同,哥哥的死亡只是一种逝去的概念,而祖父的死亡则是消逝的现实,“一个人对于死真要亲眼目睹之后,才会明白自己原来一无所知,既不知所谓死,亦不知所谓生。一切都突然动摇了;理智也毫无用处。”死亡之后则是家庭贫穷的到来,酗酒的父亲用掉了家里很多的前,于是只有十四岁的克利斯朵夫在乐队里赚钱、开设课程教课赚钱,他的成为了“一家之主”。这是人生走向社会的一个标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了朋友,奥多是他第一个真正的朋友,甚至在同性的亲热中他第一次体验到了爱情,直到奥多进了大学两个人分来;在教克里赫太太的女儿弥娜弹琴时,他又体会到了天真无邪的温情,对于女性他也萌生了爱情,甚至在母女之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上了谁——或者两个都爱;友情和所谓的爱情,对于克利斯朵夫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它们让他发现了“万物之美”,这是春天的笑容,这是天空之中的光华,这是大气之中的柔情;在这万物之美的发现中,他写出了一阕铜箫与弦乐器的《五重奏》,这是他真正用心写作的第一部作品。
| 编号:C38·2221004·1877 |
第一次的友情,第一次爱的感觉,第一次发现万物之美,第一部真正的作品,对于年少的克利斯朵夫来说,是生命不断丰富的象征,是人生获得意义的体现。但是打击也接踵而至,弥娜的信里是拒绝的口气,克里赫太太认为门第有差距,于是克利斯朵夫产生了仇恨,而仇恨最后变成了生命的怀疑,“他不是想毁灭自己的生命,毫无血气的逃避他的痛苦吗?以死来鄙薄自己,出卖自己,否定自己的信仰,是世界上最大的刑罚,最大的罪过:跟这个罪过相比,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欺骗,还不等于小孩子的悲伤?”这痛苦是理想被破灭的象征,这罪罚是生命接受洗礼的开始,他仿佛听见了上帝的声音:“痛苦罢!死罢!可是别忘了你的使命是做个人。——你就得做个人。”而实际上上帝的声音是克利斯朵夫内心的声音,“你就得做个人”成为一种箴言,它从理想的英雄主义位置上跌落下来,他也需要从个人主义的人的位置上站立起来——而“你就得做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要通过他人认识自己。
他在搬家之后认识了房东于莱老头,认识了于莱的女儿阿玛丽亚,认识了洛莎,关于生活,关于上帝,关于爱情,他不断在认识,不断在体悟,也不断受到打击,个人主义的克利斯朵夫总是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他感觉在命运的拨弄中坠入了虚无的境界,仿佛一张弓被暴烈的手快拉断了,但是这也成为克利斯朵夫蜕变的一个开始,“他只看见童年时代那颗衰败憔悴的灵魂掉下来,可想不到正在蜕化出一颗新的,更年轻,更强征的灵魂。”这种蜕变来自于萨皮纳·弗洛哀列克太太和女儿带给他的诱惑和死亡,来自于洛莎带给他的爱和噩梦,来自阿达带给他的庸俗和嫉妒,于是他保持着自己的年轻、纯洁和高傲,以及渐渐萌生出的反抗,而这一切又汇合成如舅舅高脱弗烈特所说的信仰:抛弃愚蠢的理论,抛弃对人有害的道德,抛弃逼迫人生的暴力,“对每一天都得抱着虔诚的态度。得爱它,尊敬它,尤其不能污辱它,妨害它的发荣滋长。”而舅舅对他所说的信仰,是自我的信仰,对于克利斯朵夫来说,一方面变成了他自己总结的“竭尽所能”,而另一方面又变成了个人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对于克利斯朵夫来说,这两者有时候又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人生态度。
从黎明到清晨到少年,罗曼·罗兰构筑了克利斯朵夫的人生第一章,在这序章中,克利斯朵夫强烈的生命意识表现为感觉和感官的觉醒,这是对他小天地的突围,也意味着在考验中受到了创伤,而从第二章开始,罗曼·罗兰以“反抗”和“节场”书写克利斯朵夫的转变,这是另一次突围,也是另一次的考验:从混沌、暧昧、矛盾和骚乱的青春中突围,在高扬意志和天才中接受考验,在“创造才是欢乐”中探寻不朽的动力,在“创造消灭死”中寻找永生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曼·罗兰赋予了克利斯朵夫更多象征意义,他以个体的成长映射民族的命运,以一种人类意识构筑起关于成长的母题,“我们每一缕的思想,只代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时期。倘使活着不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误,克服我们的偏见,扩大我们的思想与心胸,那末活着有什么用?”
这一个新阶段,克利斯朵夫看到了德国人的虚伪,德国艺术的谎言,“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无聊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婆婆妈妈的,沾沾自喜的,把他们的心灵尽量暴露出来。”所以他从德国音乐到德国艺术再到人类的思想,都认为是没有岩石的沙土,都是不成型的黏土,都是没有思想的存在,“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它的虚伪。人类的食粮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但是当克利斯朵夫攻击这一切,他却发现演出时没有公爵在场,剧院里三分之一的位置是空的,当他设立了足够多的敌人,他也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从认识法国戏班子开始,克利斯朵夫的目光开始转向另一边,艺术之都的巴黎带给他另一种疑惑,终于他骗过了母亲,踏上了去往法国之路:这是一次逃离,这是一种自由,在克利斯朵夫强烈的非此即彼思想中,他告别了过去的一切,弥娜,萨皮纳,阿达,祖父,高脱弗烈特舅舅,苏兹老人,他也迎来了被虚构的法国,“噢,巴黎!巴黎!救救我罢!救救找罢!救救我的思想!”
从德国到法国,从虚伪到自由,克利斯朵夫构筑了属于自我的心灵地图,但是这样的“旅程”到底意味着什么?罗曼·罗兰第一次和克利斯朵夫进行了“对话”:他问克利斯朵夫:“你批评的事太多了。你惹恼了你的敌人,打搅了你的朋友。一个体面人家出了点不大光鲜的事,不去提它不是更雅吗?”而克利斯朵夫则回答:“有什么办法?我根本不懂什么雅不雅。”他是高傲的,是决绝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这就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极致表达,对于去往法国的目的也隐含着个人式的英雄主义,“我急于要给人看到真正的法兰西,被压迫的法兰西,深深的埋在底下的法兰西:——犹太人,基督徒,还有不论抱着什么信仰不论属于什么血统的自由灵魂。”所以对于克利斯朵夫来说,接触法兰西就是为了推倒它牢狱的墙壁,从封锁大门的守卫中间打出一条路,对此,罗曼·罗兰再问:“斗争,哪怕是为了行善的斗争,总是伤害人的。你自以为能使那些美丽的偶像——艺术,人类一得到的好处,是不是抵得上—个活人所受的痛苦呢?”克利斯朵夫更是这样回答:“要是你这样想,那末你把艺术放弃吧,把我也放弃吧。”
|
| 罗曼·罗兰:创造是消灭死 |
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罗曼·罗兰将自己拉入小说中,成为克利斯朵夫性格的提问者,他的这唯一一次“访问”对克利斯朵夫的性格,实际上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既是见证者也是塑造者,或者说,克利斯朵夫信奉创造的理念,罗兰·罗曼更是在创造克利斯朵夫中创造,所以他们形成的是一种影子关系,而克利斯朵夫问作者的是:“咱们两个究竟谁是谁的影子?”影子和影子不必分开,就像性格和矛盾不必说出谁对谁错,正是这种复杂性造就了克利斯朵夫,也正是这种矛盾体让罗曼·罗兰为这个人类命运的特殊符号书写了人生的乐章。
法国之行对于克利斯朵夫一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或者正是在这里,他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逐渐闪出它固有的悲剧性,甚至成为了一种在毁灭中创造,在死亡后重生的悲剧主义。“一切是有秩序中的无秩序。”这是克利斯朵夫踏上法国土地的感受,那些下流的嘴脸、形迹可疑的光棍、涂脂抹粉而气味难闻的娟妓让他害怕,他手摸着母亲的那本破旧《圣经》,这是秩序中的无序,这越是无序中的有序。从巴黎只认识的两个人开始,克利斯朵夫逐步走近法国,走近法国艺术,走进法国文学,走近法国社会,也走近了法国的女人。法国是一个参照系,克利斯朵夫不断吸收和批判法国存在的一切,从而变成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他起初认为法国的音乐没有情操,没有性格,没有生命,所以他希望革命,“他们始终需要一个异族的主宰,要一个格鲁克或是一个拿破仑才能使他们的大革命有点儿结果。”进入法国文艺界,他对高恩说,“艺术是驯服了的生命,是生命的帝王。”他认为艺术不应属于那些以畸形怪状来博取荣名的戏子,不应是享受是色欲是虚幻的人道主义,“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发扬生命的。”
克利斯朵夫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为享乐而享乐的感官主义,他要用生命来统摄一切,并让生命在作品中焕发光彩,从那本破旧的《圣经》他获得了灵感,以大卫的故事为原型他创作了交响诗,在他看来,希伯来民族史诗中有一股精神的力量,那就是生命力,
“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时分把他被巴黎烟熏尘污的灵魂洗涤一番。”但是克利斯朵夫要推翻一切的巨大力量也带来了关于自我生命的矛盾,他患病了,他发热了,他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从哥哥的死,到祖父的死、父亲的死,以及身边朋友的死,再到因为疾病自己感受到死亡,具有不同的意义,也正是这一次不断强化的死亡意识,让克利斯朵夫的不羁的心开始走向温和:他看到了西杜妮站在他面前,如此诚朴,如此温柔,如此平静,过去的抨击,过去的战斗,仿佛涤荡了他内心的激情,现在他更渴望温暖、柔和和深沉,而这也成为罗曼·罗兰“影子文学”的一个注解:克利斯朵夫多自己说:“我真罪过。我不够慈悲。我缺少善意。我太严。——请大家原谅我罢。别以为我是你们的仇敌,你们这些被我攻击的人!我原意是为你们造福……可是我不能让你们做坏事……”而罗兰·罗兰则评论说:“疾病使克利斯朵夫心非常安静。它把他生命中最凡俗的部分剔净了。”
克利斯朵夫走向温暖、柔和和深沉的人生,并不代表他放弃了战斗,放弃了生命的荣光,他寻找着一生的爱,奥里维、安多纳德都给了他不同的感受,让他有了灵魂的交融感;他也发现了法兰西民族精神中的可贵之处,快乐、随和、无忧无虑的乐观中浸透的悲观气息;对于人类文明的拯救,克利斯朵夫渴望一种奋斗精神,“起来罢!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可以说克利斯朵夫的悲剧意识越来越明显,他认为生命就是一场悲剧,但是这不是预先被注定的悲剧,而是必须通过“应当生活”“往前冲罢”的战斗来体现它的悲剧性;对于音乐,他则希望变得更宽广、更富于人间性,“他要音乐成为和人类沟通的桥梁。唯有跟别人息息相通的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艺术。”爱与欲呢,一样要体现着生命的激情,要展现生命的悲剧性:不再是自私的情欲,而是让灵魂参与其中;而在社会层面,克利斯朵夫参加了工团组织,在这个他认为的弱者联盟里,克利斯朵夫最终用他的个人主义起来反抗……
奥利维死了,阿娜死了,唯一的朋友,爱着的人,纷纷离他而去,“这一夜,克利斯朵夫独自回到房里,想着自杀的念头。”他想用爬山、划船的运动让自己忘记,他住在孤独的农家开始躲避,想着死却又是在求着生,矛盾让克利斯朵夫喊出了这样的话:“噢!生命,噢!生命!我明白了……过去我在自己心中,在我的空虚而闭塞的灵魂中找你。我的灵魂破碎了;不料我的伤口等于一扇窗子,从那里透进了空气;我又能够呼吸了;噢,生命!我又把你找到了!……”对于克利斯朵夫的生命意识的压制和觉醒,罗曼·罗兰在最后一卷《复旦》的“初版序”中如此写到:“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我毫无隐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浑浑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消灭是一种死,它的意义是为了创造,他对音乐表达:“咱们都不作声,闭着眼睛,可是我从你眼里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光明,从你缄默的嘴里看到了笑容;我蹲在你的心头听着永恒的生命跳动。”而“影子文学”让罗曼·罗兰和克利斯朵夫站在一起:“我自己也和我过去的灵魂告别了;我把它当做空壳似的扔掉了。生命是连续不断的死亡与复活。克利斯朵夫,咱们一齐死了预备再生罢!”
在游离欧洲之后克利斯朵夫回到了巴黎,“一个新的秩序产生了。一代新人兴起来了,——爱行动甚于爱了解,爱占有甚于爱真理的一代。”他的爱情和生命相连着,葛拉齐亚带给他最后的爱情,她自己也在这种爱中走到了最后,“悲观主义的最后一些雾氛,苦修的心灵的灰暗之气,半明半暗的神秘的幻境,都被死亡的风吹开去。”欧洲爆发了战争,战争变成了国际性战争,屠杀就是对生命的戕害,克利斯朵夫再次感受到了人类灵魂的邪恶;而自己的生命也终于慢慢走向了终点,他向上帝诉说,也是为自己呼喊:“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为父的臂抱中歇一歇罢。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从感官的觉醒建立生命的基调,到过激中体现反抗精神,再到走向恬静和温和看到友谊和爱情的悲歌,最后在怀疑和破坏、狂飙和暴风雨之后看见了黎明的曙光,为新的战斗而再生,就必须经历死亡——一切又回到了生命、信仰、个体的那个原点。
约翰·克利斯朵夫变成了圣者克利斯朵夫,古教堂门前圣者克利斯朵夫像下的拉丁文铭文是:“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而圣者注解的死亡,在罗曼·罗兰的笔下是再生的开始,是未来的起点:渡河的圣者克利斯朵夫肩上扛着的事娇弱而沉重的孩子,圣克里斯多夫将他背到了对岸,他问:“孩子,你究竟是谁?”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7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