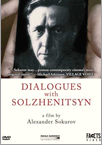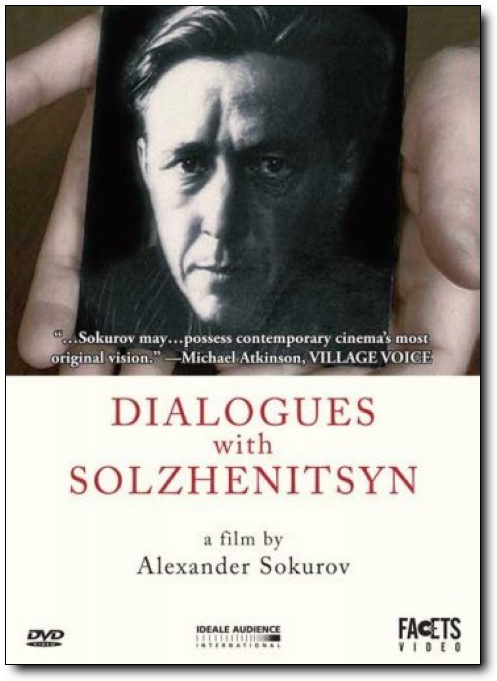2015-11-08 《对话索尔仁尼琴》:一个冗长的斧头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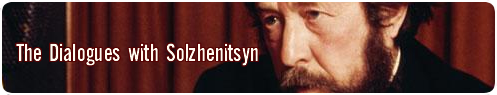
“对话”有时候不是零距离,却是永远的隔阂——索尔仁尼琴坐在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镜头前,而我坐在电影纪录片放映的电脑前,索尔仁尼琴看见的是1999年的俄罗斯风景,而我感受到的则是2015年的深秋。隔着不同的屏幕,隔着不同的国度,也隔着不同的时代,他几乎保持着唯一的姿势娓娓道来,而我也以同样的动作听说一个神话的故事——神话的国家,神话的文学,神话的作者,神话的一生。
对于索尔仁尼琴,在没有阅读他的小说之前,他的确是以一种“俄罗斯良心”的存在而在我的心中成为一个神话,被监禁、被审查、被驱逐,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变成我虚构索尔仁尼琴的神话素材,但是在阅读了《古拉格群岛》、《癌症楼》以及《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品之后,那种神性的光芒似乎就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被慢慢解构了,并非是他“持不同政见者”身份带来的争议,而是在这些作品中,看不到一个令人欣喜的作家,甚至读不出那种在大多数沉默中被折磨的“良心”,扁平的人物,愤怒的笔调,冗长的叙述,离我心中伟大的作家相差太远。似乎被压抑、被打击、被禁言了太久,索尔仁尼琴只有在文字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己,所以他几乎都以一种恢弘的方式把世界纳入到自己的创作体系里,而实际上,他不是在创作,他是在建造自己的宫殿,140万字的《古拉格群岛》让他成为“古拉格斗士”,但这只是他小试牛刀而已,他创作的《红轮》更是达到了近千万字,而这部称不上真正小说的作品是到目前为止世界文学中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反映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小说。
|
| 导演: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
 |
并不是不需要这种破坏力,而是在手握斧头的时候,甚至连索尔仁尼琴也不知道自己需要怎样一种理想世界。而坐在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镜头前,满脸胡子、目光锐利的索尔仁尼琴看起来像是一位先知,但是在那沧桑的表情背后他所寻找的俄罗斯精神似乎永远是一个未知。1994年他离开美国,回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从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乘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土地,最终回到了莫斯科。这样的回归是他某种夙愿的实现,因为他一直希望自己“最后死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甚至在美国的时候,就说过:“我们必须让孩子们成为俄罗斯人。”
|
|
| 《对话索尔仁尼琴》海报 |
当初他的作品被禁,他本人被驱逐,这是对于俄罗斯土地的一种无奈背离,但是对于他来说,美国的生活对他来说依然是流亡,在“定居”期间,他猛烈抨击西方价值,认为西方模式不适合俄罗斯,甚至可能将俄罗斯带入死胡同。所以实际上,西方给了他某种荣誉,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他似乎并非真正的认可,索尔仁尼琴所想要的是一种纯正的俄罗斯传统。但是怎样的精神属于俄罗斯?他一直认为苏联那一套布尔什维克属于西方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国际从来都是西方土壤上滋生的,甚至只适合西方。如果再向前,苏联之前的俄罗斯有着自己的民族传统吗?在纪录片里,索尔仁尼琴不接受一个地理名词,就是圣彼得堡,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名词就是彼得大帝取得一个“带有日耳曼语系特征的名字是西化媚外的象征”。所以他也否定向欧洲学习的彼得时代;再往前,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呢?在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信仰东正教,而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来自于罗马帝国的东正教依然是“西化”的产物。
他想回到俄罗斯传统,但是如果把所谓的“西方”的东西都剔除干净,索尔仁尼琴几乎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手拿斧头进行的斗争看起来只是一种形式,一种非理性的感性。实际上,俄罗斯精神、俄罗斯传统,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只是一种理念化的存在,甚至只是他民族沙文主义的一种外化,他拒绝西化,拒绝西方传统,拒绝西方价值,所以把一切变化政治秩序中的苏联、俄罗斯都看成是不纯正的,都认为异质的东西,这种异质损害着俄罗斯的纯洁的道德,并让俄罗斯失去了统领世界的荣誉。在电影里,索尔仁尼琴说到了基督教信仰,似乎这种对上帝的崇敬有着某种灵魂的救赎意义,在道德沦落的现实里,通过忏悔而被宽恕,“而那些没有宗教道德的人,至少应该对世间万物保持谦卑。每颗树都让我们感到敬畏。仅仅是树吗?鸟?动物?河流?山川?对万物谦卑,理解我们的局限,我们的渺小,即使你不信仰上帝。”而在他看来,那些心怀虔诚的俄罗斯农民,在最后死去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痛苦的,这是心怀上帝的崇敬,这是对自我生存的忏悔和宽恕。所以实际上,索尔仁尼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的资助,需要一种救赎的上帝,而这种上帝观又成为他神化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谈到哈萨克斯坦的时候,他说他们是愚蠢的民族主义,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最终会害了他们。在他来说,只有大俄罗斯主义才能改变这种愚蠢,所以他要求俄罗斯重新合并乌克兰与哈萨克斯坦,这种深入其骨髓的傲慢的民族沙文主义或许正是他理想的俄罗斯精神。所以在没有一统的时代里,他抨击苏联和俄罗斯的“寡头”政治体制,也批评西方的道德沦丧,似乎他的一生注定会在顽固、孤独和好战中,注定会手握斧头砍向每一个人。所以在他90岁冗长的一生里,他寻找自己的上帝,也把自己当成上帝,他俯视众人,也终究把自己陷在一个神化的世界里。
经历了监禁、驱逐和回归,看见了苏联的专制、倒台和俄罗斯的困难,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这一生已经足够丰富,而这丰富有时候却变成了冗长,90岁的人生经历对于他来说,依然无法真正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和归宿。冗长的作品,冗长的一生,而这场对话,也变成了冗长的纪录,四部分,190分钟,似乎只有索尔仁尼琴一个人坐在镜头前,谈文学,谈人生,谈宗教,谈政治,几乎没有相异的场景,几乎没有镜头的变化,只是片头时有关索尔仁尼琴的历史回顾,中间有过妻子娜塔莉亚的插入,但是从整体上看,单调、枯燥的长镜头,根本无需用影像来展现索尔仁尼琴的观念,或者也只有研究者在音容笑貌里看见一个片段而真实的索尔仁尼琴。
观点陈述
我们对发展上天赋予我们的天赋智慧怀有高度的责任。理性主义相信只应归罪于环境,这是很没道理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嘲笑过这点。我看到过,我已经经历过战争,监狱,癌症医院,每个地方的条件都是艰苦,粗陋,令人难以忍受的,然而人的行为却截然不同。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去抗争。……(如果)那些可以拉我一把,可以帮助我的人的缺席,不能开释我的作为。一个人必须明白,他的路由他自己决定,他必须深入了解自己的天赋能力。要彻底认识自己对人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现在是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自己,因为我年事已高,在步入老年时你会发现新的可能性和新的能力。其中之一就是你一次次地回顾一生,你会看清在匆匆流逝的时光中,那些你从未看清的东西。我们生命中大部分岁月都在忙碌中度过,忙碌让我们无暇思考生命中的那些微妙差异。而长寿让灵魂有了富余的空间来理解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总有对他人的行为作出判断的权利,因为我们低估了那些对自己的行为也没有真正理解的人不自知的程度。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这么做。
学习有不同的层次。有一种层次更“学习”,更深入,也更哲学化。你可能体验过也可能没有。有句谚语是:“知道越少,睡得越好”。还有另一句话:“学习增加不了智慧”。最开始,我很吃惊,怎么会呢?增加了那么多!在前线我们有一个政委,他经常反复说:“学习增加不了智慧。”我曾争辩说:“少校同志,这怎么可能呢。”在那之后许多年,我想:“这是对的。”有那种愚得彻底而学得很多的人,也有学得很少但是很聪明的人。他们懂得生命,心灵和生活的正确方式。和学习没关系。基本上,人类变得太过热衷进步了,从启蒙时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它推进,但事实上,人类的灵魂变得一片荒芜。技术,文明,给了我们一切,丰富的商品,现在又是互联网,信息的洪流使我们无法呼吸,灵魂变得空虚。灵魂空虚,死亡就是极其糟糕的,无处可去。道德感不是能通过知识获得的,它首先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然后才是教育。
艰难的岁月,我是怀着对上帝的信仰而长大的,而在学校这种信仰被扼杀。我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最后还是向这种做法屈服了,辩证唯物史观淹没了一切,而我丧失了我的信仰。这种事在我的学生时代是司空见惯的。在战前的5年里,我都是纯粹的无神论者。许多年之后,当我整理一些旧信件,一些早期在写作上的尝试的时候,我为我在那段时间的精神空虚而震惊。你明白吗?是震惊。我们总说能够我们想出结果。不,人单靠自己是想不出结果的。在那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当我重读我的那些旧日的文件时,我为自己精神的空虚而震惊。原因我很清楚:那是个世俗化的时期。就是如此。
如果你让一个男童,像毛克力(英国文豪吉卜林的诺贝尔获奖作品《丛林之书》男主角),即使只是在草丛中行走,他也可能产生出宗教意识。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会产生。在我的学生时代,和我的几个朋友,我们曾坐小木船在伏尔加河漂流,我们就那么坐木船下去,还都是些孩子,100%依赖天气情况,大风,骤雨,所有一切,我们毫无遮挡,什么也没有。每一天我们都变得更加迷信,不是上帝的信徒,只是可怕的迷信,害怕任何征兆,用错误的方式行事。所以,当然,人天生就能感受到超凡力量的存在,但宗教意识很明显是在后天成长中获得的,代代流传。我很好地从双亲那里继承了它。从我的母亲和我的阿姨那里,疼爱我的人。
基督教相信一切都是可救赎的,任何罪过,甚至任何罪孽,只要人还活着,他都能醒悟并悔悟。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可逆的,但是你无法改变任何事,你罪行的后果是无法消除的。它已经发生了。他没法做什么了,除了悲伤和悔改。还有,基督教非常看重灵魂的悔悟,无论它发生在何时,即使是在生命的尽头。这就是基督教。在我们身边,这种教化的转变变得罕见了,人们毫不怀疑的走上他人的错路,时代告诉它:“来吧,来吧,大家都这样做。”这个“大家都做”让灵魂完全僵化,人们判了自己的刑,彻底堕入地狱。……惩罚就是那些人再也无法悔改,迷失在洪流中,在这样的洪流中,他甚至不再是一个人。而理由就是:“大家都这么做”。这是最糟糕的想法。
在基督教的忏悔里,牧师,如果你告诉它关于过去的罪行,他会说:“你已经忏悔了,你被宽恕了。”错了。在死亡到来之前,无人会被宽恕。这非常重要,更高的权力永远是上帝的。而那些没有宗教道德的人,至少应该对世间万物保持谦卑。每颗树都让我们感到敬畏。仅仅是树吗?鸟?动物?河流?山川?对万物谦卑,理解我们的局限,我们的渺小,即使你不信仰上帝。
人们应该有勇气接受它(苦难),而且明白它是为了某种目的才出现的。揣摩它,以正确的方式接受它。他们把你关进监狱,首先,你觉得难以忍受,已经完蛋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又一个月,2年甚至3年,40个月,而你终于开始明白了,对灵魂来说生命是是非常深远和丰富的。我肯定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什么。我想如果我没有被关进监狱。我的精神发展会落后许多。
在某种意义上,人民根本没有选择,所谓“选择”应该是对整个民族,对全体人民说:“你有这条路或者那条路可以走,请注意,这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条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你可以对20年,50年后做出预想。”于是他们考虑之后就投票,这才是“选择”。但我们的选择方式却是……戈尔巴乔夫说过:“我的父亲选择追随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从德国获得资金支持,而且我们知道,也从华尔街获得支持。用于发行数量庞大的小册子和报纸,这些报纸都说:“你为何需要这场战争(指一战)?扔掉武器,杀死军官,回家耕种从地主手中抢到的土地吧。”这就是他们的选择,就像其它所有,唯一的选择,没错,这确实是种选择。我们的人民被那种廉价的诱饵吊上了。为什么?因为这正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你只关心人心的邪恶,殊不知还有贪婪和狂热,以及永远鼠目寸光。
“没有误解,就没有共产主义。”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在我看来,共产主义确实是以一种愚蠢的方式被误解了。西方的政客才没有意识到它巨大的危险,但是现在,当我知道华尔街是如何帮助布尔什维克时,华尔街,美国最大最大的钱柜,帮助布尔什维克巩固他们的地位。我想:“哦不,什么误解,他们完全明白。”当共产主义出现在俄国时,他们知道共产主义很有用,可以把俄国转化为一个原料供应地,剥削它,从它身上榨取利润。不巧的是,后来他们失败了。冷战开始,布尔什维克帝国不断壮大。而今天他们终于再次得逞了。……你能想象出现一个成功的,或者说,一个幸福的名为社会主义的试验的成果吗?任何地方?可能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互相斗争的制度都对人类怀有敌意,这一个和那一个,不管哪个都不会带来好结果。关键是道德良知。只有它在两方都应该得到发展。而我们的政治家对这此漠不关心。
现代社会的结构里,什么可以承担发展(道德)的重任?道德的发展过程应该得到管理。谁能够成为管理者呢?怎样才能推举出一个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宗教在管理它。但道德的发展同时又是不应该从外部来安排的,人们应该自己做出回应。我们的人民中,有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在邪恶和混乱的环境里,以一种诚实坦率的方式生活着,然后安然死去,不带任何罪孽负担。他们中的许多人,代表了人是怎样回应宗教的。宗教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感召与教化,然后由人民自己决定。……我们回顾俄罗斯的历史,试图弄清哪些已经发生过。我们担心今日之事,但我相信那都是古已有之的问题,俄罗斯生命中深重的苦难,不治的顽疾,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和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国家对于维持国民中平民的生活是必须的。没有了国家大批平民就无法生存。另一方面,公平正义如何才能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石呢?这很困难,因为手握权力的人总是有缺点的,不止有缺点,甚至是邪恶的或者被膨胀的野心充满。
在俄罗斯历史上有过可怕的罪恶,但是我不认为西方就更少。英国,法国,德国,在罪恶方面不会甘居人后。美国,自由的火炬,像杀蟑螂一样灭绝印地安人。我们很不走运,我们的政府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一个不稳定的政府任何东西都想不清楚。很多就像今日的改革派,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就承诺改革,政府损害了俄罗斯。你看,在90年代初我们本来可以选择一个更合理的方式来脱离共产主义。……别扯什么“因为某些原因”。不过是因为“某些人”而已。如果来一场选举,你就知道那些名字了。为什么到了今天还是他们?所有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们选择了盲目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愚蠢的做法,尝试任何来自国外的秘方,却从不相信自己的智慧,把所有的石油都送到了私人的手里。
我们已经屈服于相信我们的权力是民主化的。它们根本不民主。当我第一次踏回俄罗斯的土地时我就说过,我说:“我们没有民主(democracy),只有寡头(oligarchy)”。当时这个词根基未稳,而现在大家都接受了它。但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寡头”现在被用来指代金融巨头,绝非只此!包括他们,但不只是他们。总统帮,政府,高层的杜马议员,全部都是寡头。寡头是那些身处顶层的200到300个人,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他们之间做出。
我从来不说“圣彼得堡”,我不接受这个名字。我喜欢“彼得格勒”,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权利来为它改名。到底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的首都取一个外国名字?(十月革命前圣彼得堡是俄罗斯首都,苏联成立后改为彼得格勒,后改为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又改回圣彼得堡)。在索氏这样的大斯拉夫主义者看来,“圣彼得堡”这个由彼得大帝取的带有日耳曼语系特征的名字是西化媚外的象征)。一个“堡”(burg,源于日耳曼语系,有“城堡,有围墙的城”的意思),连“彼得-堡”也不是。彼得读它时像荷兰人一样发音,“Peter-burkh”,再把“圣(Sankt)”放在前面。(sankt在拉丁文中意为神圣)现在谁相信它和“圣彼得”有关?没有人用“圣(Sankt)”了,现在他们都说“圣(Saint)彼得堡”,这怎么可以?就叫彼得格勒!那个地区至今还是叫做“列宁格勒州”。它应该是“彼得格勒州”。
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西方,情节是最重要的,它总是获得最多的考虑。陀斯妥耶夫斯基重视情节,也许就是这个帮助他打开了西方大门。因为在这里他得到的是鄙视和侮蔑,而且默默无闻的死去。他是被西方重新发现的,然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失去了什么。在他的一生都被压制排挤。……他关心他的读者,以及怎样让他们产生阅读欲望。我赞成这种分类:故事情节和道德的情节,当然,他非常重视道德情节,但是从不忽视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卡拉姆津(影响了他),卡拉姆津对道德情节是非常敏感的,他的《俄罗斯国家史》通篇贯穿了道德判断。他的小说也是。一方面,俄罗斯文学在整体上……站得很高。因为它从未丢失的民族性,民族关怀,这是它在文学上的一贯特征。遗憾的是现在它将被粗暴的终结和放弃了。现在人们都想要唯美主义,那种只适于制造肥皂泡的东西。另一方面,很奇怪的是俄罗斯文学……部分是因为果戈理,那个对一切罪恶报以无情冷眼的人,因为他的影响力……忽视了俄罗斯历史的复杂结构层面。是谁创造了这伟大的力量?谁使得它扩张到了西伯利亚?到了太平洋,阿拉斯加,谁将文化推广到了西伯利亚?在18世纪末西伯利亚的文化活动就已经高度发达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却只谈论奥勃洛莫夫,必巧林,奥涅金,这些古怪的,这些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长性的人?那些真正的行动者在哪里?那些开拓者呢?俄罗斯文学忽略了他们。我认为那是果戈里的影响,是他开辟了讽刺、幽默的道路。果戈里无法完成《死魂灵》的第二部并不是个偶然,这要归罪于他所有过高的道德信念和动机,他看不见那些人。他知道他们应该存在,但就是看不见。他努力尝试,但是做不到,那就是他的视野。
对于文学和艺术而言,从1917年开始,已经出现了很多新事物,但只有很少是我们可以写的,如果我们违规,我们就被清除,那些描写了这些事物的人,那些被烧毁的作品……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如何被带去审问的:房子中间是一大堆文件,一些人的房间在晚上被搜查过了,并搜出了这一堆,审讯者正准备处理它们,很大的一堆,很高,形成了一个圆锥形,大量的手稿和书籍,审讯者坐在远离我的桌子边,在我们之间就是那座纸山。我吓呆了,我想:一切都完了。我的战争日记被烧掉了,五本笔记本,一切一切,我被剥夺了那些回忆。我所有写于前线的笔记都没了,这就像一种象征,你明白。所有这些都消失了。在俄罗斯有太多的东西被摧毁,1917年后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极大的改变了,人民也变得不一样了。
这只是纯物理性的:人天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清身边所有的一切,一个艺术家应该要和他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他只是记下一时的印象,那更像一篇随笔,一篇报告,而不是一篇艺术作品。只有极少数作家能够捕捉到即时的现实碎片。契诃夫可以做到,但是大多数人都需要时间以让自己的感受沉淀下来。因此,在特定的年龄有些人会开始写作,不是关于历史的过去,而是关于他私人的过去,关于他自己生命的早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回忆录?许多人写关于他们的青年时代,何时?在他们的老年。老年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往日的记忆片断变得格外鲜活。关于这点是有心理学依据的。
我和写作有一种神圣的关系,我在履行某种义务。他们在上帝之前的责任感已经逐渐消退了,即使和上帝无关,也是某种更高的力量或者监督者。某些比人自身更加伟大的事物。这种责任感的缺失是最主要的原因。今日的作家,他们全部都只在扮演小丑,写一些纯粹的胡言乱语。他们把贝利亚捏造成尼古拉二世的亲戚,然后就围绕这个构建出自己的小说,或者把夏伯阳当作一个神秘主义者。这种胡扯是为了什么?这种例子可以没完没了的举下去。这是从人的衰落到到精神的衰落。
(文学是感性的艺术。)在它里面有理性的元素,甚至有学术,分析的元素,但是感性是必须的,否则它就很枯燥。所以,文学是一种组织的艺术,天生就是,它接近建筑艺术,人们是否明白呢?诗歌更像音乐,而散文更像建筑。……艺术有很大的空间,它有助于培养灵魂的细腻和敏感,让它变得柔软,柔软而纤细。普罗提诺是亚历山大里亚派哲学家,他曾说过:“美就是透过物质看到的真理之光。”当真理通过物质触及我们,那就是美,美是高贵的。……我们知道在最近的4个世纪里文明发展的步伐是最大的,在那之前,非常慢,数千年缓慢前进,只有很少的变化,但是今日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忽略了灵魂。灵魂的空虚,人们开始失去他们的灵魂。为了物质的发展,为了文明。而艺术让人类对死亡做好准备,以各种方式。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9942]
思前: 从“又一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