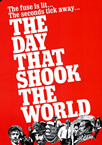2025-07-17《萨拉热窝事件》:枪声覆盖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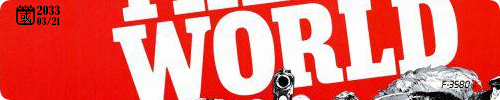
最后是被逐渐放大的世界地图,“萨拉热窝事件”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黑山向奥匈帝国宣战,俄国支持塞尔维亚,而德国则作为奥匈帝国的同盟向俄国宣战,而法国坚守和俄国的盟约,英国也向德国宣战,美国则站在英国这一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甚至标志着世界格局真正发生了颠覆,旧秩序土崩瓦解,人类由此真正进入了二十世纪。而在世界被这一事件彻底改变的同时,在宏大叙事之外还有属于刺杀者个体的命运:丹尼洛被处以绞刑,特里夫科死于狱中,默罕默德逃亡黑山,奈德里克和加夫里洛均死于狱中……
“青年波斯尼亚”这一爱国组织的激进人士完成了刺杀,在他们牺牲的同时也实现了“为国捐躯、流芳百世”的人生理想,而随着刺杀事件的上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旧秩序完全解体。这就是“萨拉热窝事件”导致的最后结果,而在韦利科·布拉伊奇的这部电影中,关于这一事件呈现的是“三段论”,最后的结局只是在片尾被提及;大部分的情节展示的是刺杀事件的密谋、行动等过程,而真正投弹和开枪的刺杀也占了很小一部分;除了过程和结局之外,就是前奏,实际上在整部电影中规中矩的叙述之外,最具叙事意义的则是前奏:在历史照片和文章之后,镜头里出现的就是一把枪的枪口,它带来的视觉冲击就指向了“暗杀”,接着是训练场中击中的人形靶子,萨拉斯正在给刺杀者进行射击训练,之后他又示范了敲击型炸弹的使用;镜头变换到另一个场景,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正在树林里狩猎,除了豢养的动物被放飞而射杀之外,野外的野猪、兔子、小鹿均在枪口下丧生,狩猎人员还与这些猎物合影留念。
一边是波斯尼亚爱国者在进行射击训练,另一边是斐迪南大公在进行狩猎,都有武器,都有目标,都是射杀,也都响起了和死亡有关的枪声,这一切构成了布拉伊奇的故事前奏——甚至在这个前奏里,没有人声,或者说都被枪声所覆盖。当故事从枪声开始,它在交叉剪辑中就演化为一种枪与枪的对立,枪声与枪声的对话:对于爱国者来说,刺杀费南迪大公就是推翻奥匈帝国的统治,就是从压迫的世界中寻求独立和自由,这就是他们口中惊天动地的事,这就是寻求国家解放的“革命”;对于费南迪大公来说,用枪声猎杀猎物,就是对弱小国家进行征服和占有,当国王约瑟夫还在担心进攻塞尔维亚会遭到俄国的反对,费南迪却早就和德国皇帝表达了自己的决心,而德国皇帝更是好战地指出了狩猎的下一步计划:“你在狩猎场浪费的弹药足够让你征服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个前奏完成的枪声叙事,实际上也是对于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的一种反转:几名爱国者训练是为了刺杀,而刺杀就意味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完成国家革命,费南迪大公的狩猎行为是一种个人爱好,墙上装饰的就是4000多只鹿首的标本,但是为了使帝国的权力更为强大,满足个人爱好的狩猎子弹也可以射向那些需要被征服的土地。
| 导演: 韦利科·布拉伊奇 |
前奏的“枪声叙事”完成的是不同的个体与国家的矛盾,而这些矛盾都被推向了“萨拉热窝事件”这一过程当中。在从前奏向过程的转化过程中,其实这种反抗者和统治者的矛盾被弱化了,它们几乎就沿着各自的轨道行进,布拉伊奇重点展示的是爱国者从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出发,向着萨拉热窝进发的过程,在其中出现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个体之间的“习惯”和他们对革命的观点:加夫里洛、奈德里克和特里科夫是三名刺杀的主要力量,但是和加夫里洛的决绝、特里科夫的沉默不同,奈德里克在一路中总是爱和女人搭讪,而且也总是把刺杀行动挂在嘴边,口无遮拦的他惹怒了加夫里洛和特里科夫,甚至差点就因说漏了嘴了泄密——的确,这样一种行动者对于刺杀行动来说就是冒险,毕竟路上有奥匈帝国的士兵,更有宪兵。除了这一习惯引起的矛盾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紧张之外,行动最突出的矛盾则是对行动本身的考量:在三个人开启形成之前,在酒吧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暗杀能不能推动革命?有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有人担心机会主义者,对于革命来说,他们都是潜在的危险;历经种种困难终于来到了萨拉热窝,接头人丹尼洛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这样做对吗?”他担心革命的风险就是会成为发起战争的借口,甚至他反对个人恐怖行为,但是奈德里克认为,“刺杀是革命的总信号。”塞尔维亚的军官找到萨拉斯,他让萨拉斯放弃,因为军官担心奥匈帝国将以此为借口对塞尔维亚动武,他不想让塞尔维亚卷入纷争,萨拉斯当然拒绝了他,但是当萨拉斯也来到了萨拉热窝,面对可能的形势,他也改变了注意表达了不安,他说的一句话是:“我害怕战争。”也正是这句话让坚持革命的加夫里洛十分生气,他不辞而别开始了自己对刺杀行为的准备。
要不要革命的担忧涉及到革命的性质和结果,甚至关涉到革命行为是不是会改变性质变成一场战争,实际上这些矛盾最后也变成了真实的现实:不仅仅是刺杀费南迪大公,而是对奥匈帝国的反抗,反抗以复仇的方式演绎,最终是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和更高级别的镇压和打击,当然最终在各方利益的驱动下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也许是那些爱国者没有料到的,也就是说暗杀不仅没能换来自由与和平,反而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似乎刺杀这一偶然事件引发了蝴蝶效应,布拉伊奇甚至在电影中也对整个事件中的偶然因素进行了叙事:假如奈德里克在行动中泄露了计划,假如在列车上加夫里洛的身份被暴露,是不是就无法顺利抵达萨拉热窝?假如塞尔维亚的长官劝说萨拉斯放弃行动而萨拉斯听了他的话,是不是不会有之后的暗杀行为?或者说当奈德里克扔了炸弹巡视的车辆已经警觉到了危险,如果他们取消巡视是不是费南迪就不会被暗杀?而且这其中还有司机开错了路的情节……
似乎很多偶然因素集合在一起,看起来只是几个人的行动,但是最后还是完成了刺杀,而且它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改变了事件的进程,这就是或然中的必然——开头的枪声就是这种必然性叙事的一种暗示,它是革命者“想死”的决绝,它是“自由万岁”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汇聚成一个词,就叫做: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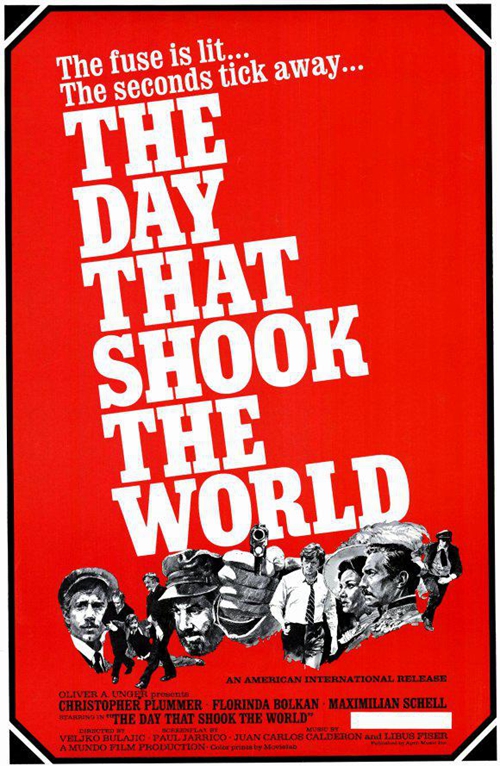
《萨拉热窝事件》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619]
思前:《降头》:妖魔化的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