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18《了凡四训》:此义理再生之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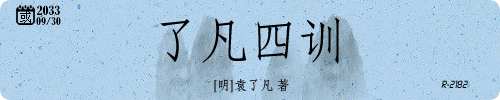
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
——《立命之学》
一切祸福自己求之而为“圣贤之言”,为天所命则是“世俗之论”,也就是在事在人为的意义上区别了圣贤之言和世俗之论,将命数做如此二分法,就在于袁了凡从云谷那里得到了启示:在栖霞山中与云谷禅师对坐三昼夜不瞑目,袁了凡说起以前孔先生给自己算命,“吾为孔先生算定,荣辱死生,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当时的云谷便笑他,“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在这里云谷就从袁了凡把一切看做是命定而嘲笑他,并进而分出了何为豪杰,何为凡夫,也由此区分了世俗之论和圣贤之言,在云谷看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将凡夫变为豪杰,把世俗之论变成圣贤之言,就在于从昨日死变为今日生,而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义理”,“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
那么,云谷对袁了凡一生转变所起关键作用的义理到底是什么?第一篇《立命之学》可以说是袁了凡的一部“自传”,而他对于命运的改变有过两个关键人物。童年时父亲去世,按照母亲的人生规划,袁了凡不考功名而是去学医,因为在母亲看来,学医可以赚钱养活家庭,也可以救济别人,而且医术精湛也可以成就名声,而这也是父亲生前的夙愿。所以袁了凡就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开始学医,但是某一日遇到了飘飘若仙的孔先生,他对袁了凡的问题便是:“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何不读书?”也是在这个问题的刺激下,袁了凡有了读书之念,回来他便开始拜师读书。孔先生给袁了凡指出了人生的第二条路,更为关键的是,他传授袁了凡皇极数正传,而且给他推算了一生的吉凶祸福,何时会考取功名,哪年会做贡生,贡生之后某年会做知县,知县三年后便辞职归家,之后到了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便寿终正寝,而且一生没有儿子。
这就是孔先生给袁了凡推算的一生,当袁了凡认为自己进退皆有命,于是“澹然无求矣”,在他留京一年时,“终日静坐,不阅文字。”直到在未入监的情况下游南雍,在南京栖霞山访云谷禅师,才彻底有了关于命运的转变。在云谷看来,当原料放将一切的荣辱死生都看做是一种定数从而放弃了“妄想”,便是一种凡夫行为,“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在这里云谷其实指出了两种定数,一种是孔先生的推算,当孔先生将他的一生的遭遇都算出,袁了凡“不曾转动一毫”,便是听命的凡夫,另一种则是袁了凡不存“妄想”的消极态度,也就是无心的状态“终为阴阳所缚”,这双重的束缚使得袁了凡在云谷看来成为了凡夫俗子,一生的荣辱都成为了无欲无求的天命,也就成了世俗之论。由此云谷开启了袁了凡的后半生,也就是以义理构建的“再生之身”,它是对血肉之身的告别,是对凡夫俗子的转身,是对世俗之论的终结,这个义理就是“立命”:“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相爱,务要惜精神。”云谷提出了关于立命的两条准则,那就是“修身以俟之”:“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曰俟,则一毫觊觎,一毫将迎,皆当斩绝之矣。”“修”就是把身上已有的过失和罪恶,如医治疾病一样去除,之后更不要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一旦有了就要将它斩绝,而“俟”就意味着在一切的修行之后被改变的命运就会在等待中自然降临,“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
可以看出,袁了凡的人生转变有两个关键时刻,母亲让他学医是为了养家糊口也是为了了却父亲的夙愿,这是在最基本的生存意义上;孔先生让他读书以考取功名,这是走向仕途的开始,但是孔先生将袁了凡的一生都推算完了,人生没有悬念也没有了妄想;之后云谷指出了事在人为的积极人生,并将他从凡夫俗子的状态变为自己求之而主动掌控祸福的圣贤状态,也正是在这个启发之下,袁了凡开始了新的人生:将自己以前的号“学海”改成了“了凡”,以示警醒;开始发愿做三千善事,也起了求子之愿,“辛巳,生汝天启。”历十余年三千善行做完又起求中进士愿,而且许下行善事一万条;“丙戌登第,授宝坻知县。”担心一万善行无法圆满,某日做梦梦中有神人让他为百姓减收粮税,于是袁了凡不仅把全县的田赋都清理了一遍减轻赋税,而且还把自己的俸银捐给了五台山斋僧。这一切就是袁了凡被改变的人生:孔先生推算他一生无子,但是袁了凡有了儿子天启;孔先生推算袁了凡五十三岁寿终正寝,但是袁了凡五十三岁连疼痛都没有,而写下这篇给儿子的《立命之学》时他已经六十九岁了。
这一种打破惟天所命的福祸人生就是自己驾驭的人生,所以在《立命之学》中袁了凡写下了“圣贤之言”: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阁一生。”要在所谓的命运面前常思常想,“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即时当顺利,常作拂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贫窭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不仅要思个人命运,还要将其延伸到国家、父母和他人:“远思扬山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愆;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种种圣贤之言都是在云谷的启示下所得,而种种的人生改变也是在云谷的教诲中发生,袁了凡之后半生的开启就是义理人生的开启,所以他对儿子的话是:“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旷也。”
| 编号:W87·2250914·2353 |
《立命之学》是袁了凡在六十九岁时所做,《了凡四训》中的《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则是他早年著作中《祈嗣真诠》中的两篇,而《谦德之效》是袁了凡晚年所作的《谦虚利中》,虽然这“四训”各自成篇,完成的时间也不同,但应该都是在云谷禅师的对谈之后,都是在得到义理之后,而且这四篇被后人整理刊刻成书,也有其义理的统一性。在不知何人所著的《旧序》中就指出了四训的关系,他认为“改过”和“积善”是正文,“‘改过之法’,发挥‘诸恶莫作’;‘积善之方’,细讲众善奉行”,而“立命之学”则是现身说法,也就是说,“立命之学”回顾自己的经历而现身说法,他所说的法就是改过、积善和谦德,这也是自己求之的“圣贤之言”,它们构成了一种总纲和分述的关系,“故‘四训’不独为千古名言,亦千古妙文也。”四训被称为是“千古妙文”,就在于给人生注入了一种可以驾驭的义理,它是修身,它是治性,它是立命,它是善行,它是改过,它是谦逊,但是作为古代伦理学的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了凡四训》的基本义理却是如何得到求功名的福田。
《立命之学》中记载遇见云谷禅师,当云谷指出凡夫和英雄的区别,这义理不是别的,就在于命是不是“我作”,福是不是“己求”,他引用佛经上的说法来阐释“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即“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在这里所谓的福就是富贵,就是子孙,就是长寿,而孔先生之前推算的命也在于登科和生子,云谷对于袁了凡命运的改变就在于这福田,“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他阐述说,福田即包括道德仁义,也包括功名富贵,向内就是反躬内省,向外则是求之有道,如此,“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在这里云谷就明确指出了什么是人生的福田,什么又是内外双得,无疑功名观就构成了袁了凡的立命、改过、积善和谦德的基本态度。
在《改过之法》中,他指出了改过要有三心,一是耻心,二是畏心,三是勇心,耻心区别于圣贤和禽兽,畏心则是对天地鬼神存有敬畏之心,而勇心就是不因循退缩而是奋然振作;他也指出了改过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禁其事”而改,第二个层次是“明其理”而改,第三个层次则是“从心二改”,这是最高层次也是最有效果的改过之法,“大抵最上治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无。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须随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但不管是改过之三心,还是三个层次,都是为了“获福而远祸”,“至诚合天,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在《积善之法》中,袁了凡指出积善和行善要明白义理,义理之要点就在于区分积善之真假、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同时也指出了“随缘济众”的十条原则:“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不管是明白积善之义理,还是济众的方法,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福报,他在前面举例说明了积善的好处:建宁人杨荣的曾祖以及祖父曾在洪水中救人,正因为这一善举,“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贤者。”鄞人扬自惩由于存心仁厚、守法公平,他还遇囚人乏粮,常多方以济之,子孙就因为积善而获益,都成为了名臣;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结果后世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在福建甚至有“无林不开榜”的说法……凡此种种,积善都是为了子孙能获得功名,所以在积善何谓阴阳中说,为善而被人所指是阳善,不为人所知则是阴德,阴德是“天报之”,而阳善则是“享世名”,“名,亦福也。”
虽然积善之方有为他人行善,“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济世之心不可媚世,“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为曲;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曲;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即为曲。”积善更在于国家大事,“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但是种种方法,最后的归结点还是自我的福分,还是命运的福田,还是子孙和功名。而在《谦德之效》中,袁了凡指出了谦德的意义,“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他举例了赵裕峰的故事,他十二岁就中了举人,但是参加会试却多次不中,有一次他拿着自己的文章去见嘉善县的名士钱明吾,不想钱明吾竟然拿起笔把他的文章涂掉了,赵裕峰没有发火而是把自己文章的缺失改了,这便是“满招损,谦受益”的例子,但是赵裕峰之所以怀有谦德,袁了凡举例说明的也是为了最后他终于考中了,而其他关于谦德的例子,袁了凡总是用“遂登第”“果中式”等词来说明最后的成功,也就是说,谦德和改过、积善一样,是为了达到命运的改变,是为了得到福田的回报,“须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而虚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基。”他还引用古语,“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宫贵:必得富贵。”所以念念谦虚,尘尘方便,感天动地的作用就是“造福由我”,就是完成求登科第的目的。
立命也好,改过也罢,积善也好,谦德也罢,这一切处处体现着古代知识分子狭隘的功名观和成功学,这也是“四训”内在的逻辑线,尤惜阴所撰的《重刻<了凡四训>跋》,比《原序》更合理地解释了“四训”内在的关系,在他看来,因为命运被前定,而命数又可以转移,所以开端就是立命之学;而改过又是立命“第一着功夫”,所以改过之法为第二;积善之方则是立命之正轨,也就是“必由之路”,或者说改过和积善是抵达立命的正反两条路,而谦德就是立命的一种补充。所以立命就是原则,就是总因,那么袁了凡为什么一再强调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被推算的命运?五十三岁寿终正寝也罢,没有子嗣也好,袁了凡从孔先生到云谷的转变,并不在于改变这两种命运,而是他对于现实之困境的一种摆脱,在《积善之法》中阐述十条纲领时,袁了凡说到了“吾辈处末世”这样一句话,他指出,正因为处于末世之中,所以,“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真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盖人、形人和困人才是末世之表现,所以要用自己积善的方法改变这一切。
为什么袁了凡会生出“吾辈处末世”的感慨?为什么袁了凡要用积善解决盖人、形人和困人的问题?这也许和袁了凡的经历有关,《原序》没有介绍,袁了凡的《立命之学》虽然可以看做是他的自传,但其实只是“半部”自传,因为袁了凡只是讲述了人生的两次重大改变,却没有提及真正感受到“末世”的遭遇,附录中彭绍升的《袁了凡居士传》中则记载了袁了凡遭遇的真正人生变故,这就是发生在他成为宝坻县县令之后:
后七年擢兵部职方司主事。会朝鲜被倭难,来乞师,经略宋应昌奏了凡军前赞画兼督朝鲜兵。提督李如松以封贡绐倭,倭信之,不设备,如松遂袭,破倭于平壤。了凡面折如松,不应行诡道,亏损国体,而如松麾下又杀平民为首功,了凡争之强。如松怒,独引兵而东。倭袭了凡,了凡击却之,而如松军果败。思脱罪,更以十罪劾了凡。而了凡旋以拾遗被议,罢职归。居常善行益切,年七十四终。
劝解提督不成,反而被罪劾,被诬陷,最后只好“罢职归”,这一段经历也许构成的正是袁了凡被盖人、形人和困人的命运,也成为了他所定义的“末世”,所以退居乡间,69岁时再次回顾人生才有了立命之说,才有了“居常善行益切”的实践,而一切的立命就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功名,就像孔子所说:“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