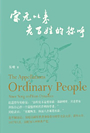2025-10-16《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呼》:避免“历史一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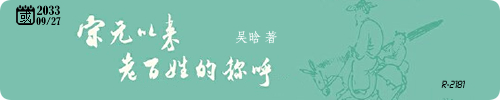
打开书还没有真正进入阅读,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目录里发现很多文章以前就已经读过,比如《论皇权》《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明初的恐怖政治》《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还有《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胡蓝党案》以及很多关于历史人物的文章。此前吴晗的作品阅读过两本,最早的一本是台海出版社的《明朝历史的教训》,另一本则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历史的镜子》,从书柜里取出这两本书,仔细对比目录,的确很多文章出现在不同的文集中,甚至有些三本书里都有。
这本作品集从编目来看,非常有系统性,它将文章分成九个大类,九个章节的标题分别为《皇权:君权神授》《战争:金戈铁马》《官员:骄奢淫逸》《刑狱:锦衣厂公》《经济:资本萌芽》《教育:读书不易》《百姓:纳赋力役》《风俗:服饰丧葬》和《人物小传》,除了第九章之外,这些标题工整统一,看上去完全是系统性的建构,内容涉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经济、社会风气、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但这无非是编辑的功劳,从内容上看,却完全是将不同著作中的篇目杂糅在一起,彼此之间反而缺少了整体性。其实,这本书选取的文章来自《明史简述》《朱元璋传》《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投枪集》《胡惟庸党案考》等多部经典历史著作——一个尴尬的现象是,所阅读的三部吴晗作品都不在这些经典历史著作之列。
实际上,这些著作虽然都是吴晗所著,但是真正是吴晗亲自编订成册的并不多,《胡惟庸党案考》是吴晗1930年代发表于《燕京学报》的学术论文,它通过挖掘丰富的史料,以缜密的考证和推理揭示了明朝著名大案胡惟庸党案考的真相,首次还该案以历史本来面目,被称为吴晗史学著作中的扛鼎之作;《朱元璋传》是吴晗呕心沥血二十载完成的作品,是一部以小说的写作说法完成的帝王传记,生动的文学想象和精练的文笔是这部著作最大的特色;《明史简述》则是吴晗在中央高级党校所作的学术讲演的记录稿,扼要系统地讲述了明太祖建国、明成祖迁都北京、北虏南倭、东林党争、建州女真、郑和下西洋、资本主义萌芽等明代历史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除了这些著作之外,吴晗的作品集还包括随笔集《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投枪集》和《历史的镜子》,而这其中很多也是出版社对吴晗作品的汇集,比如《灯下集》就是200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随笔集,收录了吴晗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军事方面的文章,而《胡惟庸党案考》这部书也是在吴晗学术论文的基础之上收录了18篇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包括《烟草初传入中国的历史》《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等文章。
如此说来,篇目繁多的吴晗著作很多就是这种靠编辑“移花接木”而汇集的作品,此前阅读的《历史的镜子》反而是吴晗自己编订的一部作品,而《明朝历史的教训》也是作品的汇集,手头的这本《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呼》更是难逃这一出版窠臼,甚至标题本身就制造了误区:这仅仅是第七章《百姓:纳赋力役》中的一篇短文,却拎出来变成了一本书的书名。不过也不能苛求太多,毕竟只是一本以8.8元购得的低价书,略过那些已经读过的篇目,在吴晗的这些小品文中也窥得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说法”,而这些说法基本上有三部分构成,一是纯粹是知识的介绍,比如在关于战争的章节中,有对于战争“三官”、首级论功和帅旗作用的《古代的战争》,在经济一章中,从和夏衍闲谈引出关于烟草的传布线路,在百姓一章中则有关于南人和北人地位变迁的《南人与北人》,风俗篇章中的《古代的服装及其他》《古人的坐、跪、拜》《盟与誓》《路引》《度牒》以及《明代的殉葬制度》都是相关知识的简单介绍。《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呼》也是此类文章,不过吴晗是以填补“阙疑”的方式介绍了古代百姓的称呼,“求之正史不得,只好读杂书,读了些年杂书,这个疑算是解决了。”在他看来,在封建社会平民百姓没有功名,所以他们既没有学名也没有官名,通常的做法就是用行辈或者父母年龄合算成一个数目作为符号,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五说:“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后来就普遍采用了这一命名方式,到了清末民初还有这样的传统,鲁迅《社戏》里就写到了八公公、六一公公等名字。除此之外,吴晗还介绍了名字中带“秀”和“朗”的称呼,它们都表示身份地位,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说:“江阴汤廷尉《公余日录》云:明初间里称呼有二等,一日秀,一日郎。秀则故家右族,颖出之人,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儿秀,称郎则曰某儿郎,人自分定,不相逾越。”
| 编号:Z51·2250914·2354 |
古代百姓命名的规则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所以吴晗也感叹:“这也就难怪正史上从来不讲这个事情的道理了。不但‘《元史》无征’,什么史也是无征的道理了。”在历史知识的介绍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是这本书中第二部分的“说法”,吴晗通过对历史文献进行“考察”,从而总结出一些观点,这其中的代表就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来大家讨论。”在吴晗看来,要确定某个事物处于萌芽状态,“必须要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要具体地指出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以往的时期所不可能发生和没有发生过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发生的。”如果不从这个界限进行考察,那么就会犯了“历史一般化”的错误。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吴晗将它局限在14世纪至16世纪发生的事实上,他举例了八点:一是手工工场的出现,明朝徐一奎在《织工对》的文章中就写到了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浙江杭州等地出现了手工业纺织工场,工场有若干间房子和若干部织机,工人都是雇工,他们不占有生产工具,老板出房子、及其、原料,工人则出劳动力,然后根据工作情况取得计日工资;第二点就是新的商业城市的兴起,很多文章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苏州等三十三个新的商业城市,吴晗认为,这并不是整个明朝的情况,它们都出现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是因为南北运输的需要才带动了城市的发展,这三十三个城市其实是当时建立的三十三个钞关,钞关就是就是向往来的货物收税,三十三个钞关就是三十三个城市,但是并不等于明朝就只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明成祖的时候就不止这个数字了。
另外,倭寇、葡萄牙海盗和沿海通商也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内地某些官僚地主也参加商业活动和经营手工工场;当时的人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化也都有总结;对钞票管理不善促进了货币经济;还有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反映了当时的变化;明朝后期还出现了一些替商人说话的政治家。从这八个方面来看,吴晗认为,这些情况都是明朝以前没有的,或者说以前并不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变化是旧的东西改变了,新的东西露出了头。”这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只不过这些只是萌芽而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此后还遭受到了压制,“因此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汉代之巫风》则是吴晗从典籍中考察巫风,尤其梳理了西王母的种种传说以及和汉武帝之间的关系。他从《封禅书》和《洞冥记》中所记载的“神君”入手,对比发现它们具有血缘关系,长陵女子神君是西王母的原型,之后西王母就衍成了女性,“因为其事秘,世莫知,所以后来西王母和汉武帝的故事,便不得不衍成各个不同的形式。”而从焦氏的《易林》这部汉代卜筮的书中,吴晗发现其中关于西王母的条目占了全书的二十分之一,“在这一些零碎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汉代的巫风和民间信仰,以及汉代农村社会的生活。”西王母不仅是古代亲族中近血缘女性的通称,而且慢慢变成执行灵巫的职司,“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相对欢喜,王孙万户,家蒙福社。”而到了后来进为社神,成为地方官吏定期祭祀的神衹:
李榕《华岳志》引唐李商隐王母祠诗,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仇池石》《羊城古钞》都记广东有王母祠,为乡民求福禄求子之处。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载西王母咒语诅人立死。道教经典中有《道教灵验》记述西王母塑像救疾验,《道藏》中有《西王母反胎按摩玉经》,有《西王母叙诀》《广黄帝本行记修行道德条登真隐诀》,《神州七转七变经》《五符经》《三皇经》《内音玉字经》《洞真西王母实神起居经》《西王母实生无死玉经》元宝经黼均载有西王母祠祀、咒法、魔让、祈福、永生的故事。
但是另一方面,吴晗分析认为,西王母信仰其实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问题,尤其在农村,政治上的松懈病态使得农民急需要这样一种神祇,“在发生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中,产生一种所谓民族的歇斯底里亚症,自上一年的年底所举行的蜡祭,继续地把它延长到第二年春间而已。”所以在很多对历史的考察的文章中,吴晗总是会进行古今对比,或者批评当时的社会问题,在《诈降和质子》中吴晗就认为,人被当成抵押品,是死是活度取决于家长政治地位的变化,这背后就反映出了封建社会的痼疾,在《阵图和宋辽战争》中,他考察了古代排兵布阵的意义之后,也指出了宋辽战争中宋屡战屡败的原因就是统帅的无知,“连兵将所在、兵数多少也不知道的前方统帅,只凭皇帝所发阵图作战。这样的统帅,这样的御将之道,要打胜仗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杨家将之所以战死,在更高的统帅内部则缺少有才略、有决断、有经验、有担当的人,“这一事实也反映了宋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
除了这两类之外,还有第三类文章,那就是从历史联系到现在,不是把以古讽今,而是在“历史的镜子”中照见现实所为,。《古人的业余学习》中吴晗就介绍了古代出身贫困却奋发图强的例子,“历史上,尽管封建地主阶级包办了学术文化,但是学术文化却不尽出于封建地主阶级,穷苦农民和牧猪牧羊的孩子只要有坚定的决心,持久的毅力,不懈的学习,是可以克服一难,攀登当时学术的高峰的。”由此他认为业余学习之风,古已有之,而现在,“有各种各样业余学习的机会,党和政府为愿意学习的人们准备了一切条件,看看我们先人的榜样,不是值得我们思之重思之吗?”在《古人读书不易》一文中,吴晗则以回忆了自己“读书不易”的经历:小时候家里穷没有书只好到有书的人那里借书,借来书就把它抄下来,“大冷天,砚都结冰了,于是赶着抄,抄完了送回去,不敢错过日子。”后来长大了想读书却没有好老师,于是赶到百里外去找老师听课,求师要冒着大风大雪,脚皮磨破了,四肢冻僵了,才有了机会跟老师学习,“一天吃两顿,穿件破棉袍,从不羡慕别人吃得好,穿得好,也从不觉得自己寒碜,因为求得知识是最快乐的事情,别的便不理会了。”
对历史知识的梳理,对历史现象的考察,对历史问题的批评,吴晗的这些文章还是没有进行深度的阐释,或者传播历史知识是他著书的基本任务,但是从历史中发掘那些值得我们探讨的东西,又从自己亲身经历传达读书的重要性,对于吴晗来说,这也许才是真正避免“历史一般化”的做法。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