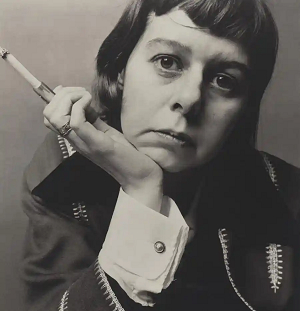2025-10-18《心是孤独的猎手》:上帝总是缄默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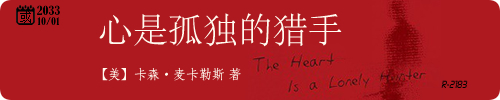
哎!自由和海盗哎!资本和民主,那个有胡子的丑男说。然后自我反驳。说自由是所有理想中最伟大的。我只是需要个机会写下自己创作的这首音乐,成为一名音乐家。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女孩说。我们不被允许服务,黑人医生说。这对我的同胞们是神圣的需要。阿哈!“纽约咖啡厅”的老板说。他是最有思想的一个。
——《第二部·7》
有胡子的丑男人是杰克·布朗特,他在辛格面前说出了他想要的自由;女孩是米可,辛格是她家的租客,米可告诉辛格自己怀揣着一个音乐的梦想;黑人医生是本尼迪克·马迪·科普兰,不相信上帝的他希望黑人能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纽约咖啡厅”的老板是比夫·布兰侬,辛格有时会在那里喝点酒,在他看来,比夫是最有思想的人……杰克、米可、科普兰、比夫,他们或者居住在小镇上,或者从外地来到这里,当他们在辛格面前表达自由、理想、权利和思想,实际上就是在对辛格倾诉,甚至在和他对话,“说话”构成了镇上的他们和辛格的关系,但是这个在他们之中的对话者,却是一个哑巴,一个丧失说话能力的人,一个永远沉默的人。
他们和辛格于是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他们可以向他诉说,但是言说缺席的辛格却无法对他们诉说,可以说话的人和哑巴变成了不对等的关系,但是单向的关系,而在这个不对等和单向的关系里,是不是预示着“孤独”将成为无法摆脱的宿命?辛格在这个小镇上生活,他每天都会在街上闲逛,于是关于他的流言四起,黑人妇女说他可以召唤死魂灵,计件工人认为哑巴的传闻扑朔迷离,有人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同类,富人认为他很富,穷人认为他很穷,“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想象出来的辛格。”他们向辛格倾诉,和辛格对话,更多的人对他制造了流言,将它变成了想象中的存在,无论是倾诉还是流言,都是在一种他们拥有的言说权利中定义着辛格,也正是在这种定义中,辛格反而变成了一个他者,沉默的他者,平静的他者,没有理想的他者,这种他者的存在是将辛格异化了,而被定义而异化的辛格甚至把自己也想象成了另一种存在。
那是一个梦,在梦中他跪在台阶的中间,赤身裸体,而身后的地面上,也赤身裸体跪着杰克、比夫、米可和科普兰,四个人的身后则是数不清的人,然后便发生了骚乱,在骚乱中台阶坍塌,性格感到自己掉了下去,“他吓得一颤醒了过来。晨辉映得窗户发白。他感到害怕。”这是一个辛格所做的梦,在梦中他跪在所有人的前面,像极了一个引领者,“暗黄色的灯笼在黑暗中一摇一摆,其他的东西都一动不动。”他是他们看见的光芒,他是他们眼中的上帝?正如米可曾经想象的上帝,就像裹着白床单的辛格,“上帝总是缄默不语”,一个沉默的上帝,一个被想象的上帝,就像哑巴,他无需说点什么,却接纳了所有人对他的倾诉和想象,只有在这种倾诉和想象之中,上帝才是存在的,上帝才会宽恕一切,“上帝宽恕,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但是,缄默不语的辛格又何尝没有倾诉的欲望?当他变成沉默的上帝,也意味着人们取消了他所需要的言说,而这一切又将他推向了最深的孤独。
但是辛格这个梦却是某种发出内心的呐喊,因为当他梦见自己跪在那里的时候,正是看见了另一个赤身裸体而在最顶阶上的安东纳普洛斯,安东纳普洛斯的手上举着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才是那盏黑暗中的灯,在这个意义上,站在最高台阶上的安东纳普洛斯才是辛格心目中的上帝,而且是辛格所认为缄默不语的上帝——因为安东纳普洛斯也是哑巴。当小镇上的他们在辛格那里找到了倾诉的欲望,当他们在倾诉中表达了对自由、理想、权利和思想的向往,当更多的人完成了对辛格的想象,甚至当他们都把他当成了照亮黑暗生活的上帝,那么对于辛格来说,安东纳普洛斯是不是也是他倾诉的对象,也是照亮生活的明灯,也是驱赶孤独的上帝——或者说,安东纳普洛斯才是辛格生命中真正言说的象征,“我不想孤单一人,不想没有懂我的你在身边。”但是这个上帝却是缺席的,正如辛格成为他们的上帝是所缺席的言说一样。
缺席而孤独,这就是卡森·麦卡勒斯所要表达的主题,而无论是缺席还是孤独,都意味着寻找一个对话者。第一部的第一章节可以看做是这种缺席的开始,“镇上有一对形影不离的哑巴朋友。”这是小说的第一句,辛格和安东纳普洛斯就是这对形影不离的朋友,安东纳普洛斯在堂兄弟的水果店里打工,辛格则是珠宝店的银器雕刻师,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干着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就是一对无法分开的知己:他们清晨无声地走在镇子的主路上,暮色时分两个人又一起慢悠悠回家,两个人一起做饭一起吃饭,饭后会对弈,工作之余会去图书馆借书或者在周五去看一场电影,发薪的日子就会去照相馆为安东纳普洛斯拍照。他们形影不离,他们的世界远离他人,所以不会说话的他们却从来没有感到过孤独,但是有一天安东纳普洛斯患病了,辛格无微不至照顾他,一周后安东纳普洛斯康复了,但是从此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安东纳普洛斯像换了一个人,连辛格也无法理解,几个月之后安东纳普洛斯的堂兄弟将他送到了两百英里以外的州立精神病院,从此小镇上就剩下了辛格,他变得行尸走肉,他不断梦见安东纳普洛斯,但是梦里的朋友变得虚无缥缈。
| 编号:C54·2250914·2356 |
形影不离的朋友被送走,对话者不在,孤独便真的产生了,“他的脸上带着只有大悲或大智之人才有的、沉思般地安详神色。不变的是他依旧游荡在镇上的街头巷尾,沉默着、孤零零的。”这是缺失的开始,没有人真正读懂辛格,但是所有人却从辛格的孤独、平静和沉默中找到了倾诉的对象,并将他变成了想象中的上帝:辛格所失去的一切只有孤独者才能体会,而他的存在却为更多的孤独者提供了摆脱孤独和困境的动力——当第一章节辛格失去安东纳普洛斯陷入真正的孤独,从第二章节开始则从他们的生活中发现了辛格存在的意义,麦卡勒斯就是以这样的多线结构开始了孤独者言说缺席而被想象的世界,而这样被倾诉、被想象以及被重构的生活,是不是也预示着寻找的真正开始?
辛格有时会出现在“纽约咖啡厅”里,和他平静坐在那里不同,杰克总是会喝醉,老板比夫·布兰依的妻子艾丽丝则骂他是个醉鬼,米可也会来到这里,他告诉比夫和杰克辛格是她家里的租客,““世上总有一些有思想和一些无知的人。每一万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有思想,其他的都不行。”喝多了酒的杰克总是在辛格面前说话,而辛格则很有耐心听他说完,一个在滔滔不绝地说,另一个耐心地听他说,然后报以独特的微笑,最后,“一如既往,他双手插兜,疾步离开了。”谁也没有想要知道辛格的生活,更不会打听他的故事,不会触及他的内心,但是从辛格的沉默、耐心、平静和微笑中,每个人似乎都获得了力量,每个人都在诉说中表达着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每个人也都在辛格的沉默不语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权利和理想。
比尔忍受着妻子对杰克的嘲笑,因为妻子艾丽丝患有疾病,而在十月的时候她开始叫喊,送到医院后不久取出了一个新生儿大小的肿瘤,不到一个小时,艾丽丝去世了。虽然比尔在艾丽丝还活着的时候认为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但是当妻子去世他才知道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为什么在真爱中,不常见活着的人自杀追随所爱之人而去呢?只因死者需要活人来埋葬吗?因为需要满足死者身后庄重的仪式吗?”关于死亡,关于重生,他都无法理解,而更难以理解的是女儿露西尔,17岁就嫁给了勒罗伊,以为嫁给了一个好人,却在婚后争吵不断,离婚之后两年又复婚,而现在已经不知所踪,“那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比尔这样对带着年幼的贝贝的露西尔说道。而作为一个有八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希特勒和传言中的战争、猪腰肉的价格及啤酒税度让他苦恼不已。比夫是忧伤的存在,而这个在辛格看来是最有思想的人,也对辛格这个哑巴产生了兴趣,“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哑巴就是自己所想的那样——就算明显那是个误解?”
|
| 卡森·麦卡勒斯:我不想孤单一人 |
米可是个小女孩,她喜欢音乐,大胆而任性的她会爬上屋顶然后高歌,她的理想就是出名,希望自己名字的缩写M.K.会出现在小镇的每个角落,“假如我们家有钢琴,我会每晚都练习,学习世界上的每一首曲子。这是比任何东西我都更想得到的。”这个把理想安放在不愿的未来,却将自己完全置于现实之外,她把世界分为“内心”和“外界”,学校、家和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属于外界,而音乐、计划以及外国都是内心世界,所以当她和哈利在一起,当哈利向她表白,米可却告诉他自己不会结婚,“我不喜欢那样。我不会嫁给任何男孩儿。”所以当弟弟巴伯不小心用枪打伤了贝贝,她却欺骗巴伯贝贝被打死了,还威胁巴伯会坐牢,后来人们找到了巴伯,但是巴伯从此改变了性格,他不再与人交流,他变得胆小,而米可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表达对巴伯的爱,“她想亲亲他,咬他,她发自肺腑地爱他。”所以当她遇到想不通的时候会自虐,“她全力击打一处,直到双泪垂流。然而,她仍觉不够用力。灌木丛下有锋利的石块。她一把抓起,在同一个地方来回刮擦,直到满手鲜血。”与其说米可拒绝外界不如说她躲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而辛格就成为了她心目中既在内心又在外界的特殊存在,她把辛格想象成缄默不语的上帝。
杰克来到镇里没有安身之所,是辛格收留了他,后来他去找了一份在游乐场的工作,但是他对社会充满了仇视,“但是,听着!无论你在哪里看到的尽是卑鄙和腐败。”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卑微地活着,每个人都又瞎又哑,所以他的理想是做福音传教士,周游全国开展布道和复活仪式,他的口号就是行动,“我谋划着一场暴乱——尽我们所能搅起大动静。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杰克是要拯救失去信仰的人,但是同样面临生活的折磨,科普兰医生却从来不相信上帝,他希望黑人用自己的骨气、脑子和胆量改变这一切,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背负使命感,成为科学家、教师和律师,“白种人无声的傲慢是他多年来一直试图忘却的事。每当怨恨油然而生,他就通过思考和学习转移注意力。”但是当女儿波西亚说辛格是个善良的白人,科普兰也拜访了辛格,扭转了他的偏见,但是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而且演变为一种悲剧,他的孩子威利因为和人打架被关进了监狱,在酷刑中甚至失去了双腿,科普兰闯入法官办公室也遭到了殴打,愤怒的他发出的是“黑人同胞们!我们必须站起来,团结一致!我们必须解放自己!”的呐喊。
杰克希望获得自由,科普兰要获得属于黑人的公平,他们所针对的都是这个社会,但是当两人在一起时,却又由于理念的不同而发生争吵,科普兰认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行动就是“以奸治奸,以强制强”,他希望号召大家去示威游行;但是杰克却认为这个计划很疯狂,他要用资本主义的腔调发表演说,指出所有的谎言,让每个人都知道真相,“还得从底层开始。不破不立。为世界打造一个全新的模式。使人类第一次成为社会性生物,生活在有序、受控的社会中,不必为了生存遭受不公。生活在一个社会传统——”科普兰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织布需先采棉”——杰克说他是黑色的谎言,科普兰说他在渎神,双方的争吵并没有从理论变为行动,也没有改变小镇上的歧视。
比尔面对生命和死亡问题,米可纠结于内心和外界,杰克和科普兰在理论和行动的选择中争吵,实际上,他们都在沉默的世界里发声,为了权利,为了理想,为了生活,而辛格自然成为了他们发声的对象,但是在他们的发声中,缺席了言说的辛格依然活在他们都不解的孤独之中,他最想要的就是去精神病院探望自己最好的朋友,安东纳普洛斯才是他摆脱孤独的唯一存在。第一次他在筹划了几个月之后去了医院,他想象着俩人即将共处的每时每刻,但是在他面前的安东纳普洛斯只有乌黑浑浊的眼睛,双手则抚弄着裆部,辛格说起小镇上的那些人,安东纳普洛斯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回来之后辛格开始给安东纳普洛斯写信,虽然他知道安东纳普洛斯不识字,“这段时间没有你,我很孤独。我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再次与你见面。”当新的假期到来,辛格又去了精神病院,但是安东纳普洛斯已经转到了另外的地方,因为他得了肾炎,当他看到安东纳普洛斯,“朋友的脸色死一般苍白。”第三次探望朋友是在半年后,辛格更渴望见到安东纳普洛斯,甚至认为两人已经合二为一,“有时,他会带着敬畏和自卑想安东纳普洛斯;有时又带着自豪——但始终带着不受指责和意志控制的爱。”但是他得到的消息是:安东纳普洛斯已经死了。
从小镇上两个人形影不离,到安东纳普洛斯被送进精神病院,从第一次见面的沉默到第二次见面时的茫然,再到最后隔着生与死永远无法消弭的距离,终于当辛格回到小镇,他喝下了一杯冰咖啡,抽了一支烟,洗干净了烟灰缸和杯子之后,“他掏出口袋里的手枪,朝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活着只有无尽的孤独,当选择死亡就是选择和孤独告别,就是选择和朋友永远在一起,死亡才是告别孤独的唯一办法,才可以永远合二为一。辛格的孤独在失语中,当死亡发生,也许对于小镇的人来说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个缄默不语的人的内心——从第三部开始,麦卡勒斯就为每个人安排了“后辛格”的生活:科普兰在波西亚的安排下离开了小镇,波西亚从辛格那里收获了人之存在的价值,“我真希望我死时,也能像辛格先生一样有那么多人为我悲伤。我真的很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有他那样悲伤的葬礼,有那么多人——”而科普兰开始相信“当下的正义”;杰克对于辛格的死,感到了一种愤怒,他也第一次感觉内心有很多话要对他讲,之后他参与了暴动,最后他选择了北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他心中充满希望,或许,这趟旅行的轨迹很快就清晰了。”第一个发现辛格死亡的米可,已经逐渐长大,她对于音乐的梦想已经变成了在伍尔沃斯上班的生活,但是她还在等待着机会,“哪怕有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事也好,那事也好,事事都应如此。它一定会带来某种好处。”比夫操办了辛格的葬礼,生活还在继续,“当最后再次回到屋里时,他静下心来,清醒地等着迎接朝阳。”
曾经辛格是他们倾诉的对象,他的无声是作为一种缄默不语的存在,是他们自我的投射,而当辛格死去,他们却听到了辛格对他们所讲的话,那些话是对于生活的另一种态度,是重新获得的力量,不管是曾经还是之后,生者的辛格和死去的辛格都成为了一种象征,缄默不语永远是他的孤独,如上帝般存在,正如安东纳普洛斯曾经“说”给辛格的三个首语,它们是:“耶稣”“上帝”和“圣母玛丽亚”。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