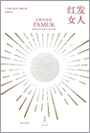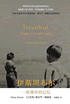|
编号:C39·2160516·1297 |
|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版本:2006年12月第一版 |
| 定价:20.00元亚马逊10.40元 |
| ISBN:9787208066410 |
| 页数:170页 |
“我们两人之间可以真正地相互了解,这不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吗?我提出,人会像喜欢噩梦一样迷恋一个自己对其了如指掌的人。”威尼斯学者和土耳其人霍加,他们联手对付了席卷土耳其本土的一场瘟疫,霍加晋升为皇宫的占星师,威尼斯人则成了苏丹的倾诉对象,他们还为苏丹发明了一件用来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的战争武器。来自两种不同的文明,他们却在神似的相貌中互换了身份,他们成了另一个自己,却也是一场噩梦,当在围攻“白色城堡”时失败之后,两人在城堡的浓浓大雾开始了不同的选择:霍加逃离而奔向他的想象城市威尼斯,威尼斯人则作为替身留了下来继续霍加的生活……一群海盗,一位奥斯曼国的帕夏,一个东方文明中的占星师,演绎的是一则东西方认同的寓言,而谁是那个本来的自己也没有了意义。
《白色城堡》:现在,我和你一样了
“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名为《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的书,在书中,“他”准备把我一生的故事呈现给“他”的意大利读者,从我在埃迪尔奈的童年开始,到“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并且还将辅之以“他”个人对土耳其人的特性的评价。
——《11》
埃迪尔奈的童年,是他被写进书里的起点,而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则是他在书中的最后一页,是的,当最后一页合拢,他变成了“他”,一个活在引号里的人,一个取代我的人,一个被历史虚构的人——也是虚构历史的人,而不管是被历史虚构还是虚构历史,不管是我还是“他”,都从关于战争、关于争夺,关于陷落的历史中走进了小说里,走进一本名为《我所熟知的土耳其人》,而当活在引号里的“他”成为土耳其人,其实意味着我成为土耳其人,被置换的身份,被置换的人生,被置换的人称,以及被置换历史,仅仅在一本小说里就可以合为一体?
小说似乎正在从历史中抽离出来,而所有小说都有一个被期待的位置,那就是读者,“我向那些不喜的读者们表示歉意,因为我给我的书加上了下面这一页”,加上去的这一页里,读者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看见了我以及我的影子,看见我以及我的孩子,看见了我以及我的“他”,那里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包容了羞耻、怒气、罪孽和忧伤,包含了痛苦、羞愧、厌恶和欣喜,甚至,当读者变成访客,来到“他”的家里,“他”会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详细谈及作为影子的我,告知关于一名土耳其人的生活,并且把一生的故事呈现给意大利读者。
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确定,阅读小说的读者确定,那么背后的作者显然可以隐退,我就在故事的身后,就在历史的背面,我看到他带着强烈的欲望翻阅我的书,终于看到了“他”的那一页:
桌上一只镶嵌珍珠母贝的盘子中放着桃子与樱桃,桌子后方有一张垫着稻席的睡椅,上面放着与绿色窗框同样颜色的羽毛枕头。现已年近七旬的我坐在那里。更远处,他看见一只麻雀栖息在橄榄树和樱桃林问的井边。再往远处,一架秋千被长索挂在核桃树的高枝底下,在似有似无的微风中轻轻摆荡。
当我作为一个作者看到他翻阅那一页书的时候,我到底是隐藏在身后的作者,还是另一个看见历史的读者?那一页里的我,到底是谁,看窗外的他又是谁?而那些桃子和樱桃、睡椅和枕头,以及橄榄树和水井,秋千和微风,是在被看见的小说书页里,却也出现在历史的某个场景中,在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在城市陷落和武力攻打前夕,在我的埃迪尔奈童年开始之后,却在“他”还没有离开我之前,所以小说中的场景以一种复原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历史之中,而所有这一切的引号、置换和虚构,就是为了在历史的真实场景中看见虚幻的东西,而把土耳其人的生活告知意大利读者,显然是是要让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是要欧洲中心拓展亚洲视野,是要在置换甚至更替的故事里找到历史的真正作者。
“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这是历史还是小说?从威尼斯到那不勒斯,最后被土耳其人截获,无论是历史还是小说,都是东西方之间冲突开始的描述,而“我们”作为一种提供体验感受的人称,自然带入到一个非历史的世界里,而从我们之中脱离出的我,又带有了更多的主观视角,我的整个人生将由此发生改变,我在猛烈的炮火中竖立了白旗,我曾经告诉船长我会号脉和验尿,而最后,我甚至和土耳其人建立了联系,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被苏丹看见,甚至最后被关进了沙德克帕夏的监狱。
其实看起来是和欧洲其他人一样,失去了自由,但是我却在这场冲突中保全了自己,甚至因为自称是医生让帕夏的病痊愈,得到了他的保护。当船长被火刑处死,当鞭打奴隶的水手被割下耳鼻,欧洲文明似乎在东方世界里遭遇到了打击,但是我之存在,我之得救,却成为这场冲突中的一个特例,是什么拯救了我?当然是知识,关于身体的知识,关于疾病的知识,虽然里面有着欺骗,但是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不是他们拯救我,反而我以知识拯救了他们。
知识和理性,代表着西方文明,即使在历史的某一个段落里,这些知识充斥着谎言,但也以奇迹的方式治愈了疾病,这是一种巧合?“现在我知道,多年来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当巧合找到了合理化的意义,就会变成奇迹,而我作为一名意大利人,就在这东西方的冲突中,让巧合变成了奇迹。奇迹的发生是因为我找到了相似的人,在没有活在引号之前,他叫霍加。“我和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那个相似的男子曾经出现在我在船上的梦里,“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其实,置换已经开始了,在开完一本书之后陷入到相似之我的梦境之中,即使醒来,那本书也开始了第一页的书写。
而霍加也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到我的书页里,甚至可以说,是我进入到霍加的书页里,通过梦境,通过镜子,最后通过现实。我一年没有照镜子,但是看到霍加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我自己,而在那个睡梦中,我变成他的速度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他以我的身份去了我的祖国,和我的未婚妻结了婚,婚礼上没人发现他不是我。而我则穿着土耳其人的服装,在角落里观看庆祝活动,遇到母亲及未婚妻时,尽管我流着泪,但两人却没有认出我,都转过身离我而去了。最后泪水终于让我从这个梦中惊醒了。”其实是令人不安的,其实是充满风险的,其实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一面镜子、一个梦境和一种现实,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我必须是他,他必须是“他”。
一个以祖辈的名字命名的男人,一个土耳其王宫里的人物,一个拥有我这个奴隶的主人,霍加却需要实现历史的突围,他和我相似,为什么在镜子里、在梦境中反复变成我?为什么把我当成奴隶却要和我保持良好的关系?只不过他要从我身上获得知识,想要获得实验结果获得武器制作方法,最后想要掌控苏丹。是的,知识可以开启另一条道路,有别于权力和地位,从托勒密的宇宙志原理到行星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从木筏上的烟火发射,到和火龙展开的激烈攻击,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潮流的成因,到北方寒冷的国度里礼拜与斋戒时间的对应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中,霍加开始慢慢接近苏丹,开始慢慢控制苏丹,他与苏丹谈及的主题,完全被纳入到这个知识体系里,蚂蚁们有规律的生活中有哪些是值得去学习和理解的?磁铁的磁力从何而来?星星这样旋转或那样旋转有什么重要性?异教徒的生活中,除了不信教之外,还能不能找到值得了解的东西?
但最重要的是能否发明出打败异教徒的武器?那时霍加会走到桌子旁,在纸张上为这种武器画下设计的图样,长炮管大炮、自行引爆的发射装置、让人想起恶魔巨兽的武器。正是被这样的知识体系吸引,苏丹任命霍加为皇宫星相学家,而且成为自己最信任的臣僚,开始关注宇宙命运的安排。苏丹祖母的叛乱,帕夏的谋反,在苏丹的掌控下平息,而霍加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而在这个知识体系中,霍加完全是从身上获得的,不管是我提供的那些方案,还是我为武器设计作证,无论是我关于宇宙的逻辑性探究,还是关于烟花的各种设计,可以说,我就是象征着知识文明,所以,霍加要变成和我相似的人,甚至要成为我。
但是霍加和我,通过镜子成为彼此的镜像,通过梦境相互交错,却是脆弱的,一方面我笃信的是基督教,从不会为了求生而放弃信仰,即使面对帕夏斩首的威胁,我依然如我,而最后帕夏还是妥协了,因为宗教的冲突似乎在知识世界面前,可以暂时搁置在那里。但是当那一场瘟疫爆发的时候,这样的搁置变成了亵渎,甚至对于霍加来说,变成了对于信仰的颠覆。城里爆发瘟疫的时候,我的精神彻底垮了,而霍加却说自己不怕瘟疫,因为在他看来,疾病是真主的旨意,“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死,那他就会死。”他把接触学校里孩子的手向我伸出来,当我退缩的时候,他却兴高采烈地和我拥抱,他说他想教会我什么叫无畏无惧。但是,那一天他却说,他开始害怕瘟疫,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淋巴肿块,虽然极力想证明是蚊虫叮咬所致,但是当他在我的身上找不到相似的肿块时,他忽然开始恐惧。
他有着淋巴肿块,而我没有,这无疑把相似的我们隔开了,无疑把镜中之我、梦中之我和现实之我,甚至知识之我,都从他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所以在这种相似危机中,霍加开始主动变成我,曾经我是他的奴隶,现在仿佛他变成了我的附庸:又一个梦,我的躯体离我而去,联合着一个长得像我但是脸孔却被阴影遮盖的人;又一面镜子,“来,我们一起来照照镜子。”是的,我们又开始走向一体,“我之所以为我”的标题下面是关于回忆,关于人格的故事,霍加命令我写下他想知道的故事,无非是要在镜子这种外表相似的镜像之外,要通过思考去观察思想的内在。
我之所以为我,其实是他之所以为我,而当那个肿块出现在霍加身上的时候,他在害怕之余却兴奋地说:“我们会一起死!”在对疾病的害怕、对死亡的恐惧中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现在,我和你一样了。我已经知道你有多么的害怕。我已变成了你!”实际上不管是“我之所以为我”的书写,还是“我和你一样”的害怕,对于霍加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背叛,何尝不是一种冒险?其实对于我和霍加来说,只要交换衣服,只要把我的胡子留出来他的胡子剃掉,就可以互换身份,就可以相互取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仅仅是外表世界的置换,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如果没有信仰的改变,其替换的意义又何在?
而知识、宗教,似乎并不是仅仅已有的一切,它根植在内心深处,根植在文明体系中,根植在东西方的历史里,简单的置换只能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我终于离开了皇宫到了黑贝利岛,为的是逃避瘟疫,和那些基督徒一样,暂时找到了一种归宿,但是霍加终于还是找到了我,把我又带回去,“他坦白表示,他需要我的知识。”我在回来之后像素单建立了许可证制度,慢慢的瘟疫得到了控制:“一个月后的星期五,霍加被任命为皇室星相家。他的地位甚至比这更高:苏丹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周五礼拜,庆祝瘟疫结束,整座城市的人都参加了这一庆典,而霍加就紧跟在苏丹身后。”
霍加看上去有了权力和地位,但是这种权力和地位显然是一种东方式的存在,也就是说,霍加用我的知识成为我,却无法变成另一个我,而当苏丹开始关注动物是否有灵魂,关注哪些会上天堂哪些又会下地狱,关注珠蚌是公的还是母的,关注每天早上上升起的太阳是新的太阳,“听了这些内容,霍加绝望地离开了。他表示,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苏丹很快就会脱离他的掌握。”当苏丹下令我和霍加研制武器的时候,其实不是霍加影响苏丹,而是慢慢长大的苏丹开始控制知识。六年的武器研究,最后变成的是那一个叫做“真实的战争机器”的东西,它画在图纸上,它运输在途中,最后它却陷入到泥地里,“在好奇的人们困惑而惊骇的注视下,这个武器笨重地动了起来。胜利的呼喊声中,它向一座想像中的堡垒发起了进攻,摇摇晃晃地出发射炮弹,然后停了下来。资金继续从各个村庄及橄榄园涌来,但旦因为费用太高,霍加只好遣散了我们召集来的人员。”
埃迪尔奈战役似乎没有打响就走向了结束,苏丹最后没有来找我们,而我们只剩下自己。我们自己,也已经不再是合二为一的集合,苏丹让我们看见的是另一个模仿者,像我又像霍加,却又不是我们,这是第二种置换,“我越来越相信,不知不觉中,我的人格已自行脱离,与霍加的人格合而为一,反之亦然;而苏丹借着评估这个想像的创造物,已经比我们本身更了解我们了。”我们不像我们自己,那么所有的知识和宗教,所有的权力和地位还有什么用?甚至在我和霍加之间,那种相似也面临着解体,我在梦中遇见早已不认识我的母亲和未婚妻,其实会变成现实;而霍加多年未公开露面,几乎已被人遗忘。
我不再是我,霍加不再是霍加,或者说我已经是另一个霍加,而霍加也是另一个我,又是一个梦,当我们身处威尼斯化装舞会的时候,却像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宴席之上,而我看见了霍加,意味我还是我,但是当他把面具摘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面具底下的就是我——我年轻时的样貌。“那个不管在别墅里、在宫中、在城里如此频繁出现于苏丹身边的人都是我,现在他们嫉妒的人是我!”我成了霍加,我变成了土耳其人,我的童年从埃迪尔奈开始,实际上,我脱身而出变成“他”,是因为我无法真正走进伊斯坦布尔,无法走进另一种文明,无法把自己当成历史中的别人,就像那山顶上的白色塔楼,士兵们永远无抵达那座白塔,它是一个存在着的知识、宗教和思想,却又远离我们,远离战争,远离权力,也远离征服。
而其实,在那艘被土耳其人截获的船上,我就开始变成了“他”,我从梦中构思他,在书中书写他,在镜中找寻他,无论是霍加,无论是模仿者,无论是我在梦中看见的我,在镜中见到的自己,都是一种自我的虚构,“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而且,或许这些耐心的读者会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认为这位在读着他的珍贵书籍之际放弃自己人生的年轻人,他的故事会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那个他出现,我给了他名字,给了他“我之所以为我”的故事,给了他知识和信仰,给了他害怕瘟疫和死亡的思想,“那些日子里,我想将心力放在自己创作的其他故事上去,这些故事不是为了苏丹,而是为我自己而创作的。”
而当他被书写,我便从历史中逃离出来,“在苏丹的军队开赴维也纳之前,在阿谀奉承的小丑及接替我的皇室星相家因狂败被斩首之前,在我们那位热爱动物的苏丹遭到废黜之前,我就逃到了这里,来到了盖布泽。”我成为陌生的一个人,一个只拥有过去的事和将要做的事的人,而所有一切看起来像是小说又像是历史的故事,早就变成了虚构,就像有人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
是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却让我变成了读者,我之抽离,我之陌生化,我之读者,在历史中我变成了影子:“因此,我回到了这本有着自己身影的书,想像一些好奇的人会在我们死了多年或许是数百年后阅读此书,更多地幻想他自己的而非我们的人生。”而当1982年有人打开一本书的时候,他自动就会变成我,变成作者,变成书写另一种历史和小说的人:“选择这个书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此书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献词的读者可能会问,其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