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28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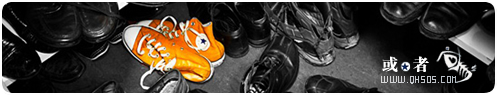
雷迅、阿累、但非、雷雨声、凡布衣、千虑失、柳叶刀……这些笔名的背后,是一个更真实更具体的名字:徐迅雷,与这个名字连在的是一个更为人熟知的标签: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或者在徐迅雷自己看来,前一部分代表着某种理想主义,而后半部分则是一种生存现实。
这两种身份是不是也是一种割裂?只是在一个下午的讲解中,这种割裂似乎被深深隐藏起来,只是在偶尔的放大中,在互动和谈笑中,你能触摸到一名媒体从业人员在理想与现实面前的困惑和无奈,甚至是妥协。“百姓立场,公民写作”,如果解读从这一句话开始,整个午后应该洋溢着某种人文关怀的温热。作为都市快报的时评写作者,徐迅雷以一种“评论专业主义”的态度针砭时弊,发出媒体的声音。他用言之有物、言之有识、言之有情、言之有序、言之有文等方面构建他的媒体评论舆论场,这似乎更多代表着评论写作的教学意义:如何积累素材,如何写好时评。
不论是《世界宪法全书》、《沉思录》、《旧制度与大革命》、《寻路中国》、《江城》、《炎黄春秋》、《南都周刊》等阅读素材的推荐,还是评论写作中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三段论、“起、承、转、合”的四段轮、“叙、阐、引、议、结”的五段轮,徐迅雷更多在技术、器物层面介绍媒体时评的写作,而这些方法论阐述只是让他的个体意义具有媒体属性,正像他在那本《只是历史已清零》的杂文著作上的自我介绍一样:徐迅雷,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丽水学院客座教授,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入选《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1949-2009)》,是《杂文选刊》评点的“当代杂文30家”之一。已出版《只为苍生说人话》、《让思想醒着》、《这个世界的魂》等著作。
 |
| 徐迅雷的杂文集 |
但是这不是全部,甚至这只是一个书面化的徐迅雷,而从他个人经历来说,这些“成果”也未免有些“扁平化”。“知道‘不要什么’比知道‘要什么’重要。”也许正是这句启示,徐迅雷从2001年开始对自我进行了颠覆,他曾经留校6年,后到政协干了6年,再后来下派到一个江南小镇做镇委书记,而最后的决定便是对这句话的实践:弃政从文,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感到还不干自己感兴趣的事,这辈子要废了。“感兴趣的事”,从一开始来说,或者只是关于阅读,关于写作的自我定位,但后来这样的人生转折便像眼前的这本书的标题一样:清零。
“清零”代表着重新开始。每年花费2万元买书,用10个小时的阅读和积累来完成2个小时的写作,这是徐迅雷工作的一些感悟,但其实这些感悟也只是为了在媒体上谋得一个生存的机会,但是作为媒体评论人,徐迅雷的“清零”似乎带有太多了的理想主义。和“百姓立场,公民写作”一样,“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也并非是他对自己写作风格的概括,苍生和帝王、人话和赞歌,也都是在一种对立状态下,尤其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下,这两种趋向的存在并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二元论,相反,作为两个舆论场的对立,徐迅雷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必然是充满矛盾,甚至是退让和妥协。
这便成了我与他对话的一个问题:在“凡布衣”的个人标签和当下媒体标签下,如何保持一个开放的个性和自我,或者说,在“评论专业主义”和媒体体制下如何协调?他依然带着微笑,依然有着一种人文关怀的温热,甚至在他说出“戴着镣铐跳舞”这样的现实困境的时候,在他脸上也没有多少的“断裂”的感觉。但是正如他说,必须先生存,必须知道媒体从业的风险在哪,所以即使遇到苍生和帝王、人话和赞歌的矛盾,也依然需要知道高压线在哪,知道底线在哪,在表达个人情绪的时候,更多是为了发出媒体的声音,更多需要选择。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时机,徐迅雷的这种“替换”也是媒体时评作者在当下的一种智慧选择。
但是智慧也仅是化解风险而言,但是在本质上也依然是一种妥协,或者正如徐迅雷给自己定义的双重身份:职务写作者和非职务写作者,前者是生存是工作是首席评论员,而后者是爱好是人文是追求。历史已清零,但是对于现实而言,永远没有清零的机会,永远会面对一个扬汤止沸、掩耳盗铃的媒体现实,所以他的生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他名字的一种戏谑化解读: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不管是“只为苍生说人话”的理想主义,还是“不为帝王唱赞歌”的英雄主义,徐迅雷也都只是提供了在断裂时代的一种个体生存标本。
“太阳从来无意担负下雨的责任。”徐迅雷引用《沉思录》里的这句话,或许也是一个遥远的理想。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