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28《走出黑暗》:这个手势在创造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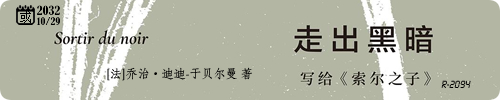
这是光与影、黑与白、清晰与虚化的视觉保存,直接见证了这些影像所处的情境,就像“幸存者”一样。
光与影、黑与白、清洗与虚化的视觉保存,是四张照片,是四张1944年8月拍摄的照片,是四张由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五号焚尸场的纳粹行刑队员拍摄的照片,当这些被保存下来的照片被看见,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将其称为“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不仅刺激了《索尔之子》的导演拉斯洛·奈迈施,也刺激了于贝尔曼——是作为《索尔之子》的观众的于贝尔曼,也是曾经在照片中探讨了大屠杀不可再现与不可想象的于贝尔曼。
“强烈的刺激”由此形成了不同层面的受体:作为看见了照片并导演了《索尔之子》的拉斯洛·奈迈施,作为《索尔之子》电影观众的于贝尔曼,和作为曾经照片研究者的于贝尔曼,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无数从这部电影中看见“大屠杀”历史和影像的观众——“强烈的刺激”形成的这种不同圆圈的反映是不是正是大屠杀这个“我们之间的黑洞”带来的思考?是不是正是我们如何“走出黑暗”显现为一种光明的思考?要“走出黑暗”,必然是因为我们在黑暗之中,阿多诺说:“奥斯维斯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为什么是野蛮的?为什么写诗是野蛮的?因为大屠杀制造的黑暗是“我们之间的黑洞”,而“奥斯维辛之后”那些反思甚至歌颂当下的诗歌,在历史之外、在暴行之外,已经是无力的存在,甚至开始随波逐流,这就是阿多诺所说的“不可还原”,但是当写诗是野蛮的,也就意味着必须对这野蛮的行为进行批判,这就是“完美的黑”对大屠杀的一种可能回答,“如果要在最黑暗和最极端的现实中求得生存,艺术作品如果想避免成为纯粹的可以出手的安慰品,就必须同化在那种现实之中。”
阿多诺抛弃了无视黑暗背景的当代艺术,他提出对现实的“同化”其实就是在完成对“完美的黑”的书写,“从内容上看,完美的黑是最深刻的抽象趋向之一。”而于贝尔曼对于这个“黑洞”的反思是:面对它我们可以做什么?是在内心世界埋下炸药还是试着返回从而让它走出黑暗在光亮之下显现?而对于这个问题,在《索尔之子》没有问世之前,于贝尔曼就在那四张“光与影、黑与白、清晰与虚化”的照片中发现了这“完美的黑”。《四张从地狱抽出的底片》一文收录在于贝尔曼出版于2003年的《影像战胜一切》一书中,他在书中面对这四张照片,提出了不可想象之想象的可能性问题,“为了了解,我们必须自己去想象。我们必须去想象1944年夏天的奥斯维辛地狱。”似乎在历史之外,我们已经不能以任何方式去想象,我们选择了躲避和遗忘“那种可被想象之物”,我们应有的态度,就是把“去想象”看成是文字与影像的负债,“为了我们,从他们那些令人痛心的真实经历中抢夺出来的。”
在1944年8月,就有人选择了面对,甚至选择了以死亡的方式将它们变成视觉的保存,照片成为了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它们是“未知摄影师”拍摄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五号焚尸场的树篱屏障》《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五号焚尸场》和奥斯维辛的纳粹行刑队员拍摄的《在奧斯维辛集中营第五号焚尸场毒气室前面的露天焚烧坑中燃烧的尸体》和《被推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五号焚尸场毒气室的女人》——前两张照片由德国未知摄影师于1943-1944年拍摄,后两张则是由纳粹行刑队员在1944年8月拍摄,它们现在都收藏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国家博物馆。于贝尔曼将它们看成是“从地狱抽出的底片”,当然是一种黑暗的影像:首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行刑队员在这个黑暗的地狱里,他们本身就是囚犯,他们的任务是焚烧其他囚犯并处理这些尸体,但是他们也面临着被抹杀的命运,1942年7月成立之后一共有12支队伍被抹杀,“作为开始,随后的队伍会去焚烧前一组人的尸体”;他们在这样的黑暗地狱中却保存了“证人的即将消失与证词的不可描述之间”影像,被限制在“地下孤立的小牢房里”的他们偷来了相机,然后组织了一场“集体性的的监视”,故意制造了第5号焚尸场屋顶被破坏需要修理的借口,然后藏在水桶底部的队员在焚化炉的前方拍摄了照片。
“这个暗室的可怕悖论是,为了从水桶中取出相机,调整取景器,将相机靠近他的脸,并用相机拍摄第一个图像序列,拍摄者必须要藏于毒气室中。”毒气室的受害人尸体还没有完全被清理出去,拍摄者走回黑暗处,“他所站立的倾斜与黑暗的地方保护着他。”这个拍摄者据后来的资料显示他的名字是“阿历克斯”,曾是希腊抵抗运动的活跃分子,被捕后成为第1号焚尸场的行刑队员,担任“锅炉工”。在黑暗中拍摄黑暗,这就是这些照片“走出黑暗”的危险,终于它们还是通过一管牙膏被送了出去,牙膏里的纸条上写着“将胶卷尽快送出去”,照片最后到达了克拉科夫的波兰抵抗运动。从地狱里抢夺一张照片,从黑暗中让图像走出黑暗,于贝尔曼在这篇文章里把这四张照片看成是“不顾一切的影像”:“不顾及需背负的风险,不顾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地狱。”而在看完《索尔之子》之后,他把这些见证了黑暗的视觉保存,称为“幸存者”——当那些囚犯在纳粹的暴行中死了,当那些行刑队员被一批批抹去,只有这四张照片幸存了下来,这样的“幸存者”不仅仅是见证了黑暗,更在于通过我们“去想象”最终“走出黑暗”:
这个情境的恐怖(一边是纳粹行刑队刚刚从毒气室运出来的尸体,一边是被推向下一批炼化炉的赤裸的女人)、这个决定的紧急(在忙乱中安排时间以提取视笕证据),以及这个拍摄动作所面临的危险(在党卫军死亡威胁之下,从他的口袋中拿出照相机,端在眼前以瞄准这个宛如地狱的世界的某个场景),他怎样做出判断让这一切最终沉积为影像?怎样在留给我们照片表面,聚集了最细微的感官?
照片没有所谓的构图,没有所谓的用光,但是它们也是阿多诺所说的“完美的黑”,而当拉斯洛·奈迈施拍摄了《索尔之子》,更是影像再现黑暗并走出黑暗的方式书写了“完美的黑”,“您没有忘记黑暗,但您以抽象的形式让黑暗显现。”在剧情上,索尔就是在实现着“走出黑暗”的想法,“走出黑暗,因此对于索尔来说就意味着尝试一点一点地把死去的孩子从解剖试验品中拔出来,把他从焚尸场这个残暴的岩洞中挽救出来,避免把骨灰散落在维斯瓦河。走出黑暗,在这里意味着抵抗死者之不存在:为了让死者存在,这需要一场仪式、一个合适的祈祷、一位犹太教士,尤其是一场有尊严的下葬。”对于索尔这样一个纳粹行刑队员来说,走出黑暗就是拯救“孩子”,这是疯狂的,这是荒诞的,“正因如此他才是分裂的,不仅从他自身中分裂,而且也从他周围的所有其他人中分裂。”而在影像表达上,于贝尔曼认为奈迈施通过场面调度的“现实主义”完成了本雅明所说的“在一个视角和光学发挥作用的世界”的批判:一方面电影中的镜头聚焦的是“纪录的精确”,是历史现实主义的再现,另一方面则是寻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距离”进入到了距离的辩证中。
| 编号:Y23·2250318·2269 |
“这是您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电影特色。”于贝尔曼在写给奈迈施的信中就说到这是一个“现象学问题”:“清晰的区域就像一块薄片:它就像可见空间的切片,但是它的有效间隔,它切开的位置却是非常薄的。”影像首先是模糊的,就像1944年的那几张照片,处在恐怖、紧急和危险之中拍摄的照片从不是被“固定”的,而且影像里本身就带着让距离扭曲的恐惧,而在电影影像中,奈迈施在清晰与模糊的关系中制造了知觉疾病,这就是他所说的“惊恐-影像”。当然,黑暗世界除了影像本身之外,奈迈施还要把这种黑暗具有可见性,那就是与观众相遇,给于贝尔曼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纳粹行刑队员与集中营里的其他人是分开的,他们在工作结束几个月之后被杀害”,在字幕卡概括了纳粹行刑队的基本情况后,银幕陷入了黑暗和几秒钟的寂静,然后出现了声音,那是大自然中的鸟鸣声,是放飞自由的无辜声音,然后是光亮照见的风景、树干以及在地上模糊前进的暗点。森林里传来的声音、光亮照见的风景,都是作为黑暗结束后的呈现,但是这些声音和光正是为了表现寂静和黑暗,于是,“一个来自黑暗的影像,它从阴影或模糊中出来,将与我们相遇。”
于贝尔曼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在观影的过程中,他好几次都忍不住想闭上眼睛,在黑暗的电影院里,闭上眼睛是为了适应黑暗?还是在“去想象”中寻找黑暗之外的光亮?而实际上,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看见奈迈施的电影,是一次对黑暗的相遇,也是于贝尔曼在“电影本身闭上眼睛”时返回了黑暗——也许这才是与黑暗相遇产生的“强烈的刺激”,“您的(虚构)故事从黑暗开始,它本身携带着秘密,只不过是带向光明。”所以于贝尔曼在探讨“走出黑暗”的意义时,完成了关于“黑暗”的多重情景:大屠杀的历史是“我们之间的黑洞”,它是吞噬着我们记忆的黑暗;行刑队员在恐怖、紧急和危险的黑暗中拍下了照片,这是黑暗的证据;奈迈施通过影像讲述了一个黑暗地狱中的故事,历史现实主义意味着走进黑暗;电影在黑暗的电影院里上映,用黑屏和寂静制造屏幕上的黑暗,而观众“忍不住想闭上眼睛”返回到黑暗之中。从历史到“幸存者”的照片,从照片到电影,再从电影到影院和观影者,黑暗无处不在。
但是黑暗之存在是为了走出黑暗,走出黑暗的意义就是“让黑暗显现”并最终完成“完美的黑”的书写。回到电影,于贝尔曼认为索尔“走出黑暗”的行动首先是疯狂的,“不仅限于用车拉着数不清的尸体,而且也是拖着一个死者的意志。”所以他认为索尔是一个分裂的人,拯救一个死者让他从自身中分裂,而且从周围所有其他的人中分裂,分裂的意义就是超越绝望,因为行刑队员是要死的,死是必然,无论是囚犯还是队员,“我们已经死了”,索尔说,但是死亡之后是什么,就是对绝望的超越;我们已经死了,但是还要去拯救死去的孩子,这是一种意志,行动本身就是重启、强化和释放这种意志;索尔要为死去的孩子进行一场葬礼,要为他找到安葬的土地,于贝尔曼认为这种疯狂的背后是“对良知的凝视”,“体验到对他的同志的凝视,以及对电影观众的凝视——这种疯狂拥有故事的结构,一种在深处非常文学化的神秘客体的结构。”
超越绝望、重启意志、对良知凝视,这就是索尔“走出黑暗”的行动,奈迈施之所以让索尔在黑暗中走出黑暗,就在于构筑了一个“死亡空间”,按照布朗肖的说法,“当俄耳甫斯向着欧律狄刻下降,艺术就是能够打开黑夜的力量。”索尔作为“幸存的被审判者”,就是完成了这个“文学”的存在,最后的笑容、森林、绿色,都是越过黑暗而显出的光明,是“完美的黑”所书写的奇迹——毋宁说,是艺术打开了黑暗。一方面,索尔作为“难以挽救的垂死者”,在“我们已经死了”之后为了死去的孩子,无疑就是在完成一个标准临终之人的手势,“这个手势在创造儿子”;另一方面,“阿历克斯”们在黑暗中保存黑暗的证据,“奈迈施”们在黑暗电影院里让黑暗显现,无疑都是这个打开黑暗的人,打开,然后去想象,去抵抗,去思考,去记录所有人类的“手势”:
从这个故事出发,从这部影片出发,索尔全部的权威,是迎着这个世界及其残酷性逆流而上,把所有的碎片创造成存在一个孩子,而他其实已经死了,以让我们自己能从这个残酷故事的黑暗中走出来,能够从历史的“黑洞”中走出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