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22《塔可夫斯基:在电影中祈祷》:不朽的诗与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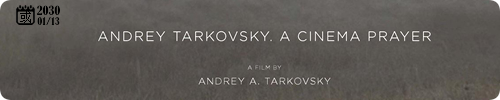
心底吹起一缕清风,飞吧,你轻盈地飞!胶片上的爱情,抓住了灵魂的衣袖,遗忘,像一只鸟偷食谷粒,那又如何?至少没有让风吹走它们,你虽死犹生,不是完全活着,而是百分之一地活着,无声无息,恍然如梦,如游荡在田野上一般。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一起甜蜜,清晰、生动,重复飞行,而镜头的天使会将你包裹在他的羽翼下……
——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摄影》
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的文字如诗一般流淌,这是对自由的高歌;病魔缠身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病房里放飞了一只小鸟,这是对爱的礼赞;安德烈·A·塔可夫斯基的镜头下,是俯视的城市,是辽远的天空,是父亲的那些私人照片,这是对生命的怀念……祖父的文字、父亲的电影和照片,儿子的纪录片,组成了塔可夫斯基三代人的“家族”影像,它也以“谱系”的方式构成了时间的一种绵延,叙说着特殊意义的“祈祷”。
无疑,在三代人的所唤起的家族记忆中,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无疑是中心,他以向前和向后的方式构筑了回忆和展望部分——安德烈·A塔可夫斯基第一章《明亮的日子》便是将祖父的文字和父亲的回忆结合在一起,“茉莉花旁有一块石头,石头下面藏着宝藏……”引用的这句话就来自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的文章《明亮的日子》,茉莉花和石头翻开的是塔可夫斯基童年的记忆,照片中那个在日光中翻着书的小孩就是塔可夫斯基,他像是在阅读父亲那些泛光的文字,“艺术家总是从童年中汲取营养,他的童年决定了他的艺术会是什么样子,我的诗人父亲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父亲的巨大影响就体现在那些文字构筑的诗意中,它们并不会因为父亲的离开而消失,但是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父亲却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对于父亲最初的记忆来自我18个月的时候”,记忆里是一间开阔的露台,是一条小径,是一排栏杆,是几步台阶,是一大片丁香,是玩着的铝锅盖,之后便是天上的声音,一架飞机从头顶上飞过……”那时一家住在莫斯科旧城区,但是这些记忆都是片段的,三岁那年,父亲深夜回来,“他想把我带走”,但是母亲拒绝了,父亲从此就没有再回来,而母亲照顾自己的妹妹,“没有母亲,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导演……”
| 导演: 安德烈·A·塔可夫斯基 |
关于童年的记忆,关于父亲和母亲的分离,塔可夫斯基虽然并没有真正生活在“明亮的日子”里,但是父亲的诗歌和母亲的爱给他留下了最为珍贵的东西,这也是塔可夫斯基一生在找寻并实践的东西,在电影《镜子》中,母亲的目光穿过树林延伸到遥远的地方,那就是一种童年的投射。从第二章《开端》开始,安德烈·A·塔可夫斯基开始叙述父亲投身电影创作的故事,“开端”中的短片《压路机和小提琴》以及长片《伊万的童年》,都和孩子有关,都和童年有关,但显然《伊万的童年》标志着塔可夫斯基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那就是战争,“战争没有赢家,我们赢了也输了,因为我们参与了战争……”这部根据博格莫诺夫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塔可夫斯基接手的时候,另外导演已经拍摄了一半,但是塔可夫斯基重新按照自己的思路拍摄,“这是一个寻求私人角度的诗意作品……”
塔可夫斯基虽然认为这部电影是一种“私人”角度,但是他所关注的是人类的情感,之后的《安德烈·卢布廖夫》表现的就是反抗主题,“真正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信徒……”在电影中塔可夫斯基探讨了宗教和文化以及它们对人性的影响,甚至在他看来,艺术也是一种宗教,“影像本身就带着一定的神秘性,它完全是形而上的……”正是因为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反抗”,当时的电影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反历史”“反俄”的电影,电影引起的争议也让塔可夫斯基遭受了“蒙难”;在《飞向太空》之后,塔可夫斯基拍摄了《镜子》,这部电影一样引起了争议,《潜行者》是塔可夫斯基认为是“我所有电影中最成功的一部”,因为它表现了“脆弱的力量与灵魂深处更高力量的联合”,但是这部电影也让塔可夫斯基遭受了打击,他被迫离开祖国,和家人分离,1983年的《乡愁》就是在意大利拍摄,而三年之后的《牺牲》也是在瑞典哥特兰拍摄,这也是塔可夫斯基生命中的最后一部电影,他在与祖国的分离中承受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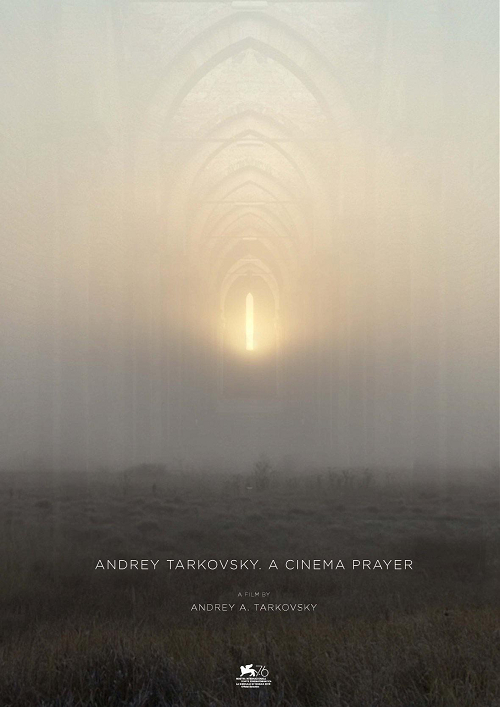
《塔可夫斯基:在电影中祈祷》电影海报
但是无论是不公还是痛苦,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诗意,坚持自己的爱,在他看来,“邪恶越占上风,就越需要进行艺术创作,因为艺术就是祈祷。”祈祷是怀着对宗教和艺术的虔诚,是对人类之痛苦的救赎,它们化作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真正的影像,是礼物,是祷告,是献给造物主的,上帝创造我们,我们创造艺术,那时,是我们和上帝最接近的时刻,这是人类最无私的行为,是自我的祈祷。”在自我祈祷之外,则是为他人祈祷,“如果我的祈祷成为他人的祈祷,那我的艺术也成为了他人的艺术,然而,在今天,这种思想已经走形了。”带着遗憾,带着无奈,更带着伤感,塔可夫斯基知道最后死去也没有回到祖国:1986年12月29日,距离新年还有两天,罹患癌症的他在巴黎逝世,这位苏联最富诗意的电影导演走完了他54岁的生命,他的身体永远留在了俄罗斯之外的土地上,他最后的葬礼在巴黎一所东正教教堂举行,这仿佛是这个漂泊的游子最后得到的安慰,因为他在终极的归宿意义上回到了自己的家。
“如果我不回俄罗斯,如果看不到故乡,我就会死。”《乡愁》中的索斯诺夫斯基曾经这样说,塔可夫斯基在生命最后时刻也许一直萦绕着这句话,但是正如他对于祈祷的理解一样,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精神的重生”,他在电影中重生,在诗歌和爱的世界里重生,就像父亲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在《摄影》一文中所说,“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一起甜蜜,清晰、生动,重复飞行,而镜头的天使会将你包裹在他的羽翼下……”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语录
孩子是连接我们这个世界与另一个超验世界的纽带,他们还尚未失去与那个世界的联系,因此孩子的角色对我很重要。
文化无法脱离宗教存在,宗教在文化中升华,文化在宗教中发展。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谜团,那么影像的真实性便是这个谜的一部分。
当你记录下一个影像时,它便带有了严格的内在含义,一种象征主义,但绝不会有一个外在的,可塑造的意义,它是完全形而上的,影像越深邃,越让人难以捉摸,也因此越伟大,它所需要的结构也更为严苛,最崇高而诗意的影像是非常自然的,它并非是理想化的,而是世俗的,因此,当我们谈论某个影像其结构的简洁性时,对我来说,其意味着创作者一手触碰着大地,一手触碰着另一个超凡世界。
符号是可以被解释的,因而完全是反艺术的,影像不是一个猜谜游戏,不是谜题,当谜题被观众解开后,这个符号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它证明了其本身的局限性,若符号是被局限的,他又如何代表无限呢?我们甚至可以说谜题只是代表无限的符号。
我们把自然排除在了电影之外,仿佛它毫无用处,我们完全地排除了它,将我们自己视为主体,但我们不是主体,我们依附于自然,自然远比我们重要,我们本身就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自然是唯一一处有真理在等待着我们的地方。
如果有人问我《伊万的童年》《安德烈·卢布廖夫》《飞向太空》以及我正在拍摄的这部《镜子》有什么共同的主题,我会说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那种想要让人们沉浸在一个高度紧张且缺少情感平衡的角色身上的欲望,而这样的角色最终将打破或坚定他们的信仰和原则。
电影究其本质究其偏好,是由影像组成的诗意的实体,因为它可以没有文字意义,也不一定符合日常规律,甚至连我们所谓的剧作都不是必须的。电影的独特性包含这样一个事实,即电影是用来留存和表达时间的。哲学感知,诗性感知,和文学感知上的时间,它实际产生于,人开始感受到时间的稀缺时。在我看来,十九或十八世纪的人是无法在当下这个时代生存的,他们甚至可能会死于时间带来的压力,而电影从本质上是用来,诗意地解决这个问题的。电影是唯一能真正留存时间的艺术形式,从理论上说,人们可以无止境地反复观看一部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是时间的矩阵。如此说来,那些韵律、长度、节奏的问题,都在电影中展现出他们独特的重要性。因为时间能自我表达,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艺术形式,在其最好且最极致的状态下都是诗意的。
仅仅称达芬奇为画家是很荒谬的,称巴赫为作曲家是荒谬的,称莎士比亚为剧作家是荒谬的,称托尔斯泰为小说家是荒谬的,因为他们都是诗人,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有它自己的诗意,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片段,世界的某一部分是无法用其他艺术形式所理解和体悟的。因为电影可以做到的,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做不到。
哈姆雷特的悲剧并不在于他因为对复仇或正义的执着而最终死去,他的悲剧在于他因为想要修补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而注定的万劫深渊。一个人为了他人而毁灭自己,用那种想要缝合被撕裂的时代的渴望将自己奉献于历史洪流而成为历史进程的催化剂,而在这个过程中,最终不可挽回地毁灭,而这种消失和死亡的危险,为了变革,为了历史的进程而彻底消失的危险,才是哈姆雷特所经历的悲剧。因为他彻底消失,彻底成为了这场历史变革的催化剂。
创作自由,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没有创作自由的概念,艺术就无法存在,它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例如,人们无法严肃地讨论创作与创作不自由的环境中的不完全成功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的工作环境缺乏自由,那很肯定,我们的作品并没有完成。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考虑的,应该只有作品本身。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艺术作品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它们是在表现其自身表现其作者和姿态。
我认为,《潜行者》是我所有电影中最成功的一部,因为它的表达意图与最终呈现的结果是相关联地位,而且不仅如此,还因为,它的结构更为简约,拍摄时采用了很少地位表现手法与技巧。而且很显然,《潜行者》也体现了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过去几年间的处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可以说是真正遭受了打击的人,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仍然具有那种骑士精神。对我来说,这是一部表现脆弱的力量的作品,对精神力量的信念让这个觉得诞生。这部电影的主题在于一个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行为来自他的灵魂深处,来自一种与更高力量的联系。
我一直在想,行为可以是荒谬的,没有意义的,不现实的,做不实现的事对我来说是一种超脱的精神的标志,它是无私的象征,因为其他看法,因为这个世界的构成方式,无法创造一个有精神力量的人,但那种力量会让他以一种脱离现实的方式去行事。
乡愁是一种笼统的复杂感觉,人们会体会到乡愁,即使他留在自己的家乡没有与家庭分开,生活在幸福中的人同样会体会乡愁,因为他会感觉到他的灵魂受到限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蔓延。
人是由爱组成的,爱是一种牺牲的能力,一种把自己赠予他人的能力。如果爱遇到了阻碍,人就会变得扭曲而痛苦,而当你感觉到爱,当你看到这些人为建立起的可怕的限制,这些我们在彼此间设立的障碍时,人就会因此受到折磨。
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精神的演变比物质的演变要少,而我们还在为此付出极大代价。如果人性将死,原因只会是,人类的发展进程受阻,也因为人性未在精神层面上发展,引领人性的是恐惧,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抵抗世界而非寻找方法与世界共存以及与世界建立联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转变为了在彼此身上施加痛苦、怒气、负担与病态。而非把交流转化为快乐,我们抓住了离我们最近的玩具,我们信仰石斧而非慈父的注视,或一个愿望能产生的奇妙影响,而它本可以抵挡铁锤的击打。至于拯救,我们上一次在地球上的经历告诉我们,个人的拯救是有意义的,我们在否定生命与艺术,现在如果没有共同抵抗世上邪恶这样的想法,就没有希望。因此,艺术与拯救的问题,与我们这个时代更息息相关。是急需完成的事。
当我谈到精神性时,首先是指人类对生命的意义所产生的兴趣,这是最基本的第一步。一个人只要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他就不至于在当前水平上倒退,他只会不断向前进化,去问自己为何活着,问我们去向何处,问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意义。而不关心这个问题的艺术或艺术家,根本算不上艺术家,因为他不够现实,因为他回避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问题。只有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真正的艺术才会出现。
与我而言,邪恶和魔鬼,是美德与上帝的缺位,就像影与光一样。邪恶是人与生俱来的,正如美德也是与生俱来的一般,我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战胜自己内心的邪恶。那样,我们就拥有了所谓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战胜邪恶,也可以被邪恶战胜,其中的责任只在于我们自己,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们开始与他人的恶而非自己的恶斗争。
艺术是祈祷,人借由艺术表达希望,其他所有皆毫无意义,一切不表达希望,不建立在精神层面上的事物都与艺术无关。
我不畏惧死亡,死亡并不让我害怕。唯一令人畏惧的,是身体上的折磨。死亡,对于有生命概念的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这一点我敢确定。死亡即将来临的念头并不会令我不适,而且恰恰相反,有时我甚至觉得死亡,那种绝望的感觉,能让我对自由有最为美妙的感受,那是一种我们在生命中未曾体验过的感觉。
一部作品如果能作为一个逝去灵魂的见证,它便会成为杰作,而它也会留向后世,永久流传,如同慢慢消散一般,在身后留下一缕清风。这就足够让一部作品成为天才之作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20]
思前:购书生活的基本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