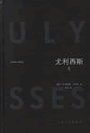2014-01-06 《尤利西斯》:是记忆的母亲们编造的寓言

复活,生命。人死了,就是死了。所谓末日的说法。到一座座的坟墓上去敲门,把他们统统喊起来。……拉起来吧!末日到了!于人都东翻西摸,到处寻找自己的肝哪、肺哪等等一切零碎玩意儿。
黑色的末日,不是死亡,也不是复活,是记忆,是记忆的女儿们编造的寓言,是记忆的母亲们编造的寓言,她们最初在《最后审判的景象》里,在一句诗句的典故里,在一个希腊神话的引用中,可是除了寓言或讽喻,还有那些受灵感支配的想象呢?在“海豚仓,字谜游戏。卜一:上”里?在十八小时的如水的行走中?在音乐响起的赞歌里?还是在最后仅存一个标点的“珀涅罗珀”中?编造的寓言必须接受谁的审判,是神父?是历史学家?是犹太民族的最后一个回家的英雄?或者是荡妇是妓女,是充满情欲的女人?还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可是,谁是格蒂呢?”桑迪芒特海滩边的声音最后是一个问号,它不是“我希望有一天有那么一个男人当着他的面就搂住我亲嘴什么也比不上一次又长又热的亲吻一直热到你灵魂深处简直能使你麻醉过去”那些完整地呈现在内心深处的挣扎和快感,句号是最后的“真的”,最后的“我愿意”:“于是我用眼神叫他再求一次真的于是他又问我愿意不愿意真的你就说愿意吧我的山花我呢先伸出两手搂住了他真的我把他搂得紧紧的让他的胸膛贴住我的乳房芳香扑鼻真的他的心在狂跳然后真的我才开口答应愿意我愿意真的。”而瑙西卡的问号到底能否开启那个灵感的女儿编造的想象?
想象就是末日里的坟墓,一座座坟墓,有着一扇扇门,然后有人敲门有人喊起来,有人东翻西摸寻找自己的肝和肺,零碎玩意儿难道就长在自己的身体里,就在经过坟墓的死亡里?它或者早已经是布鲁姆嘴巴里的点心,或者是圣餐上的面包和酒,在缓乐奏起的时候,肉体和灵魂,血液和创伤,以及有问题的白血球都变成了仪式的一部分,只是地道的基督女已经变成了亵渎神灵的“黑弥撒”,这些以裸女为祭坛的仪式是不是将圣洁的基督女变成了在末日接受“最后审判”的记忆的母亲们?从少女到母亲,从基督女到裸女,被命名为的最后晚餐里是耶稣最后的象征和讽喻,只是当马利根将Christ加词尾变成一个女人名字似的christine的时候,末日回来的生命就在寻找自己那些丢失的零碎玩意儿。
|
| 编号:C38·2130513·0984 |
站在面前的就是斯蒂汾,把乔治五世和爱德华七世复活的光看成是历史的一次荣耀,是不速之客的光荣旅程,可是当梅·古尔丁取代母亲的记忆,取代母亲的死,还有什么可以让马利根免除对那个末日般的死亡的侮辱,下跪而且祈祷,变成了一种逃避,背后是对爱的拒绝还是对历史的背叛?被感染的基督女,被死亡的母亲,被重新命名的美貌梅·古尔丁,在斯蒂汾的记忆里,一切都变成了被取代的寓言,包括名字,马利根叫他啃奇,“像刀刃”,切开了不能超脱的压抑,切开了对于父亲的忏悔,但始终切不开“挺了狗腿儿啦”的亵渎,所以在马利根的命名之外,也有自己荒谬的寓言:“玛拉基·马利根,两个扬抑抑格的音步。倒是有一点希腊韵味,是不是?跳跳蹦蹦,高高兴兴,正是壮鹿的意思。”
想象的返回,依然不能阻止那些和死亡有关的记忆,以及和记忆的母亲有关的寓言,“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正在设法从梦里醒过来。”历史是圣餐,历史是坟墓,历史是莎士比亚,历史是都柏林的一场大火。斯蒂汾无法释怀的就是母亲死亡之前被拒绝的下跪,所以在死亡之后,“爱的奥秘叫人辛酸”,“我在家里,压低了深沉悠长的和音独自唱着。她的房门敞着:她要听我的歌声。我内心悚然而又哀伤,默默地走到她的床边。她在她那不成样子的床上哭泣。”那首歌曲变成了忏悔,“因为弗格斯统率着铜车”,而其实这些阴沉的秋夜,只有一个被挖去果心塞上红糖的苹果,她那修长的指甲已经被染成了红色,最后是目光里的祈祷文,“愿光辉如百合花的圣徒们围绕着你;愿童女们的唱诗班高唱赞歌迎接你。”重重地按下去,重重地忏悔,却也是重重地忏悔,而在斯蒂汾被写好的寓言里,只有食尸鬼和吞噬尸首的怪物,只有红色的苹果和指甲,只有辛酸的爱,“不,母亲!放了我,让我生活吧。”那个大声对她说话的人,给她正骨的人,给她医药的人,不是斯蒂汾,不是不信教的人,不是讨厌“一仆二主”的人,“神圣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何在?” “我敬爱的牧师”幻化成“可敬的腐肉鸦”,专吃着动物死尸,专门守候着死亡,所以在“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救赎中,只有那些被遗弃的“肝哪、肺哪等等一切零碎玩意儿”,只有麻风病而挺了狗腿儿的死亡,也只有莎士比亚麻痹中的盛怒杀人——杀人之后是没有胡须的脸,是写在一本巨作里的象征,而都柏林的大火在那个夜晚烧起来,而在末日的火中,死人都从前景公墓和杰罗山的坟墓里钻出来,像是被敲醒的门,被末日召唤的魂灵,被编造成寓言的记忆,而那些“肝哪、肺哪等等一切零碎玩意儿”真的还在自己身上?
 |
| 詹姆斯·乔伊斯:书写爱尔兰记忆的寓言 |
篡夺者。斯蒂汾不想念《小荣耀颂》:“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始如此,现在仍是如此,永将如此,无穷无尽。”他的命运是“斯蒂汾老弟,你是永远成不了圣徒的。”所以在他来说,不如坐在孩子身边解一道关于莎士比亚的数学题:用代数证明莎士比亚的阴魂是哈姆雷特的祖父。但这不仅仅是一道数学题,一道可以计算的题目,“哈姆雷特,我是你父亲的亡灵”,飘荡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也成为自己记忆中的一个符号,“他就是鬼魂,国王,是国王而又不是国王,而演员就是莎士比亚,他一生中所有并非虚妄的年代中都在研究《哈姆雷特》,就是为了演幽灵这一角。”《李尔王》、《奥瑟罗》、《哈姆雷特》、《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莎士比亚剧中的痛苦经历是什么投下的阴影?又会在什么情况下消散?这不是历史学问题,当然也不是文学和哲学问题,是关于肉体和灵魂,关于命运的抗争和死亡的归宿问题,是圣父圣子的寓言问题,是“没有发生而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为可能而存在的可能性”。在《裘力斯·凯撒》中,为什么预言家警告凯撒提防“三月中”,而不相信预言的凯撒果然于“三月中”被杀死,没有发生而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为可能而存在的可能性一样,都是无人知悉的事情,都是和死亡有关的末日情结,“泰尔的亲王佩里克利斯在惊涛骇浪西斯似的备受艰辛,是什么东西把这样一个人的心肠化软了的呢?”
那道阴影其实是和不成活的儿子有关,“莎士比亚就是哈姆雷特的信念”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文本和虚构来代替记忆,不安宁的父亲的阴魂最后就是失去的儿子的意象,就像你年轻时立下的愿望,到中年时会真的出现,“要他注意听。他是在对儿子讲话,他的灵魂的儿子,青年王子哈姆雷特,也是对他的肉体的儿子哈姆内特·莎士比亚,那儿子已在斯特拉特福去世,从而使那位与他同名的人得到永生。”莎士比亚的儿子名哈姆内特,Hamnet与Hamlet只差一个字母,这个一五八五年二月二日生,夭折于一五九六年八月的肉体成为永恒的梦魇,灵魂是在肉体上的永恒回归?是被书写的剧本和哈姆雷特,是生存还是死亡的疑问,或者变成了一个buonaroba,一个象征艳俗女人的“普通东西”,“从那些词句中感到,他受到一些肉的驱策,使他产生了新的情欲,这是当初的情欲的一个影子,使他对自己的理解也蒙上了一层阴暗。”这是等待的一种命运,是自己掌控的狂暴,情欲幻变成没有胡子的脸,William和himself变成了一个固定的符号W.H,变成了“我是谁”的终极疑问。
所以按照斯蒂汾的分析,莎士比亚是灵魂的刽子手,“他不愧为屠夫之子,往掌心里啐上一口唾沫就绰起了战斧。为了他父亲的一条命,九个人送了性命。我们的在炼狱中的父亲。穿咔叽军服的哈姆雷特们开枪是不犹疑的。第五幕那血流满地的大屠杀,正是预示了斯温博恩先生歌颂的集中营情景。”父子之间的这种屠杀象征在他拒绝的宗教里又如何变成了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所以依照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有一个嘲笑的观点:“他,自己生下了自己,中间夹上圣灵,自己派自己来当救赎者,在他自己和别人之间,他,受了他的妖孽的欺弄,被剥光衣服又挨了鞭打,被钉在十字木架上饿死,活像蝙蝠钉在谷仓大门上,他,让自己埋入地下又站立起来,下地狱救人之后才上天,在那里坐在自己的右手边,坐了这一千九百年,然而将来有一天还要回来毁灭一切生者与死者,但那时所有生者已经成了死者。”
他自己生下了自己,他也将所生者变成了死者,救赎和惩罚,都变成自己的寓言,所以在上帝的启示面前,埋葬着许多末日里的亵渎,那些鬼魂从坟墓里出来,像是被释放的囚徒,寻找自己丢失的肉体,而贵格会创始人基督福克斯呢,因为反对而受迫害,多次逃亡和被捕使他成为一个被英国教会的讽喻,穿着皮裤子,藏在枯萎的树杈间,没有女伴却获得了妇女的信仰,这里有巴比伦妓女,有法官太太,也有豪放的酒店老板娘,这种信仰最后变成了一个关于“狐狸与鹅”的游戏,就像在“普通东西”身边的莎士比亚,也仅留下一个松弛而不贞的身体,留下内心害怕的坟墓,留下未获宽恕的生命。
解构的不是文学,不是哲学,不是历史,是宗教,是民族,是生命,是死亡,是灵魂,是肉体,“灵魂的某种意义说来就是全部存在:灵魂是形态的形态。突如其来的、巨大的、白炽的宁静:形态的形态。”而肉体呢?“我登上天主的圣坛。”这句神父主持弥撒开场用语在最后的晚餐里不是圣餐,是身体和血液,在考利神父那里是唱着的秀美姑娘,是在风中飘扬的面纱,是竖琴,是卤肉,是杜鹃花丛;在康眉神父那里,是灵魂的蓝没公费,是路旁树篱下缺口里钻出的男女,手里的野菊花不是祝福,不是祈祷,是写着Sin的罪过,是逾越教规和道德的谴责,“王侯对我无故加以迫害,但是我心中敬畏的是您说的话。”身体甚至就是那些“肝哪,肺哪”的东西,布卢姆说,已经在我的嘴里了,他也看见了那些死亡,看见了大火,看见了末日,看见了莎士比亚,看见了斯蒂汾,看见了记忆的女人们和记忆的母亲们,看见了肉体。那是妻子莫莉的身体,莫莉的肉欲,莫莉的背叛。当对于他来说,这种背叛反而变成了对肉体的某种迷恋,颠簸的生活和劳累的工作,使他在10年前就丧失了性机能,而布卢姆明明知道妻子对他不忠,明明在众人面前深感羞辱,也只能沉默忍受。工作、起床、洗澡、吃饭、写信、散步,以及吃动物内脏,成为他生活的全部,而在18小时构筑的世界里,他却在猥亵庸俗之中寻找一丝快意,那本《偷情的快乐》摆放在那里,而读着“给了他一个甜蜜性感的吻,同时他的双手伸到她的睡衣里面,去摸那丰满的曲线。”这样的句子,布卢姆竟感到全身灼热,肉体受到一种压力,“在压皱了的衣服中间,肉体毫无保留地交了出来”;在莉迪亚的身边,他成为一个男人,在他离去的时候,这个女人发出了“走过玫瑰花,走过缎子胸脯,走过抚弄的手,走过酒渣,走过空杯瓶,走过废瓶塞堆,走着打着招呼,走过了眼光和处女毛、古铜和深海阴影中隐隐约约的金发,布卢姆走了,柔软的布卢姆走了,我非常寂寞的布卢姆走了”的感慨;而在那片海滩上,遇见的格蒂就如瑙西卡,“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膝盖以上很高的地方,那地方从来没有任何人看到过,甚至在荡秋千或是涉水的时候也没人看到过,而她并不害羞,他也不害羞,这么肆元忌惮地盯住了看……”像那烟花,黑黑的,软软的,飞来飞去,越升越高,兴奋地不敢喘气,“高的几乎看不见”。“简直是野兽”是格蒂内心里的一种声音,而另一种声音是“并不害羞”。
对于妻子的肉欲,他曾经有过“真的我觉得他那么样的嘬奶把奶头都嘬得硬一些了他嘬了那么老半天弄得我都口渴了他把它叫做奶子我忍不住要笑真的至少这一边的硬些这奶头有一去我要用马沙拉白葡萄酒调鸡蛋喝把乳房为他养得肥肥的”的不间断的故事,可是在某一个肉体消逝之后,这种情欲的享受就变成了折磨,那就是自己小儿子茹迪的夭折,在那个写着寓言的记忆里,有着茹迪侏儒似的脸,有着全是皱纹的紫红色的脸,“像油灰那样疲软,装在一只衬着白布的松木匣子上里。”还是丧葬互助会付的款。“恨。爱。这些都是名称。茹迪。我快老了。”这是布卢姆想说的话,而这个夭折的孩子就像莎士比亚的故事一样,充满着某种宿命,是记忆中的那一部伪作,就像假托亚里士多德的《杰作》,歪歪扭扭、乱七八糟的印刷呈现的是一个血红的子宫,“像从新宰的母牛身上取下的肝脏似的,里面是蜷成一团的婴儿。”婴儿都在努力用脑袋往外顶,但是这种生命的意象对他来说是折磨,那本伪书和《偷情的快乐》放在一起,这是肉体的出生和毁灭,这是情欲的恢复和消灭,而布卢姆的痛苦已经被命名为失去贞操的妻子的灾祸,所以即使在“衣服褴褛发臭”的肉体里也能看见一个妖女的“白皮肤”。
茹迪的夭折,在布卢姆看来,却是一种父权的失落,这是轮回转世,这是灵魂转移,按照保罗·德·科克的书的观点,“我们死了之后又用另一个肉体接着活下去,生前也有生命。他们把这叫做投胎。”所以茹迪就是布卢姆灵魂的一次转移,一种投胎,是“一切肉体都归向您”的救赎,而那个侏儒的身体和油灰般疲软的尸体总是出现在布卢姆的脑中,也如斯蒂汾所说,是通过不安宁的父亲的阴魂,显现不成活的儿子的形象,而布卢姆的父亲在第二只抽屉里留下的启事是关于一个家族改名的秘密:“我,鲁道夫·费拉格,现居都柏林克兰勃拉西尔街52号,原匈牙利王国松博特海伊,今已更名为鲁道夫,布卢姆,并决定今以后在一切场合与一切时期均用此姓名,特此启事。”信封上写着:致亲爱的儿子利奥波尔德。当费拉格变成布卢姆,一种传承的父权体系也解体了,那种投胎或者灵魂的转移只能出现的布卢姆的梦中,梦中有父亲鲁道夫的质问:“你在这地方作什么?你没有灵魂吗?你不是我的儿子利奥波尔德吗?你不是利奥波尔德的孙子吗?你不是离开了亲生父亲的家,离开了祖先亚伯拉罕和雅各的神的,我的亲爱儿子利奥波尔德吗?”梦中当然也有布卢姆受道德审判,发表演说,和神父争吵、医生证明以及受妓女欺凌的场景,但是这一切的梦幻并不能建立一个家族的谱系,也不能延续父权的某种荣耀。
而布卢姆的父权意识完全是身为犹太人的民族寓言,“我的亲爱的臣民们,一个新的时代即将露出曙光。我布卢姆郑重宣告,它已经近在眼前。确实的,按照我布卢姆的诺言,你在不久之后就要进入一个未来的黄金城市,未来世界的新海勃尼亚的新布卢姆撒冷。”这些演讲对布卢姆来说只不过是臆想,当有人问什么是民族时,布卢姆的回答是“民族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群人”,所以在被人嘲笑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位向非犹太人传道的新使徒!”实际上他是被排除在秩序之外,正像斯蒂汾引用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所说:“你们犹太人为何不接受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语言?你们是一个游牧无定居的部落;我们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你们既没有城镇,也没有财富;我们的城镇中有繁忙的人群,我们还有大批配备着三排桨、四排桨的大船,满载各式各样的货物,航行在已知世界四面八方的海洋。”而在爱尔兰,只因为成为唯一没有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实际上只是因为从来没有让犹太人放进来过,而布卢姆无疑是这个国家中一个异类,青年摩西为什么当初要出埃及,就是要从拥有强大队伍和胆战心惊的武器的埃及寻找属于自己的力量,“你们被人称作流浪汉和卖苦力的:我们的名字威震全世界。”,所以弱小的以色列到最后变成了一种怀疑,“如果他在这种高傲的教导前低下了脑袋,丧失了斗志,丢掉了主心骨,那他就决不会率领神选的民族脱离奴境,也不会在白天追随云柱了。他决不会到西奈山顶的雷电阵中去和神明对话,也决不会满脸放射着灵感的光芒从山顶下来,怀中抱着用亡命者的文字镌刻着律条的石板。”
布卢姆“属于一个被歧视、被迫害的民族”,但是他所想要的是博爱,“侮辱和仇恨并不是生命,真正的生命是爱”。正像父亲所说:”他将为自己所迫而永远漂泊,直至自己的彗星轨道的顶端,超过各种恒星和各个多变的太阳和用望远镜方能见到的行星,那些天文学上的流浪儿和走失者,直至空间的尽头,经过一片又一片的国土、一个又一个的民族、一件又一件的大事。在某一个地方,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将会听到召唤他回家的呼声,将为太阳所迫而不情不愿地应声归来。“他的漂泊是寻找那个“顶端”,那些行星,那些流浪儿和走失者,那一些召唤他回家的呼声。
而流浪儿和走失者在哪儿,那个家在哪儿?“我们的出生方式莫不相同,而我们的死亡方式却各有一套。”对历史、对宗教怀疑的斯蒂汾在街上被人毒打之后,渴望寻找救赎的父爱的他从布卢姆身上找到了契合,而这种契合在布卢姆看来,刚好是填补自己丧子之痛,按照文·林奇提出的设想,出生和死亡都受着某种守恒的规律,“和宇宙演变的一切其他现象相同,如潮汐运动、相转换、血液温度变化、各种疾病,总而言之,在大自然的巨大作坊中,从某个遥远的太阳的陨灭,到点缀我们公园的那无数朵花之一的盛开,一切都受一种至今尚未弄清的数字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父权的失去就意味着回归,妻子的背叛意味着救赎,对宗教的怀疑也意味着肯定,“一个由正常健康的父母生下而本人看来也很健康的孩子,照料也很恰当,何以竟会在童年的早期无故夭折?我们大可放心,大自然对其一切作为,都自有其正确有力的理由,这一类的死亡很可能是服从一种预防性的法则”。在规则面前,在布卢姆和斯蒂汾共同的“回家”中,他们在各人审视对方中,“相互形成肉镜”,这个有着爱尔兰艺术象征的镜子在这里变成了“拼合形象”,这是一名孤独而变化男人形象。孤独是“自我关系”,是“兄弟姐妹他一概全无,他父亲的父亲是他的祖父”的关系,而变化是“异己关系”,是“自婴儿期至成年期,他像他的母性生育者。自成年期至老年期,他将像越来越像他的父性生育者。”
他们在这种“拼合形象”中形成了新的“三位一体”,他们回家的归程是一条平行路线,途径下加德纳街、中加德纳街、蒙乔伊广场西路,然后降低速度,均向左转,沿加德纳里直走至远处的圣殿北街口,然后仍以慢速走走停停,向右拐人圣殿北街,直走至哈德威克里。,再到后来不再挽臂,以轻松步行速度,同时取直径越过乔治教堂前圆形广场,直到最后回到家里。他们用姓氏、年龄、种族、信仰这四种分隔力量来区分那些临时客人,而他们之间的年龄也构成了某种关系:
十六年前的一八八八年,在布卢姆为斯蒂汾现有年龄时,斯蒂汾为六岁。十六年后的一九二〇年,当斯蒂汾为布卢姆现有年龄时,布卢姆将为五十四岁。至一九三六年,当布卢姆为七十岁而斯蒂汾为五十四岁时,他们二人起初的年龄比率16比0将变成17½比13½,随着任意性未来年数的增加,比例将增大而差距将缩小,因为如果一八八三年的比例一直保持不变,假定这是可能的话,则于一九〇四年斯蒂汾二十二岁,布卢姆应为三百七十四岁,至一九二〇年斯蒂汾达到布卢姆这时的年龄三十八岁时,布卢姆将为六百四十六岁,而至一九五二年斯蒂汾达到大洪水后最高年龄限度七十岁时,布卢姆将已活一千一百九十年,出生于七一四年,比大洪水前最高年龄即玛土撒拉的九百六十九岁还大二百二十一岁,而如果斯蒂汾继续活下去,至公元三〇七二年达到那个年龄,则布卢姆应已活八万三干三百年,出生年代不能不是公元前八一三九六年了。
科学气质和艺术气质,深沉苍老的过去和敏捷年轻的未来,以及一先一后的小便,不相似的轨迹,都变成了一种灵魂的转移和拼合,当斯蒂汾把身体蜷成一团,布卢姆拿着帽子和手杖直立在一边的时候,身体的变幻完成了一次“投胎”,斯蒂汾的脸和身体有了另一种意义:“脸像他那可怜的母亲。在树林的浓荫里。深处的白色酥胸。”而远处的那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就变成了茹迪:“直视布卢姆的眼睛而无所见,继续念着书,吻着书页,微笑着。他的脸呈现一种柔嫩的紫红色,衣服上的钮扣是钻石和红宝石做的。他的左手拿着一根细细的象牙棍子,上面系着一个紫色的蝴蝶结。一只白色的小羊羔从他的坎肩口袋里探出头来。”
微笑着,呈现出紫红色的脸,象牙棍子、蝴蝶结以及白色的小羊羔,成为一种救赎的象征,但是这个在布卢姆和斯蒂汾之间形成的“拼合形象”和肉镜到底会不会带来新的秩序?那面镜子如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妖精凯列班看见的自己一样,“十九世纪人们对现实主义的憎恶,是凯列班在镜中见到自己面容时的狂怒。十九世纪人们对浪漫主义的憎恶,是凯列班在镜中见不到自己面容时的狂怒。”王尔德的注解成为这个世界的隐喻,看见自己和不看见自己是不是都意味着狂怒?“有何事件能使这些计算全部作废?”回答是:“两人或其中之一停止生存,历史另辟新纪元或新历法,世界毁灭以及随之而不可避免但无法预言的人类消灭。”
“它是一部关于两个民族(以色列-爱尔兰)的史诗,同时是一个周游人体器官的旅行,也是一个发生在一天(一生)之间的小故事……它也是一种百科全书。”当回家从身体、灵魂、宗教、父权、民族的十八个小时变成一个时代的象征时,谁能找到那面肉镜的象征,那种流亡的救赎,那种编造的寓言和想象的神话?而当乔伊斯站在一九二二年的记忆中的时候,那一张判决的纸张正如那个装在匣子里的柔软身体,是需要有人唤醒,从前传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到续篇的《芬尼根守灵夜》,夹在回家路途中的布卢姆用一个仪式化的“布卢姆日”开启了与神的对话,是的,只有在地震、大火和旱灾的毁灭面前,才会有灵魂的转移,才会有形态的形态,才会有死亡之后看见真正的自己:“这时一个声音自天而降,呼唤着:以利亚!以利亚!他的回答是一声有力的叫喊:阿爸!上主!他们见到他,正身的他,儿子布卢姆·以利亚,由大群大群的天使簇拥着升向金光圈中,以四十五度的斜角,飞越小格林街的多诺霍酒店上空,像一块用铁锹甩起来的坷垃。”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0533]
思前: 《一一》:寻找自己世界里的唯一
顾后: 《渔光曲》:无声现实里的命运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