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16《影像的法则》:建立分析的“知识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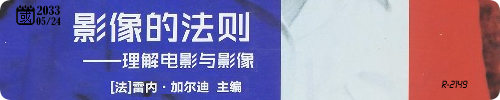
我们处在一个影像得到发展的时代。
——《从文化角度研究影像》
书名是“影像的法则”,副标题则是“理解电影与影像”,电影和影像到底是同一性概念还是异质性所指?雷内·加尔迪的第一部分分析的是“电影”,第二部分则分析“影像”,如此区别电影和影像是并置结构,而实际上,影像范围更大,外延更多,在加尔迪看来,影像可以是电影影像,也可以是照片的、绘画的、电视的和数字的影像,影像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它在社会上的标志就是语言、图表、声音所包括的各种物品,甚至还包括光盘等媒介,如此,影像是一种可见、可听的“展示性”内容,而电影影像无疑属于影像之一种。
加尔迪讲电影和影像并置,其实是把电影从影像中单独抽离出来,从而阐释电影所具有的独特影像意义。但是作为一本为相关专业学生进行学习的图书,加尔迪并没有系统而深入地阐述影像的内在特质,而是着眼于一种条目式的介绍,他在“引言”中就指出,本书旨在为电影爱好者提供了解电视和交互式图像的方法,或者反之为交互式图像谜提供走进电影和电视的方法,不管是何种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关于影像分析的“知识状态”,通过对各种影像特点的介绍,概括和揭示影像所具有的文化、叙事、预言、美学等方面的意义,“对方法论提出建议,以便共享上述知识。”所以很明显,这只是一部介绍影像知识的图书,只是把影像放置在一种“知识状态”之中。
所以,知识所提供的就是学习,就是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在电影部分,加尔迪介绍的是和电影有关的一组术语,比如取景、镜头、视点、剪辑、叙事等,不过在这些和电影有关的基础知识之外,也提供了一些理念式的知识。比如“取景”指的是“一幕”或“一幕效果”,它所界定的是一个视觉空间,并将其转化为一个展示空间;“美式取景”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大腿中部犯人取景方式,也称为“3/4取景”,名字来自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西部片;特写镜头可以和情感进行连接,按照吉尔·德勒兹的说法,“没有所谓的面部的特写镜头,面部本身就是特写镜头,特写镜头本身也是面容,它们都充满情感,都是富有感情的影像。”除了这些纯粹知识性的介绍之外,加尔迪也比较简单地引入了一些理念,比如取景和影像的关系,当取景界定和建构了视觉空间,它的目的就是转化为一种展示空间,而影像所具有的就是它的“展示性”,取景是影像诞生的第一步,但它并非是对现实的拷贝,而是关于世界的论述,一方面,影像改变了自己记录的东西,它将拍摄的内容纳入一个叙事过程之中,并对之进行解释,同时在情感层面,影像的展示性通过主题和突出因素引发情感体验。
从视觉空间转变为展示空间,影像超越了视觉,具有了一种“影像意识”,它与镜头给观众带来的现实主义体验不同,它造成的是一种非现实感,也就是说它和“镜头”不同,影像是一个异质的空间,这就是影像所具有的另一方面的功能:取景是对观众眼睛位置的想象,或多或少透露着导演的想法,这样的影像理解在克里斯蒂安·麦茨那里就变成了“无人称表述”,也就是在电影中加入了一些推理性的自省,这种自省并没有特别的特征,但却通过不同形态,以及在电影不同的层次中得到反映,而米歇尔·马利和马克·韦尔内对它的解读是:“表述是一帧折页卷边的风景,通过这帧风景电影告诉我们它是电影。”从单纯的记录,到展示,再到表述,影像区别于镜头,区别于取景,具有了丰富的含义,在剪辑部分中,加尔迪举例说,当摄影机直接从一个人物移到另一个人物,它是动态的,却是同一个影像,但是当分别给两个人物各一个镜头,然后在中间停机,就变成了不同的影像,这两个不同的拍摄对象通过两次取景被连接起来,这就是分镜头,它调整了视角,它分离了元素,它也整合了另外的元素,由此形成了一种连贯性,这种连贯性的影像具有的意义,一方面在对叙事的单位进行分割,有利于反映事物所代表的意义,另一方面则确保影像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
同样,“视点”也存在着这种影像关系。视点在摄影机的运用中造就了一个目击证人,如果摄影机在构建镜头时所采取的技术与日常生活所见匹配的话,观众对这个目击证人的定位就是麦茨所说的“初级认同”,但是当不匹配时它所创造的是一个“占据有利位置的看不见的证人”,比如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总是以低于日常的视点进行拍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认同,但却交给了观众更多对某些规律的发现,按照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话,导演只要讲述了一个开头,剩下的事就可以交给观众了,而观众通过拟人化达到了一种认同。而实际上,不管是初级认同还是看不见的证人,视点构成观众的体验点,观众就不是被动接受,而是成为了“偷听者”或“偷窥者”,他们看到和听到的同时“既不会被看到也不会被听到”,从而有了对上演的故事进行决断的可能。除了和观众有关的视点,还有莱尼·里芬斯塔尔在纪录片中创造的视点,它以眩晕的、晃动的方式让视点不属于叙事主体,在拍摄《意志的胜利》时,她的镜头数次推移到了纳粹党位于纽伦堡的议会大楼,围绕着在讲台上发表演讲的元首进行巡回仰拍,目标是静止的,也非剧情需要,但是通过摄影机的运动制造了视点,实现了对机器运动的自由运用。还有的视点叙事就是放弃对片中人物的跟拍,而是摄影机与演员同步移动,但方向不同,它具有一种后现代风格,加尔迪认为,这是在心理学意义上起到了从“心力内投”到“表情传达”的转变效果,另外如杜拉斯的声画分离制造的视点和声点,则在异质中玩起了心理现实主义。
| 编号:Y29·2250705·2327 |
电影导演对视点的不同处理,其实都是在完成一种电影叙事,叙事学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叙事是独立于叙事所使用的语言之外的实体,二是叙事根据语言不通、进行方式不同而进行的“诉讼”,加尔迪认为还有第三个层次,那就是实现叙事媒介的不同。电影叙事的理论是对不同叙事文本的借用和发展,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提出了民间故事的叙事具有一个“自主的实体”,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一篇文章具有了叙事性,那么这篇文章就是“故事”,也就是说叙事性是故事的“第一义”;格雷马斯则拓展了叙事的逻辑结构,他认为所有的故事都建立在六项基本的功能之上,它们相互联系,但他所注重的是台词的意义,所以这样的叙事更多是一种符号学理论;罗兰·巴特则提出了故事中的功能和指数,功能关注于故事的发展,侧重于“做”,它沿着意群主线而展开,而指数则着力于丰富故事的内容,侧重于“是”,也就是说,功能构成了故事的骨架,而指数则丰富了故事的血肉。
吸取的这些理论丰富了电影叙事的内涵,艾提安·苏利欧将叙事从文学引入电影,就是要构建一个属于电影的叙事世界,这个世界的“知道”是明显区别于“看到”的浅层次表达,“知道”并不局限于看到的东西,所以在“知道”意义上构建的叙事学就涉及到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定位,通过摄影机位置及焦距的选举可以确定一个可视范围,但是它也对应于“不可视”范围,可视范围是肯定认知,而不可视范围则是一种“假象认知”;第二个则是展示,向观众展示的东西或者源于叙事的内部审视,即内部展示,或者是一种外部审视;第三则是聚焦,它要处理的是讲述者、人物和观众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知道”的意义,观众“知道”的是一种“子叙事世界”的东西,它来自于视觉和听觉系统所接受的信息。电影叙事学其实凸显的是观众的位置,它不再只是对电影物的观看,而是构建了一个电影世界,甚至这是一个观众根据电影所给出的暗示而现象出来的世界。
对电影的分析,加尔迪基于电影学相关的术语进入一种“知识状态”,电影只是影像的一个类别,而“分析影像”则进入到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世界,对于影像具有的“展示性”特征,加尔迪引入了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当我们观察某物时,我们的所见总是被我们的所想左右,所想所力图摆脱的是最初的印象,也就是说,它在摆脱的同时重组视觉元素,以另一种方式观看这一被想象的物——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所有的“看”都是“看起来像”,它是一个看和解读同时发生的过程。这其实也是将影像的展示构建在观看者的位置之上,那么观看者是不是被赋予了影像作者的角色意义?在观看变成“看起来像”的过程中,当观看者被赋予了影像作者的身份,在影像作者的意义上,就产生了不同的身份:首先它是“证人”,是对现实情况描绘的证人,和真实情况发生关联;第二则是讲述者,故事是由讲述者直接讲述的;第三则是调度员,尤其在一些电视游戏、辩论节目中,调度员控制着节目的节奏;第四种则是“符号的”存在,它是一种翻译者,与对现实的某种解读产生关联,并由此进入到一种具有相似性的特殊世界。
阐述了影像作者具有的不同身份之后,加尔迪分析了“动态影像”具有的审美意义,首先什么是“动态影像”,加尔迪并不局限于“动态影像”即电影的界定,而是扩展了外延:它是一个由机器和社会行为构成的装置系统,这些社会行动包括去电影院看电影、在家里看电视以及对影像进行评论;其次,它是一个包含有思想和催生意义的行动具有的媒介视听信息系统;它也可以指的是一整套的作品——比如电子游戏是一种装置,电视节目是信息系统,电影是作品,但是这种分类还是太过于机械,“动态影像”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各种形式的影像系统,而对其分析所要确立的标准就是美学,在审美意义上,动态影像所具有的也是不确定性,如罗兰·巴特所说:“解读一篇文章,不是要赋予其意义(不管是有所依据还是天马行空),相反的,是要欣赏它到底有多少种可能的意义。”很明显,对动态影像进行美学分析,就是使其从科技层面回到艺术层面,“科学一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美学就该登场了。有足够多的东西在等候着美学登场……”
对影像的审美也在这一层面上展开,比如在观众层面,既有“被表现的观众”,也有“被分析的观众”,在格式塔理论与完形主义、电影学、精神分析法、实用主义、文化研究本配合、认知主义等理论中分析观众,加尔迪重点阐述了“精神分析法”中的观众,而这又恰恰是“把观众视为不知情的精神分析的对象”,这里存在的观点,一是一种假设理论,即在电影设备和心理机制中存在着某种相似性:“观众处于运动机能不足的状态,易收到视听刺激。从影像的角度来说,摄影机大体沿袭了针孔照相机的视角,将观众的视线置于中心(整个空间是以观众为中心建构的)。从声音的角度说,观众被多多少少都能被感知到的的噪音和言语包围,一切与声音有关(真正的声源不得而知)。”第二种是梦理论,当观众深处黑暗影院,被弃于自我无法掌控的影像之中,在广义的视觉化、戏剧化、凝缩、移置的过程、逻辑和时间顺序混乱中进入到一种梦中;第三则是欲望理论,影像的看和听带来的是某种冲动的欲望,它指向的事偷听和偷窥——这也是和在电影中已经提出的视点相关。
对于电视的分析,加尔迪强调了电影观众的无法选择性性,电影观众可以自己选择观看的电影,但是电视观众是在拿着遥控器的时候与影像不期而遇的,他也不知道影像的来源,不清楚影像的背景,所以在这里加尔迪更把这种状态看做是分析哲学所说的“符号”,影像本身是“代表项”,而观众的作用就是一个“解释项”,为了构建而形成更高级的符号。从“代表项”的影像和“解释项”的观众之构建,是不是也体现了一种影像的生产机制?这在交互式影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交互式影像就是数字化影像,它是由数字构成的信息语言,它通过“计算”合成影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影像和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如果使用者不介入,那么影像就静止不动,它等待使用者的介入以变化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互动中的行动导致了变化,“行动-变化”则构筑了影像流,在这个影像流的空间里,影像作者和产品进行着“超沟通”形式,而使用者则扮演了“超观看”者,它带来的是关于视点的变化:观众自身的要求变成了影像;影像包含了一个自身的“界面”,因此加尔迪提出的问题是:交互式影像提供了怎样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是否可以谈论“表现”?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