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06 《圣洁百合》:她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撒旦

最后,一个总结性的特写镜头:四五个妇女惊慌地在浓烟与烈火中从掩体里跑出来,她们惟恐被枪弹击中。当她们怀里抱着孩子、手里牵着孩子来到开阔地时,不停地眨着眼睛,好像刚刚睡醒似的。孩子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孩子们啊。
——《克拉克/以扫/斯利克》
孩子太多了,母亲也太多了,从一场火灾中被救出,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是一个睡梦,终于看见了那个真实的世界。看见是一种真正进入现实的状态,而这个一九九〇年的特写镜头在电视上播出,坐在屏幕前面的却是对电影极其反感甚至抵抗的特迪,一个年迈的老人也是看见真实的世界,也是进入现实的状态,而在被看见的镜头里,除了太多的孩子,除了太多的母亲,还有那个改名叫以扫、加入“真理与真正信仰的圣殿”之后叫做斯利克的克拉克,太多的名字组成了特迪外孙的唯一镜像,不管是宗教意义、异教名义,还是家族意义,克拉克都在用一种超越的方式定义自己,是的,看见这一幕的还有自己的母亲,改名叫阿尔玛的埃茜祷告着说:“感谢你,上帝,使我的儿子最终成了一位英雄。”
从堕落者到英雄,是一场火的救赎,对于克拉克来说,仿佛经历了两次死亡,进入圣殿是他在现实的第二次死亡,那个“下河——圣殿入口”的世界给他打开了一扇门,他看见了宛如上帝的荣光,“我们不是天使,克拉克,我们是等待被拯救的人。”当从越战战场回来的耶瑟告诉他需要拯救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那个充满着金钱和娱乐意义的现实,这个以娱乐为中心的世界早晚有一天会垮掉,那么进入了圣殿,就是远离亵渎,远离迷失,甚至远离母亲,那里有一个上帝就叫耶瑟,“上帝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而对于电影演员的母亲,耶瑟的定义是:“上帝让她在淫荡的娱乐圈里占有一席之地,她为了不破坏他们的合同,连一个宇也不肯吐露。她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撒旦,对你说,她甚至不愿意跟撒旦分享她那不体面的幸福,包括她与人的性关系和对上帝的亵渎。”
|
| 编号:C54·2150517·1172 |
那么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羔羊必将战胜,可是谁是那只待宰的羔羊,谁又是那群跟随着上帝的羔羊?母亲阿尔玛31岁结婚,却和克雷斯维持到1970年再分手,对于克拉克来说,似乎雷克斯只是自己一个虚拟的父亲,“一桩失败的婚姻导致了另一桩的产生”,这是阿尔玛婚姻的写照,在那么多婚姻面前,降生的克拉克一定找不到真正的父亲,甚至阿尔玛在回答他的提问时,也以一句“雷克斯就是一个鸡巴”作为答案,只有鸡巴的父亲,无数段婚姻的母亲,克拉克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存在感的现实里认出自己,只有自己认出自己,也只有自己能够确认自己的死亡。
以扫,或者叫斯利克,克拉克需要的是一种在赎罪中的重生,两次死亡他一直在寻找上帝,而在他面前的上帝就是耶瑟,这个在越战中负伤的人继承了基督复临论,“基督复临论”在遭遇了第一次失望和更大的失望之后,终于在耶瑟的秃头精神中寻找上帝的复临,只有消灭政府才能找到上帝存在的意义,“没有上帝的政府”,三个字头GOG拼合而成便成了Gog——歌革,歌革是上帝,歌革是救赎者,歌革就是耶瑟,“我们的宗旨是爱,爱是我们所能互相感受到的。我们并不是总不实施惩罚。”歌革的爱是什么,是对于政府的痛恨,是对于秩序的颠覆,是对于娱乐的否定,而作为电影演员的阿尔玛自然成了他们摒弃甚至攻击的目标,娱乐化、肉欲化,甚至无父化,都成为克拉克新的向往,所以他才会死心塌地成为圣殿组织的成员,在两次死亡中迎接他的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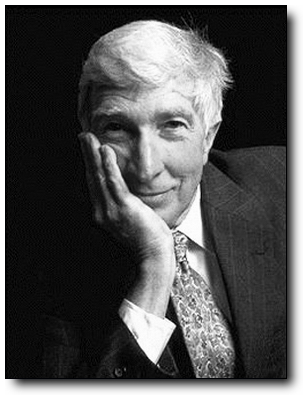 |
| 厄普代克:乌托邦只是一个沉沦的漩涡 |
但是这是不是新的亵渎,那个上帝是不是也是撒旦?当以扫穿上圣殿里姐妹们用白床单做成的长袍时,他感觉到死亡之手在轻轻抚摸他;当圣殿成员和州警察交战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神圣的使命,“圣殿里那个朝校车开枪的成员已在枪战中死亡。他是烈士。我们是受害者,不是侵犯者。”而当耶瑟将这块土地视作天国,视作宝藏的时候,却是最后被剿灭的现实,一场新的战争光凭这复临论的观点,光凭歌革的教义,光凭对于所谓真理和真正信仰的信心,会得到永恒的拯救?那曾经的爱又在哪里?依然是痛苦,依然是死亡,依然是惩罚,甚至伤害的是另一些无辜的人。所以圣殿里的上帝只是一个虚设的符号,就像克拉克曾经在妈妈的游泳池边面对陌生的克雷斯一样,玩的只是那个空心棒球,父爱的缺失不仅仅只是亲情上的遗憾,也是信仰上的空白和欺骗,所以当克拉克最后向耶瑟连开两枪的时候,他打倒的是一个假先知,也把自己的人生推向了另一种死亡。
第三种死亡,羔羊必将战胜。“他没什么好担心的;那位活人上帝曾经控制过他,而那位永恒的上帝能否带给他理想的白局又超出了他押宝的能力。”活人上帝死去,永恒的上帝在寻找,克拉克用英雄般的壮举将太多的孩子、太多的母亲从火场上救出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完成了救赎和自救,他甚至也成为一个活着的上帝。堕落而重生,对于克拉克来说,曲折的信仰之路其实推翻了种种的信仰,缺失的父亲,亵渎的母亲,假冒的上帝,甚至他用这样的壮举完成了一个家族四代人对于信仰的找寻。
电视新闻上的特写,母亲口中的赞叹,其实就像是一个讽刺,克拉克讨厌娱乐化的电影,讨厌以肉欲为手段的演绎生活,那么这样的上帝是不是就是一种解构,对于现实的解构,对于暴力的解构,对于金钱的解构,甚至对于信仰的解构?解构对于这个家族来说,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成为一个矛盾和多元的行为方式,第一代的克拉伦斯是牧师,二十年的生涯给他的不是对现实的超越,而是对上帝的怀疑,“摩西五经里的上帝是个荒唐的恶棍,野蛮地叱咤于一个完全被曲解了的宇宙之中。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想法。没有这样的上帝,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上帝。”从一开始,上帝就以恶棍的形式出现,战争、物欲、金钱和失业,在这个现实里,为什么没有真正解救的上帝?“除去残酷与死亡,所有抽象的事物都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了上帝这个前提,一切抽象事物都不再是抽象的了;一切都变得十分具体,而这一切又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忘却。”其实抽象的上帝是无法在具体的物质世界里让人们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堕落,这是迷失,信心丧失的克拉伦斯把责任归罪于自己,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他坚持的上帝之道是一种机械式的教义,面对物质化的现实,他无力而无奈。
现实是什么?是报纸上登载的社会新闻,高温天气,欧洲的洪水和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一九三一年开始的纺织工人大罢工,是两万五千名工人与三百个业主对峙不休的斗争,“在意大利,爸爸常说有三个暴君——神父、绅士和il tempo,就是天气。在这里只有一个暴君,金钱。”卡拉威罗的小女儿的这句话让卡拉伦斯彻底从牧师的座位上走下来,辞去牧师之物,他推销二十四册的《通俗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物质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书里全是事实,没有幻想。”而丧失了信心对于克拉伦斯来说,却是一种再无回来可能的驱逐:“是我的上帝决定把我驱逐出去。”
而在家族的第二代特迪身上,具体、物质的现实并非让他得到适应,他反而用一种病态的爱来拯救自己。克拉伦斯推销百科全书以失败而告终,最后结核夺去了他的生命,死亡变得平静,变成早晚的事,“父亲去世以后,他们就像内疚的密探,越过敌人防线,潜入那个真实的、喧嚣而又冷漠的另一个世界,然后又偷偷回到被寂静摧垮了的家中。”对于特迪来说,他既不会成为牧师,也不会寻找新的上帝,收租员、药店服务员,在社会的底层,特迪构筑自己的人生,而当1926年春天见到艾米丽的时候,他才在这个跛脚姑娘身上发现了爱的温度,“我有一只严重残废的脚,但是没有黑色的血液。”她说。离开纽约,回到贝辛斯托,他们完成了不被家人赞成的婚姻,健全的特迪,富有的艾米丽,他们似乎在一种互补中找寻心中的那个上帝,相信上帝有手,当然相信上帝有爱,“一份工作,一个妻子: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不管是卡拉伦斯的逃避,还是特迪的发现,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现实已经动摇了信仰的根基,动摇了上帝的定义,和这个家族的变迁轨迹相对应的,还有另一条变化的轨迹,那就是娱乐化的电影的发展。一九一〇年春天,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市郊贝尔维斯塔城堡的开阔高地上,人们正忙着拍电影。电影作为一种新技术的革命,“掩盖了人类诸多苦难,以它迷人的轮廓博取人们的信赖。”这种掩盖是一种现实的物化,是一种生活的戏剧化,
“电影把观众带往各地:荒蛮的西部、曼哈顿的贫民窟、加拿大北部的木星区、中国的鸦片馆、英国的城堡、圣地的沙漠以及公元头几世纪的罗马斗技场,惟独带不到像帕特森这样普普通通的城市。”所以当电影打开一个世界的时候,很多旧有的秩序都在改变,甚至在审美、道德、信仰之上变成了新的威胁,“电影撩开了所谓的安全可靠、高洁正派和平静和谐的世界的裙裾,暴露出肉体的欲望与残酷的不公。”
但是,卡拉伦斯似乎是迷幻在这样的电影世界里,光斑闪烁、画面晃动、忽明忽暗的效果把克拉伦斯从已坠人的漆黑之中推向了光明,但这似乎只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在特迪看来,现实在电影中被放大,也在电影中被美化,“电影把一切该隐蔽的事物赤裸裸地搬上了银幕,除此以外还有痛苦、拳斗、爆炸、暴力、甚至还有死尸以及龙·钱尼扮演的妖怪。”所以面对电影发展的潮流,特迪选择的是与父亲相反的道路:躲避和反抗。相反的道路,总是会在后代的生活中呈现另一种的逆行方式,在特迪和艾米丽健康的女儿阿尔玛身上,而完全变成了人生最重要一部分。“世界好硬好硬,如一块大石头,无论是梦还是思想只能从它表面一溜而过。她又朝相反的方向把四个角落看了个遍。”
相反的方向总是一次冒险,对于阿尔玛这个生活在最美好的城市最幸福家里的女孩来说,电影带给了她一种幻想,“电影中有许多非常穷和非常阔的人,可是像威尔莫特和西福德这样在两者中间的人不多。像这样生活在中间,这是让埃茜感到幸福的又一个原因。”而其实电影生活已经渗透到当时的现实社会中,现实甚至已经变成了电影化的现实,而拥有完美身体的阿尔玛似乎注定无法走出电影世界的那种幻影,渴望成功的本性和充沛的精力,使得阿尔玛一步步走进电影世界那扇光怪陆离的门。欲望或者是天生的,而用身体直接表达欲望或者是内心真正走向“相反方向”,十三岁被人拽了裙子边的带子,十九岁时开始向男人展示自己的身体,二十八岁时被编剧弄大了肚子,在阿尔玛的身体叙事里,电影带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她也渐渐成为欲望的牺牲品,“羞耻可不属于她的宗教信仰范畴。”其实是走向了宗教的反面,以一种邪恶的方式表现自我。
相反的道路永远有着无法弥补的缺憾,“在她扮演过的诸多角色中,扮演母亲是她演得最不成功的少数几个角色之一。”克拉克出生,对于她来说,完成了关于母亲的使命,但这个使命从来不是伟大的,甚至是将他带入到另一个堕落的深渊,为什么“她更希望她的家人假装以为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电影”?在这个电影世界里,她像是天使,像是主宰男人的上帝,但是这种上帝的另一个意义是撒旦,实际上,阿尔玛从特迪和艾米丽的女儿埃茜更名之后,她就住在了电影这个乌托邦里,在这个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里,只有本性和欲望,没有信仰,没有爱情,当然,也没有母性。
“大海彼岸基督诞生圣洁百合丛中,/以他荣耀胸怀净化你我心灵;/如他以死换得我等神圣,/当主继续前行,/我等亦应以死换取自由人生。”引用朱莉亚·瓦尔德·豪的《共和国战歌》来表现对于“圣洁百合”的向往和追求,看起来上帝之救赎只意味着牺牲,实际上,在物质化、娱乐化、战争化的现实里,四代人对于上帝的找寻中,都叉入了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克拉伦斯的《百科全书》,特迪和艾米丽缺陷的婚姻,阿尔玛的电影,以及克拉克的圣殿,都以一种拒绝的方式回归到自我,但这种回归并非是真正的信仰,并非是心灵的归宿,死亡和痛苦,暴力和欲望,甚至堕落和邪恶缠绕着他们,而当那一场大火让最后的故事走向英雄般的救赎,真正的上帝是不是正在出现?太多的孩子,太多的母亲,但是那个唯一的父亲又在哪里?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