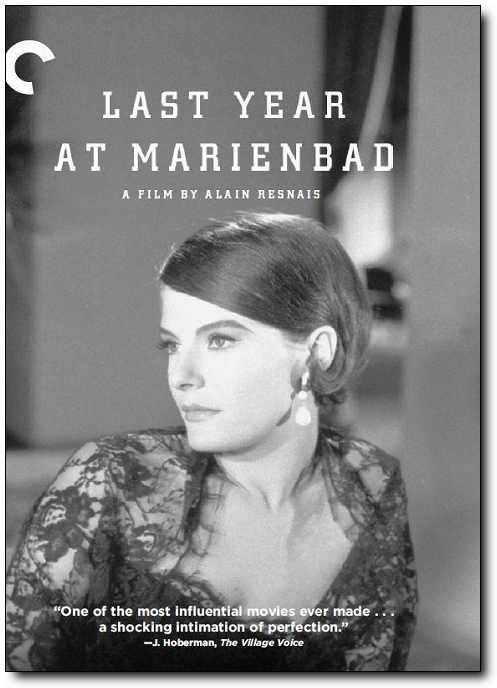2016-02-03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从时空的迷宫脱身

为什么挂钟会敲响?先是第一声,之后的两声,五分钟在鸣响一次,钟声是时间的标记,这是午夜?这是今晚?在时间被标注之后,是空间的确定,他从楼梯上走下来,脚步自上而下,而她则回过头来望着他,目光从下往上,他是凝重而作出决定的,她是微笑而释然的,然后走下楼梯,走过过厅,向着出口的地方走去——没有携手,没有相拥,他和她,依然是前后左右地在各自的道路上行走,只是从可以有选择的通道出去,便不再有前后,不再有左右,不再有他和她。
背景空无一人,灯光还亮着,旅馆越来越远,却像越来越大。是吞没,还是脱身?他的声音传来:“这个旅馆的大花园是一种法国式的花园,没有树,没有花,没有任何种植物……砾石、石头、大理石、直线条使空间显得刻板,使外表没有神秘感,乍一看,好像不可能在这里迷路……沿着笔直的小径,在姿态僵死的塑像和花岗岩平板中间……乍一接触,好像不会迷路的……而现在您正在迷路,在这静静的黑夜里,单独一人跟着我永远迷失方向。”是独白,像是只对着自己说,但是不管是法国式的花园,不管是树和花,不管是砾石、道路,不管是直线的空间,都应该是确定的,就像独白的声音,总是他在这个离开的夜晚说出的话。但是,笔直的小径,僵尸的雕塑,花岗岩,却在寂静的黑夜里,慢慢被吞没,没有了他和她,没有了确定的花园,走向的是更远的时间,更远的空间。
|
| 导演: 阿伦·雷乃 |
 |
两个男人,一个女人,是不是一场爱恋的三角故事?今晚是不是早就注定了这样的结局?这是被计划的夜晚,也是被命名的夜晚,就像他叫X,她叫A,而她的男友或者丈夫叫M,X、A、M,是被命名的符号,所以命名的故事就是一种言说的秩序,就是无法被想象的存在,那么当挂钟敲响,当大门打开,当灯光不灭,确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如何真正脱身?但也只是一个个代号,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作为背景的故事,X或许就是拥有这样一切的存在,所以他在今晚要带她离开,完全变成了一个逃离的行动,只不过他要寻找一个客体,一个可以带离的客体,一个迷失自己的客体,这样便像一个不曾发生的故事一样,充满了无限可能性。所以他对她重复的那句话是:“离开他,离开你自己。”
|
|
|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海报 |
A问他,你是谁?X说:“您知道的。”A问他:你叫什么名字?X的回答是:“这无关紧要。”所以他起初就是陌生人,就是被架空了一切的陌生人,而他只在自己的独白里看见陌生的自己。连同这个旅馆,这个花园,这个女人,都是作为一种自己对面的可能性存在的。像一堵墙,“碰来碰去总是墙,——我的周围到处是墙,——单色的、光滑的、锃亮的,没有任何支撑点,碰来碰去总是墙……”墙是冰冷的,墙是厚实的,墙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旅馆里,古老的大厦,奢华的房子,无尽的走廊,黑暗的木雕,灰暗的肖像,以及空荡荡的客厅,看起来是一种具体的存在,但是却像一个囚禁的牢笼,是将人推向隔绝和孤独,推向恐惧和惶惑。旅馆里住着男男女女,他们跳舞,他们听音乐,他们看演出,一种生活仿佛就是奢华而富有的,仿佛就是具体现实的反映,却也是走不出的藩篱。
所以,他们几乎禁止在那里,成为一种死去的雕像,他们谈论,却总是被淹没,那幅画,那场演出,那次交际,那个图书馆,以及那一位父亲,都变成了和X的孤独有关的背景,以及这个几乎成为荒地的花园。所以,在那些斜体字标注的独白里,X是要从这样的时空和生活中走出去,到处是空荡荡的走廊,到处是黑暗的门,到处是精致的花纹,到处是“请勿说话,请勿说话”的告示,X的声音似乎也变成了这里的一部分。那个游戏为什么总是会输?七张牌、五张牌、三张牌,以及一张牌,每个人每次只能从相同的一行中拿牌,但是最后拿到一张牌的人会输掉游戏。那些人是围观者,是议论者,而在游戏中的只有X和M,他们说,这是一个愚蠢的游戏,他们说,这是一个骗局,他们说,谁先拿牌谁输,他们说,必须拿七的余数。而在他们的议论和指责中,X却一次次输掉了牌局。
七、五、三、一,单数的排列,单数的存在,而X拿到最后一张牌,也就是把自己列入到单数的世界里,它们都是质数,都是孤独的质数,X也是质数,是孤独的质数。所以游戏的意义是让他区别于那些住客,区别于M,也区别于自己。所以在质数的孤独中,他是必须要寻找一个对应物。那些走廊上的玻璃是对应物,照应着一个孤独的身影;那些镜子是对应物,反射着陌生的自己,所以,当A在镜子里出现,便也是X看见的那个对应物。镜子里的A,是被X首先看见的,然后变成身旁的A,变成对话的A,甚至变成一起走过过厅走向黑夜的A。
“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时候是在弗雷德里克巴花园里……”这是X对A说的话,也是自己对于对应物说的话。第一次在哪里?在记忆中,在虚构里,在花园内?还是在那个镜子里?第一次总是指向那个起点,只有确定了起点,任何一种行走方式都会找到出发的理由,而X把时间定在了去年,把空间定在了马里昂巴德。去年是什么,是结冰的冬季?马里昂巴德在哪里?在某一个被命名的花园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在这个词语结构中,重要的不是“去年”,也不是“马里昂巴德”,而是“在”——在是确定,在是状态,在也是“现在”。
所以,对于X来说,“在”的意义就是确定自己,确定对应物,确定时空,确定对于孤独的逃离。从镜子开始的“第一次”,到“再次踏足其上”,时间不是轮回,空间不是重复,而是将一切“在”的状态变成此时此地,“我再次遇到了您。——您从没有表现出等待我的样子,但我们总是碰到一起,在每条小径的拐角,在每个灌木丛的近旁,——在每个塑像的脚下,——在每个水池的边上,就,好像在整个花园里只有您和我。”“再次遇到你”,之后,便是总是遇到你,在小径的拐角,在灌木丛的近旁,在雕塑的脚下,在水池的旁边,每一个时间,都是“在”,每一个地方,也都是“在”。
但是,A说,我不认识你,A说,你认错了人,A说,不。“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A不需要这样一种陌生的确定吗?A不想要一个对应物吗?她从镜子里走向现实,走向有M在的现实,走向去年不在马里昂巴德的现实。躲避也好,否定也罢,在A的故事里,“在”只是不在的对立物,她的确定是为了找到“不在”的理由。所以他和她,X和A,分别从不同的起点看见对方。但是,在和不在不是一种永远的对立,不是永远的矛盾,X说到了高跟鞋,说到了灌木丛,说到了水池,也说到了那一尊雕塑。在花园里,雕塑是存在的,A就是靠在雕塑旁的栏杆上,她问,这是谁。可以有很多人的回答,但是X说,在尊雕塑里,你手臂伸出来,你给他们取名。那雕塑的男人用手护着女人,女人的手则靠着男人的背,还有那一只脚下的小狗。X也是曾经这样护着她,甚至也是要她将手放在后面,并且对她说:“请跟我来。”A起初是摇头的,但是后来她靠近了他,就像是从来他们就认识。
还有那张相片,X拿出来给她,说是去年在这里拍摄的。A看见相片里的女人,穿着白色的的衣服,坐在花园里,面朝着她。就如镜子一般,照片无非是寻找到了对应物,她是她,静止的她,去年的她,而只有拿在手上的时候,她被阅读被确认而成为自己。所以在女人不停地看相片的过程中,她把里面的女人当成了自己,“任何人都能拍这样的相片,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是,不管是任何时间还是任何地点,都不是“在”,只有在自己确认是自己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此时此地的“在”。在抽屉里,A发现了无数张相同的相片,相同的自己,当她将相片排在床上,像那个游戏一样,选择一种单数的时候,她其实也已经和X一样,走进了必然会输的游戏里。
被确认的雕塑,被确认的相片,被确认的自己,被确认的画,“那么也许在别处,在卡尔斯塔,在马里安巴,或在巴顿萨沙——或干脆就在这儿,在这个客厅里。您一直跟我到这里,让我给您讲这幅画。”X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为“在”提供多种可能,但是即使在别处,也永远是不会改变的此时此地。从镜子到游戏,从雕塑到高跟鞋,X最后说到了房间,白色的床,白色的长袍,即使A穿上了黑色的衣服,房间布置成黑色的色调,但是在被确定的“在”里,变化只能说明她在害怕:“你害怕了。”为什么要害怕,害怕什么还怕谁?是那空荡荡的走廊,是那断掉了鞋跟的高跟鞋,是那无数张的相片,是那在射击馆开枪的M,还是说出“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X?慢慢离开不在,慢慢模糊不在,对于A来说,去年和马里昂巴德渐渐成形,她变成了在的一个背景,在的一个主体,在的一种方式,“一天晚上,我上楼到了您的房间……”然后便是说好一年后的今晚,一起离开。
一年,是从起点到今晚的时间,一年,是从不在到在的时间,而一年,也是从孤独到离开的时间,“一年了,你等着我,我等着你。”对于X来说,等待意味着活着,意味着不死,所以等待也是一种“在”的状态,而A曾经等待过吗?等待M对她说爱她?等待镜子出现自己?还是等待从今晚走向去年?迷宫一样的花园,迷宫一样的时间,其实都是因为那一面面的墙的阻挡和隔绝,所以X要从这墙的世界寻找对应物,而A也要从墙的世界找到去年的坐标。
脱离于今晚,就是回到去年,而去年就是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去年,马里昂巴德在地图上也不存在。这个过去是硬性杜撰的,离开说话的时刻便毫无现实意义。但当过去占了上风,过去就变成了现在,好像一直是如此的。”这是X的去年,这是阿伦·雷乃的去年,这也是罗伯-格里耶的去年,而当过去变成现在,所有的孤独的质数,孤独的游戏,都从那个过厅的门脱身而去,不是在黑夜中迷路,也不是在寂静中迷失,而是在从“不在”到“在”的时空中,以暧昧的方式为现实与回忆寻找一个交错的可能,正如阿伦·雷乃所说:“我们从未想使本片妥协于什么明确的意义,我们永远希望它带着点暧昧,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实中复杂的事物到了银幕上就清晰起来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73]
思前: 六边形的现场